《八零之改嫁隔壁老王》 5. 第 5 章
第5章城里拜訪
冬麥覺得,生孩子這個事并不難,很多人結婚一年半載就生了,而自己結婚半年沒生,不過是運氣不好,但自己這麼努力,晚上隔三差五都要忍著痛,按理應該很快就能懷上吧?
然而事并不像冬麥想得那麼順利,夏天過了麥收后,就了秋,冬麥的桃紅子洗洗收起來了,秋天被風一吹,樹葉嘩啦啦地落了滿地,中秋節吃月餅,月餅吃完了,眼看著天就要涼了下來,冬麥肚子依然沒靜。
王秀為此說過好幾次,意思是催著林榮棠帶冬麥去陵城看看:“不看看怎麼知道,萬一有個啥呢?這都眼看進門一年了,肚子還沒靜,你說我能不急嗎?人家隔壁老三家媳婦肚子吹氣一樣大起來,人家天天問我你家媳婦啥時候懷,我怎麼有臉和人家說?”
這并不是王秀非要為難兒媳婦,是確實覺得自己委屈了,沒臉了。
這個人個子矮,長得也不好看,以前自卑,人堆里不吭聲,后來三個兒子爭氣,揚眉吐氣了,揚眉吐氣后,就比一般人更要強,事事都要出風頭,生孩子一項比人家落后了,就不了了。
天天被這麼說,冬麥難起來,覺得這日子真是沒法過,甚至曾經哭著對林榮棠說:“等明年咱們結婚一年,我要是生不出來孩子,我們就離婚吧,我是不了了。”
是當兒媳婦的,做不出和婆婆對上的事,況且確實肚子沒靜,人家婆婆說,至按照村里的邏輯,那是句句在理的。
林榮棠自然是心疼冬麥,抱著冬麥安,說沒事,等等,也許就有了,還說咱去醫院查吧,趕明兒就去醫院查。
于是這天,秋天莊稼收了又播種后,林榮棠找王秀要了五十塊錢,提了半袋子玉米面,帶著冬麥過去陵城了。
Advertisement
去陵城,先是坐牛車,之后又乘坐公家的那種公車,總算到了陵城后,冬麥暈車,一下車吐得稀里嘩啦,林榮棠從旁邊悉心照顧,找旁邊小賣鋪要了水來,給漱口,又給買一兜的小包子吃。
冬麥含著眼淚看林榮棠:“你對我真好。”
只是可恨,沒能給他生孩子,對不起他。
林榮棠嘆了口氣,安地了冬麥的辮子:“別瞎說,你我是夫妻,這都是應該的,我們先去二哥家安頓,明天再去醫院,今天估計去醫院也晚了。”
冬麥越發,心想找的這個男人,天底下再也沒有能比上的了,如果自己真和他離婚,以后的男人是萬萬不可能像他這樣疼自己。
吃了小包子后,林榮棠背著玉米面,扶著冬麥出了門店,站在路邊研究著公車站牌,城里車水馬龍,林榮棠雖然來過,但也不是特別,他還是得先研究研究。
正研究著,就聽到一個聲音:“哥,你怎麼在這里?”
林榮棠看過去,竟然是沈烈。
他頓時笑了:“你怎麼也在?我說這兩天沒看到你人影,原來是來城里了。”
說話間,他看到沈烈旁邊還站著一個人,看樣子四十多歲,穿著黑呢子大,一看就特氣派,倒是有些驚訝。
沈烈便介紹了林榮棠,又對林榮棠說:“這是我以前部隊認識的前輩,路奎軍,我得他一聲大哥。”
林榮棠一聽路奎軍三個字,頓時肅然起敬,他知道這個人。
三年前,這個人的大名就傳遍了陵城下面各公社,人人都知道,這位從某蒙拉來了三貨車的羊,之后自己用改造過的舊梳絨機,用兩個月的時間將三貨車的羊梳了羊絨,他把羊絨賣出去后,一口氣掙了五萬塊。
要知道這年頭,一年能掙一萬的,都是萬元戶,都要上電視,路奎軍這件事瞬間傳瘋了,大家都羨慕得流口水,都想跟著路奎軍學。
林榮棠只約聽人提起這位傳說中的路奎軍以前在部隊干過,沒想到沈烈竟然認識他。
路奎軍倒是一個笑的,他趕了自己的手,之后向林榮棠出手來,慌得林榮棠趕和他握手,恭敬地說:“認識你真高興,幸會幸會!”
這是他以前別人家里看電視學到的,知道電視上這麼說。
路奎軍看向了冬麥,見冬麥臉不好,便問:“這是怎麼了?”
沈烈也注意到了,挑眉問:“暈車?”
林榮棠有些不好意思:“暈車厲害的,剛才還吐了,現在好點了,我正打算坐公車去我二哥家先歇歇。”
路奎軍:“你二哥住哪兒?”
林榮棠:“就在歷崔路那邊。”
路奎軍點頭:“行,我車就在這里,我開車送你們過去吧。”
沈烈見了,略猶豫了下,還是說:“路哥,別麻煩了,你不是剛才還有事?”
路奎軍豪爽地笑了:“這是你從小一起玩到大的,都是兄弟,你平時也不是這種人,怎麼現在和我見外了?”
林榮棠連忙說不用了,路奎軍堅持,熱難卻,沈烈也就勸林榮棠上車,并提著那半袋子玉米面放車上,于是林榮棠便要扶著冬麥上車。
冬麥現在上都是虛的,覺得自己頭重腳輕,但他們剛才說的話,是聽到了,看沈烈那意思,好像剛開始不太樂意,也就不想勉強,便說:“算了,我現在好多了,就不麻煩了。”
上這麼說,可語氣卻是有氣無力,一看就虛弱。
沈烈涼涼地看了一眼,沒說話。
林榮棠反而勸:“你別逞能了,上車吧,咱盡快到了我二哥家也能歇著。”
冬麥倔不過,上了。
這個時候私家車很見,紅旗轎車,坐上去別有一番覺,坐在車里看外面,特新鮮。
林榮棠扶著冬麥,便忍不住看看車里布局,好奇地問起路奎軍,路奎軍都一一說了。
“他也會開車,還是高手,你平時多問問他就行了。”路奎軍說的這個“他”自然是指沈烈。
林榮棠倒是意外:“你還會開車,我竟然不知道!”
沈烈扯笑了笑:“這不是沒車嗎,沒車,會開車有什麼用。”
路奎軍笑道:“得,我這個給你開行不?”
幾個男人說笑著,冬麥歪歪地靠在座椅背上,座椅上有一皮子的味道,聞著其實反而更難了,不過想到這樣比坐公車滿滿晃悠著去家里快多了,也就努力忍著。
說話間,不知怎麼就提起來沈烈離婚的事,兩個男人自然安沈烈,大丈夫何患無妻,但沈烈卻是并不在乎的樣子。
冬麥懨懨地靠著,心里卻想起來鄰居們叨叨的,說是孫家向他道歉了,彩禮二百塊也還給他了,至于其它的,他竟然真得一分錢沒要。
大家都替他惋惜,對方姑娘做出這種事,害得他人財兩空,他不要一筆太可惜了,可是又有什麼辦法,人家說不要就是不要。
當然也有人認為他這算是仁義,大男人嘛,人家人不愿意跟你了,也就認了,追著人屁后面要錢算什麼?
這個時候林榮棠二哥家已經到了,車停下來,林榮棠謝過了路奎軍,冬麥也表示了謝,林榮棠便扶著冬麥下車了。
下車后,還對著人家揮揮手,人家就開車走了。
這個時候涼風一吹,冬麥反而覺得好多了,人也清醒了許多,便和林榮棠一起上了二樓。
林榮棠他二哥林榮在陵城化工廠上班,娶的媳婦是陵城第一醫院的護士,兩口子都忙的,這個點兒都不知道在不在家。
吭哧著爬向二樓,運氣好,林榮棠二嫂竟然在。
二嫂戴向紅,皮白,不過眼睛下面有個大痦子,格溫開朗,懂的也多,冬麥雖然只見過幾次,但對很是敬佩。
戴向紅一看林榮棠兩口子過來了,趕把們招呼進門,見他們帶著半袋子玉米面,倒是高興的,說這個自家種的比外面賣得好,又沖了橘子水給他們喝。
戴向紅問起他們兩口子來陵城干嘛,林榮棠有些尷尬,便起裝去上廁所避開了,冬麥便把這事說給戴向紅了。
戴向紅聽了,笑道:“才結婚不到一年,其實不用急,要孩子這事真是緣分,不過婆婆那里既然說了,那趕明兒我帶你們去醫院,你們都去查查就是了。”
冬麥有些懵:“都去查查?”
戴向紅:“是啊,可不都得去查查嘛!一般都沒問題,這不是著急嗎,著急就查查唄。”
冬麥懂了:“所以我們生不出孩子,有可能是我的問題,也有可能是他的問題,還有可能我們兩個都沒問題,只是暫時沒懷上。”
戴向紅笑:“對,就是這樣!”
冬麥恍然,恍然之后簡直是打開了新世界的大門。
以前,婆婆說是下不出蛋的母,是不是也應該說,不一定是誰的問題呢,不查怎麼知道?
當然了,現在在陵城查個明白,萬一真是自己的問題,自己就識趣點,趕離婚,如果不是,那以后婆婆說自己,自己可是有話說了。
所以來查查真不是壞事。
戴向紅倒是喜歡這個村里的弟妹,覺得淳樸可,長得也不錯,誰不喜歡水靈靈的小媳婦呢。
“總之,你不用著急,明天就帶你去醫院查,這個我給你安排就是了。”
冬麥聽著,一掃之前暈車的低迷,心豁然開朗。
猜你喜歡
-
完結1662 章

悠哉獸世:種種田,生生崽
一跤跌到獸人世界,被一頭花豹強擄回家,白箐箐的心情是崩潰的。這個世界的雄性個個長的跟花孔雀一樣華麗英俊,雌性卻都是丑女無敵,長的丑還被雄性寵上天。她本來只能算清秀的高中生,在這里卻成了絕美尤物,迷死獸了。最最最惡搞的是,這里還是母系社會,姐可不想三夫四侍啊!撩花豹,逗猛虎,誘毒蛇,擒雄鷹。後宮充實的白箐箐欲哭無淚,她真的不是故意的啊︰“哎哎哎,豹兄,虎哥,蛇鷹兄,你們做什麼?別過來啊!”男主有四個︰年輕氣盛豹、陰郁沉默蛇、強勢大佬虎、冷漠正義鷹。
147.7萬字8.18 206489 -
完結1793 章

試婚100天:帝少的神秘妻(陌下悠竹)
「我們的媽咪就是你的老婆,怎麼?你的老婆有兩個娃這事你不知道?」小娃兒望著他,『好心』的提醒。他呆愣了兩秒,臉上的神情瞬息間風雲變幻。好,很好,他倒要看看她還瞞了他多少事?這賬是該跟她好好算算了。然而……溫若晴是誰?又醜又笨一無是處的花癡大小姐?NO!她是犯罪心理事學博士,她傾國傾城、冰雪聰明,絕代無雙!夜三少,這賬你想怎麼算?夜三少是誰?翻手為雲覆手為雨,叱詫商場無人能及!據說夜三少寵妻也是無人能及!!!
342.5萬字8 96002 -
完結1760 章

軍婚撩人:性冷首長夜夜寵!
他是集團軍長,冷酷如狼,唯獨對她束手無策。自從那晚醉酒他親了她後,喬顏就明白了一個道理。她要征服這個男人,就得撩他、親他、上他!矜持啊羞澀什麼的,去它嘛噠!喬顏:“靳哥,我要吃肉。”穆靳堯:“紅燒,清蒸,水煮還是涼拌?”她瞟他八塊腹肌,“原味更好。”她問,“穆靳堯,你信不信有天我紅杏出牆?”他輕蔑一笑,“有我這堵牆,你能出的去?”
162.3萬字8 420947 -
完結68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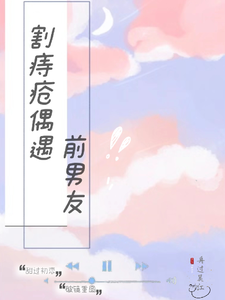
割痔瘡偶遇前男友
新作品出爐,歡迎大家前往番茄小說閱讀我的作品,希望大家能夠喜歡,你們的關注是我寫作的動力,我會努力講好每個故事!
15.5萬字8 609 -
完結173 章

救命!戀愛腦沈總又在秀夫啦!
【雙男主+雙潔+豪門太子爺】【綠茶嘴毒攻×清冷美人受】 沈褚辭第一次見到謝遇桉是在酒吧。 身邊的狐朋狗友正在喝酒吹牛,不知怎的就提起了謝家那個一頭銀發及腰的謝大少,話題還沒聊多久,主人公就帶著三十多個保鏢將酒吧一齊圍了起來。 忽明忽暗的燈光下,沈褚辭一眼就對上了那雙清冷絕情的眼眸,等到謝遇桉走近,他才發現,一直被人說是顏狗而言辭義正糾正的他,原來就是一只顏狗…… 長著一張天人共憤的絕美容顏的沈老狗,此刻心里嗷嗚嗷嗚的嚎:怎麼會有人的顏值剛好長在自己的心巴上啊!! 于是他理了理衣領,優雅的走上前,朝銀發美人伸出手,語調深情:“你好老婆,結婚。” 謝遇桉:? 誰家好人一上來就直奔結婚的?!! 但……謝遇桉是個資深顏狗,看著面前妖孽般的沈少爺,他可恥地心動了。 幾秒后,銀發美人伸出手,瓷白如玉的手握上那只伸過來的大手,臉上波瀾不驚道:“好啊。” 沈褚辭:!!!老婆答應我了!!!
26.3萬字8 132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