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庭春》 第 103 章 番外11
閃電劃過的一瞬,整個天際都被照亮。
隨之而來的雷聲,像震在耳上的鼓點。
陸國公驚醒過來,愣怔地著這間簡陋狹小的斗室。
空氣中彌漫著的檀香味道,令他很快沉靜下來。
他在這里,已經生活了十幾年。
遠離塵囂,避世至此,對外他以“靈一”法號自稱,早當自己是方外之人。
對,……他已經連續夢見璧君好幾個年頭。夢見穿著大紅宮裝,揮別深宮來到他邊。夢見掀開蓋頭的一瞬腮邊凝結的那滴眼淚。夢見把男嬰抱在手上推向他。夢見臉蒼白形容枯槁般躺在棺槨中。夢見黃土掩埋了的棺木,香消玉殞再也醒不來……
他從夢中驚醒后,枕邊總是了一塊。
他一向心狠,別說流淚,一輩子就連說句話都不曾。
他不知自己到底是怎麼了。
有人說,當你頻繁夢見一個死去的人,興許就是你的時限也將到了。
若這個說法是真,想必,是璧君來接他了。
黃泉路上,他還能再遇到嗎?
還愿意,再見到他這個人嗎?
看護他的小廝發覺他醒了,忙端了熱茶走近,“先生,先喝口茶,潤潤嗓子吧。”
他帶發修行,不是僧又以方外之人自居,不許人稱“爺”或旁的世俗稱謂,只得喚生“先生”以表敬意。
陸國公接過茶來,抬眼向線朦朧的窗屜,“什麼時辰了?”
“丑時三刻,先生,外頭雷聲擾了您吧?天還未亮,您再眠一眠?”
陸國公擺擺手,將飲過的茶遞回去,“將燈移過來,昨日沒瞧完那卷經,找出來與我。”
小廝待勸些什麼,見他蠟黃枯瘦毫無表的臉,最終將話又吞了回去。他知道,陸國公不會聽勸。
Advertisement
屋里燭火昏暗,陸國公倚靠在竹床上,沉默地瞧著經書。
他看的是梵文謄抄的手稿,這幾年閑極無事,他開始鉆研梵文和偶然得來的教古經。在這些晦的文字間,他能尋求到一難得的平靜,他將生命的全部時耗費在這上面,避免有閑暇去回憶從前,去追溯對錯。這是他與自己和解的方式。
天亮之時,他又昏昏地睡了過去。
明箏來時,沒有人驚擾他,將帶來的東西命人收整好,問過了他的病,瞧了昨日的脈案,明箏對服侍他的人道:“等公爺醒了,勸一勸,說道路難行,大夫不便上山,若是愿意,可遷到城里,安定門大街東南的宅子還空著。”距離公府甚遠,環境清幽,四周沒有署和人,方便看病抓藥,又不怕被人打擾。“在那邊也修了小佛堂,不耽擱公爺清修。”
小廝尚未答話,便聽里頭傳來一陣咳嗽聲,“是陸筠家的?進來吧。”
又一陣咳嗽聲后,明箏被請室。
這是頭一回,走進陸筠父親的居所。
尋常人家公媳雖也不見得日日相見,定時不定時的請安問候總不可免,更別提年節家宴、族中祭祀、宮中大禮等場合。可明箏,這才是第二回見到陸筠的父親。
“媳婦兒請父親安。”居室不大,一間明堂一間書房一間寢房,明箏立在明堂磚地上,垂頭不敢看。
陸國公擺擺手,道:“這幾日你常來,夏末秋初,多雨,醫者上山不便,你一婦道人家,愈發不便。今日之后,再不必來。”
明箏抿了抿,“聞知父親抱恙,家中牽掛不已,侯爺公務纏離不得,祖母年歲大了出門不便,故托付于我探侍奉……”
陸國公笑了聲,“公務纏?陸筠卸任指揮使一職,有一年余了吧?”
明箏倒也沒什麼被拆穿了謊言的窘迫,如何彼此都明白,只是這個份,有些話不好明說。
陸國公咳了咳道:“我知,你是個仁義的,不論是為了陸筠,還是為了你祖母,盡心竭力,無論什麼事你都做得很好。很謝謝你,對他們這樣赤忱用心。也謝謝你,沒像那些俗人一樣張口就問我份責任輕重迫我回京。”
明箏道“不敢”。
“我在山上習慣了。”他說,“這十幾年,我日出即起,日落而息,黃卷殘燈相伴,沉香翠樹環,再紅塵,更添不便,無法,只得辜負你一片好心。”
明箏想了一路相勸的話,想過要如何曉之以,可這一刻,發覺那些道貌岸然的話說不出口。無疑對陸國公,其實也是百般不解,甚至有些生怨的。怨他委屈了陸筠這麼多年,怨他冷落了陸筠這麼多年。
“我在山中有些好友,他們有的是樵夫,有的是山腳下的賣茶人,也有為我講經布道的高僧,我的半生都在這里,余生也都將在這里。我識得懂醫的士,我對自己的況很了解。你送來的人,我收下了,年紀大了,行不便,邊確實再離不得人,有這幾個孩子,我已經很知足,你選的人都很穩妥,我要謝謝你。”
“我不會下山,你別再為我奔忙,明、明箏是嗎?你和陸筠回去好好過日子,要善待子,善待對方,壞的方面,就不要學我了。對了,桃桃,剛過了三歲生辰對嗎?小寧子,去,把我書房桌上那東西拿來。”
小廝飛快去取了只盒子奉上,陸國公指了指明箏,“給。”
“是我親手刻的一枚印,送給桃桃,賀生辰。算我……算我這個不合格的祖父,一點心意吧。”
他說這話時,語速放得很慢,如果仔細傾聽,能在那過分漫長的停頓中聽出一抹心酸。
他自稱是“祖父”,他這個了半生,說自己再不世俗的男人,這一刻自稱是桃桃祖父。明箏知道,他終究還是沒有放下紅塵。
沒有放下陸家。
也沒有放下過陸筠。
雙手接過盒子,覺得手里的東西仿佛千斤般重。
“為什麼?”明知不該問,可這三字還是自口中問了出來。
陸國公抬眼,了明箏。婦人俏麗的臉上帶了抹哀,也正著他,迫切地祈求一個答案。
是在為陸筠問他,為那個從小被他拋下、從來不肯多瞧一眼的獨子問他。
漫長的沉默過后,陸國公淡然的表也有一松。
也許是他老了,心腸不起了。
“我是在贖罪。”他說,“我這一生,對不起太多人。守著青燈黃卷,跪拜八方神佛,以求得一星半的寬恕和藉。告訴他,不是他的錯。他母親和我,也都很歡喜他來這世間。只是我不配被稱一聲父親。明箏,替我好好地守著他,他這一生,因我而遭了太多的苦痛,但愿你,能替代我平他所有的傷。”
一滴清淚自他左眼落,很快被灰的袖角抹去,明箏再瞧時,就只見他又出平素那平淡坦然的面容,仿佛適才他所說出的所有字句,都只是一個人的幻想。
明箏行禮退了出去。
天晴起來,不知何時變得這樣刺眼。
扶著瑗華的手往山下走,才走了半段路,就見前頭石階上立著個高大拔的影子。
“是侯爺!”瑗華認出來人,有些吃驚。侯爺從來不肯踏足這片地界,他連提起陸國公都不肯,又怎麼愿意來瞧他?
他朝明箏走來,出手,將從瑗華手里接過,“剛下完大雨你就上山來,萬一倒了摔跤了怎麼是好?慢些。”
“侯爺是來接我的?”明箏攀住他手臂,含笑說。
“嗯。”他點頭,除此外,還有別的理由來這兒嗎?
“侯爺真好。”把頭輕輕靠在他臂膀上,陸筠側過頭打量,果然在眼角發覺了可疑的一點紅腫。哭過。
“他、給你臉看了?說重話你難了?”他將拳頭起,眉頭也蹙了起來。
“沒有的。”忙解釋,“爹待我很和氣,還給咱們桃桃送了生辰禮,是爹親手做的。”
陸筠不吭聲,對那個父親,他連評價一句也不愿。
兩人上了馬車,才坐穩,明箏就擁了過來。抱著他,著嗓音道:“筠哥,他說你能出生他是很高興的,娘也是很高興的,他鬧著要出家,鬧著不回公府,他是不知道該怎麼面對你,他自責,因為他害得娘郁郁寡歡早早亡故,他心里覺得太歉疚了,所以沒臉見你,不是你的錯,不是你不好,筠哥,你聽見了嗎?你聽見我說什麼嗎?”
陸筠沉默著,他的額頭在明箏鎖骨之下,他不說話,眉頭鎖薄抿。
明箏俯下,捧著他的臉吻他的臉頰、他的。
“你是天底下最好的人,我就知道,沒人會不喜歡你的。他也一樣,早年他們之間發生過什麼,我們也許沒辦法完完全全去了解了,可這世上有許多種夫妻,吵吵鬧鬧一輩子,未必心里沒有對方的。筠哥,你相信我,他不是不想面對你,他是沒辦法面對傷害過你的他自己,筠哥,你聽見了嗎?每個人都會做錯事,當年的他也會。筠哥,我不是想勸服你去接他,或者勸你去原諒這一切。你有權恨,有權怨,有權生氣,你沒有錯。我只是……我只是想告訴你,你是最好最好的人,沒有人會不愿意見到你,那些冷冰冰的面孔惡毒的話毫不在意的表,都是假的。你不要恨自己,不要怪自己,放過自己吧,好不好,筠哥?”
猜你喜歡
-
完結2088 章

廢柴王妃又在虐渣了
蕭涼兒,相府大小姐,命格克親,容貌被毀,從小被送到鄉下,是出了名的廢柴土包子。偏偏權傾朝野的那位夜王對她寵之入骨,愛之如命,人們都道王爺瞎了眼。直到人們發現,這位不受相府寵愛冇嫁妝的王妃富可敵國,名下商會遍天下,天天數錢數到手抽筋!這位不能修煉的廢材王妃天賦逆天,煉器煉丹秘紋馴獸樣樣精通,無數大佬哭著喊著要收她為徒!這位醜陋無鹽的王妃實際上容貌絕美,顛倒眾生!第一神醫是她,第一符師也是她,第一丹師還是她!眾人跪了:大佬你還有什麼不會的!天才們的臉都快被你打腫了!夜王嘴角噙著一抹妖孽的笑:“我家王妃肩不能挑手不能提,是個柔弱小女子,本王隻能寵著寵著再寵著!”
400.4萬字8.08 204045 -
完結1816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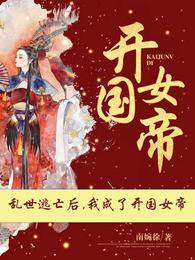
亂世逃亡后,我成了開國女帝
◣女強+權謀+亂世+爭霸◥有CP!開局即逃亡,亂世女諸侯。女主與眾梟雄們掰手腕,群雄逐鹿天下。女主不會嫁人,只會‘娶’!拒絕戀愛腦!看女主能否平定亂世,開創不世霸業!女企業家林知皇穿越大濟朝,發現此處正值亂世,禮樂崩壞,世家當道,天子政權不穩,就連文字也未統一,四處叛亂,諸王征戰,百姓民不聊生。女主剛穿越到此處,還未適應此處的落后,亂民便沖擊城池了!不想死的她被迫逃亡,開
238萬字8.18 16115 -
完結129 章

盛寵
【全文完結】又名《嫁給前童養夫的小叔叔》衛窈窈父親去世前給她買了個童養夫,童養夫宋鶴元讀書好,長得好,對衛窈窈好。衛窈窈滿心感動,送了大半個身家給他做上京趕考的盤纏,歡歡喜喜地等他金榜題名回鄉與自己成親。結果宋鶴元一去不歸,并傳來了他與貴女定親的消息,原來他是鎮國公府十六年前走丟了的小公子,他與貴女門當戶對,郎才女貌,十分相配。衛窈窈心中大恨,眼淚汪汪地收拾了包袱進京討債。誰知進京途中,落難遭災,失了憶,被人送給鎮國公世子做了外室。鎮國公世子孟紓丞十五歲中舉,十九歲狀元及第,官運亨通,政績卓然,是為本朝最年輕的閣臣。談起孟紓丞,都道他清貴自持,克己復禮,連他府上之人是如此認為。直到有人撞見,那位清正端方的孟大人散了發冠,亂了衣衫,失了儀態,抱著他那外室喊嬌嬌。后來世人只道他一生榮耀,唯一出格的事就是娶了他的外室為正妻。
31.9萬字7.92 62628 -
完結99 章

和死對頭成婚后
六公主容今瑤生得仙姿玉貌、甜美嬌憨,人人都說她性子乖順。可她卻自幼被母拋棄,亦不得父皇寵愛,甚至即將被送去和親。 得知自己成爲棄子,容今瑤不甘坐以待斃,於是把目光放在了自己的死對頭身上——少年將軍,楚懿。 他鮮衣怒馬,意氣風發,一雙深情眼俊美得不可思議,只可惜看向她時,銳利如鷹隼,恨不得將她扒乾淨纔好。 容今瑤心想,若不是父皇恰好要給楚懿賜婚,她纔不會謀劃這樁婚事! 以防楚懿退婚,容今瑤忍去他陰魂不散的試探,假裝傾慕於他,使盡渾身解數勾引。 撒嬌、親吻、摟抱……肆無忌憚地挑戰楚懿底線。 某日,在楚懿又一次試探時。容今瑤咬了咬牙,心一橫,“啵”地親上了他的脣角。 少女杏眼含春:“這回相信我對你的真心了嗎?” 楚懿一哂,將她毫不留情地推開,淡淡拋下三個字—— “很一般。” * 起初,在查到賜婚背後也有容今瑤的推波助瀾時,楚懿便想要一層一層撕開她的僞裝,深窺這隻小白兔的真面目。 只是不知爲何容今瑤對他的態度陡然逆轉,不僅主動親他,還故意喊他哥哥,婚後更是柔情軟意。 久而久之,楚懿覺得和死對頭成婚也沒有想象中差。 直到那日泛舟湖上,容今瑤醉眼朦朧地告知楚懿,這門親事實際是她躲避和親的蓄謀已久。 靜默之下,雙目相對。 一向心機腹黑、凡事穩操勝券的小將軍霎時冷了臉。 河邊的風吹皺了水面,船艙內浪暖桃香。 第二日醒來,容今瑤意外發現脖頸上……多了一道鮮紅的牙印。
25.2萬字8 140 -
完結123 章

不是聯姻嗎?裴大人怎麼這麼愛
姜時愿追逐沈律初十年,卻在十八歲生辰那日,得到四個字:‘令人作嘔’。于是,令沈律初作嘔的姜時愿轉頭答應了家里的聯姻安排,準備嫁入裴家。 …… 裴家是京中第一世家,權勢滔天,本不是姜時愿高攀得起的。 可誰叫她運氣好,裴家英才輩出,偏偏有個混不吝的孫子裴子野,天天走雞斗狗游手好閑,不管年歲,還是性格,跟她倒也相稱。 相看那日—— 姜時愿正幻想著婚后要如何與裴子野和諧相處,房門輕響,秋風瑟瑟,進來的卻是裴家那位位極人臣,矜貴冷肅的小叔——裴徹。 …… 裴太傅愛妻語錄: 【就像御花園里那枝芙蓉花,不用你踮腳,我自會下來,落在你手邊。】 【愛她,是托舉,是陪伴,是讓她做自己,發著光。】 【不像某人。】
23.8萬字8.09 92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