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權相養妻日常》 114.重歸
次日清晨, 令容醒來時枕邊空的, 韓蟄不知去了何,簾帳層層垂落, 隔出榻間昏暗。上酸痛, 轉了個, 懶得爬起來,只懶聲道:“宋姑。”
聲音出口才發覺有點沙啞似的,聽著都疲倦無力。
“夫人醒了”宋姑聽見靜掀簾進來,見令容懶懶的趴著, 溫聲道:“再睡會兒吧。”
“什麼時辰”
“快巳時中了。大人吩咐的, 他去夫人那邊問安,夫人隨便睡到多晚都。”宋姑已在別苑里伺候過了,將昨晚的痕跡略收拾過, 見令容仍趴在被窩里睜著眼,才道:“不睡了嗎”
“睡不著了。”令容瞇著眼睛, “備水沐浴吧。”
沉睡后沒半點困意,卻仍疲累,再睡也沒用,還不如沐浴舒緩酸痛。拿手指頭摳著韓蟄的枕頭,隨口道:“他呢”
“去和堂后就沒回來,不是去書房, 就是在老太爺那里。”宋姑回來卷了簾帳, 滿屋明亮照進來, 竟有點刺目似的。自去浴房, 備妥了,才招呼枇杷過來,伺候令容去沐浴。
溫熱的水蔓延全,浴房里的凌痕跡也被宋姑收拾干凈了。
令容闔目泡著,任由宋姑慢慢地幫著手臂肩膀,緩解難。
韓蟄還算有點良心,昨晚初時沒太強,等適應了才馳騁,是以子雖疲累難,倒不像頭回似的疼痛。泡了小半個時辰,才不得不因腸轆轆而爬出來,干子套了寬松的裳,吃過紅菱備下的香甜早飯,才算神起來。
然而間畢竟難,也懶得走路,知道韓蟄招呼過,也沒去和堂。
歇了整日,傍晚時才見韓蟄回來,神抖擻。
Advertisement
今晚雖是元夕,卻累得不想彈,楊氏是兒媳有孝在,韓瑤興致也不高,便沒特地去賞燈,只在府里放了些煙花便罷。
晚飯是闔府一道吃的,仍舊設在慶遠堂附近的暖閣里。
韓鏡仍坐在上首,底下兒孫按次序坐著,旁邊沒了太夫人,便是楊氏在下居首。
令容是跟著楊氏一道去的,因劉氏婆媳還沒到,先在廳里坐著等候。待韓鏡過來時,如常起問候,那位沉肅依舊,也沒多分幾個眼神,目掃過令容和韓瑤,落在楊氏上,才眾人回座位,又跟韓墨和韓蟄兄弟說話。
這形跟令容初府時沒太多區別,此刻看破背后爭執,再瞧起來,就截然不同。
宴席至戌時盡了才散,韓鏡留兒孫說話,令容自回住。
明日十六,正好休沐,過后韓蟄便須忙碌起來。
先前唐敦死后,令容有意去寺里進柱香,算是給前世的事一個代。因在金州心緒歡暢,不考慮那些煩惱事,便在回京城的路上跟韓蟄提起,韓蟄也沒多問,答應了。
今晚跟楊氏提及,韓瑤也說要去,順道往山間散心,約定明日用過早飯便出發。
令容可不想明日帶著滿疲累騎馬出城,早早沐浴了,也不等韓蟄,先上榻安歇。
待韓蟄夜深回來時,屋中燈火雖明,里頭卻頗昏暗。
宋姑奉命在外候著,見他回來,恭敬稟報道:“夫人子不適,覺得疲累,先歇下了,還大人勿怪。奴婢奉命在外伺候,浴房里已備了熱水。”
韓蟄頷首,命退下,自去浴房沐浴,換上寢出來,就見令容睡得正。
室燈燭熄了一半,仍舊明晃晃的,向里而睡,呼吸平緩綿長,錦被下的軀微微蜷。韓蟄沒打攪,自將燭火都熄了,坐到榻上,掀被而。
榻上換了新的寬大被褥,他仰面躺平了,卻睡不著。
在外征戰奔波,宿荒郊是常有的事,獨宿書房時,滿心政事,也不覺心煩氣躁,躺下調息片刻就能睡。到了銀院里,枕畔是的呼吸,鼻端約有沐浴后的清香,懷里空的總難清心靜氣,遂往里挪了挪,臂握住手。
令容似乎察覺,睡夢里翻了個,迷迷糊糊的了聲“夫君”。
韓蟄臂將抱著,心里仿佛覺得踏實,沉沉睡去。
京城外名剎頗多,令容這回選的是普云寺。
普云寺在城南三十里的孤竹山中,香火不算旺盛,里頭卻有數位高僧修行,佛學修為的名頭未必如旁人趨之若鶩的寶剎響,在書畫上的造詣卻是京城里排得上號的。因孤竹山里還有章老的梅塢,其間主人或是鴻學巨儒、或是顯貴名家,常有才子題詞揮毫,高僧琴彈佛法,兩名聲疊,孤竹山便雅致所在。
去普云寺進香的,也都是文人雅客,倒有清幽離塵,絕世而立的況味。
令容向來是雅俗皆的,這回因惦記著梅塢尚未開敗的茶梅,便選了此。
早飯后騎馬出府,因韓征回京后重歸羽林衛,替了原先范自鴻羽林郎將的位子,皇宮戍衛值與衙署休沐不同,他無暇空,便只韓蟄帶著令容和韓瑤,帶飛鸞飛跟從。
春日里天氣漸暖,出城后放馬疾馳,道兩側的柳樹已能瞧見零星的新綠枝。
孤竹山底下有溫泉,地氣比別和暖,踏馬而過,春草青。
來這兒的多是文人雅客,或孤或結伴,不像別似的眷車馬仆從如云,進寺的路倒是清幽,兩側古柏高聳,老松墨綠,中間石徑蜿蜒而上,有枯葉未掃,隨風輕。
五人棄馬而行,韓蟄跟令容走在前頭,韓瑤帶飛鸞飛在后信步賞玩。
令容雖歇了整日,將石階走得多了,雙也自酸痛,悄悄拽著韓蟄的袖借力,被他察覺,反手握住拉著,倒省了不力。
普云寺建在孤竹山腰,遠山巒起伏,石徑兩側卻都是松柏,春里疏影橫斜。
前后數十步外也有人造訪佛寺,紙扇輕搖,仿佛閑庭信步。
令容縱有那樣閑適的心,也沒那等力,被韓蟄半拉半攙地帶到佛寺山門外,已是氣吁吁,兩頰泛紅,拽著韓蟄的肩膀,先忙著緩口氣。
高聳的山門里有一片碑林,周遭松柏映襯,有年輕學子觀評點,其中一人站在人群外兩三步,墨長衫秀,玉冠束發腰纏錦帶,背影頗為悉。
那人仿佛也察覺了似的,忽然回往這邊瞧過來。
這一轉,不止令容,連同才輕而易舉趕上來的韓瑤都怔住了。
竟是飄然去后杳無音信的高修遠
時隔一年,他在京城銷聲匿跡,忽然出現在此,著實人意外。
然而比起記憶里溫潤如玉的年郎君,他姿雖秀如舊,氣質卻變了許多。從前慣的玉白錦換作深濃的墨長衫,隔著不近的距離,他清秀的臉上殊無笑意,靜靜著這邊,像是冬日里霜雪封著的青竹似的,冷清淡然,沒了舊日的意氣風發、溫和談笑。
怔了片刻,還是令容開口,“那是高公子”
“他怎會”令容詫異,見韓瑤只管怔怔著那邊,輕握住手。
韓瑤回過神來,有些無措似的,淡然斂了眉目。
那邊高修遠似也在猶豫,但既然瞧見,畢竟沒有視而不見的道理,遂緩步過來,拱手為揖,“韓大人,夫人,韓姑娘。”他走得近了,容貌俊秀如舊,眼底的冷清也愈發明顯,全無從前的溫潤笑意。
韓蟄頷首,令容也同韓瑤行禮,“高公子也是來進香嗎”
“我住在這佛寺里,請慧深大師指點技藝。”
“還以為你已離開京城了,想求幅畫,也沒音信。”令容笑了笑。
“臘月回來的,先前不在京城。”高修遠微笑,卻沒接后面的話茬。
令容頷首,一時間倒不知該說什麼。對高修遠的才華極為嘆服,數番往來,也敬佩他心為人,前幾日在金州時,傅錦元還曾嘆,說想再找幾幅高修遠的畫來觀玩,卻杳無音信。久別重逢,原本有話想說,但韓蟄就在旁,還得留意分寸。
韓蟄在外仍是錦司使的冷厲模樣,甚跟人寒暄,見到高修遠,也只神微而已。
剩下個韓瑤,從前為求畫,總尋機往高修遠那邊跑,自知無后,也適時收斂了心思。
山風拂過,片刻安靜,高修遠墨衫微,“幾位若是進香,就不攪擾了。”
說罷,也沒多瞧韓蟄兄妹,只朝令容招呼般瞧了一眼,轉走開。
裳被風卷得翻飛,他走出老遠,才在松柏下駐足回。
隔著松枝掩映,令容的姿影影綽綽,比從前又修長窈窕了許多。旁邊韓蟄冷肅如舊,一如他初京城時所見的錦司使。
田保死后,父親龍游縣令被人刺殺在府里,案卻被寧國公甄家得死死的,只以暴斃之名上報,不許州府細查,他直到回鄉時才得知實。寧國公甄家為一己私憤清算舊賬,謀殺縣令,那件事在龍游縣人盡皆知,縱然難將消息傳到京城,但以錦司遍及天下的耳目,韓蟄未必不知。
故人重逢,韓蟄只字不提此事,也許早已忘記,也許對一介縣令的死毫不在意。
屹立三朝的相府,縱有扳倒佞權宦以清君側的名聲,卻仍與仗勢欺人的甄家沆瀣一氣,在朝堂聯手謀權,在私下往來親近,京城里擺出和善禮儀的面孔沽名釣譽,卻只在僻遠之盤剝掠奪,魚百姓。
高修遠沒指誰能張正義,但韓家與甄家的往來,仍讓他覺得心寒。
從前,是他想岔了。
高修遠收回目,邊笑意嘲諷。
猜你喜歡
-
完結585 章
小公主又幫母妃爭寵了
穿書成了宮鬥劇本里的砲灰小公主,娘親是個痴傻美人,快被打入冷宮。無妨!她一身出神入化的醫術,還精通音律編曲,有的是法子幫她爭寵,助她晉升妃嬪。能嚇哭家中庶妹的李臨淮,第一次送小公主回宮,覺得自己長得太嚇人嚇壞了小公主。後來才知道看著人畜無害的小公主,擅長下毒挖坑玩蠱,還能迷惑人心。待嫁及笄之時,皇兄們個個忙著替她攢嫁妝,還揚言誰欺負了皇妹要打上門。大將軍李臨淮:“是小公主,她…覬覦臣的盛世美顏……”
105.9萬字8 170382 -
完結729 章
東風第一枝
葬身火場的七皇子殿下,驚現冷宮隔壁。殿下光風霽月清雋出塵,唯一美中不足,患有眼疾。趙茯苓同情病患(惦記銀子),每日爬墻給他送東西。從新鮮瓜果蔬菜,到絕世孤本兵器,最后把自己送到了對方懷里。趙茯苓:“……”皇嫂和臣弟?嘶,帶勁!-【春風所被,第一枝頭,她在他心頭早已綻放。】-(注:無血緣關系無血緣關系無血緣關系,重要的事情說三遍!)
97.7萬字8 8970 -
完結467 章

全家帶著千億物資去逃荒
【全家穿越、空間萌寵、逃荒、種田】 蘇以安撓著雞窩頭看著面前冰山臉少年,心里一頓MMP。 全家集體穿越,本以為是個大反派制霸全村的勵志故事,這咋一不小心還成了團寵呢? 爹爹上山打獵下河摸魚,他就想老婆孩子熱炕頭,一不小心還成了人人敬仰的大儒呢。 娘親力大無窮種田小能手,就想手撕極品順便撕逼調劑生活,這咋還走上了致富帶頭人的道路呢? 成為七歲的小女娃,蘇以安覺得上輩子太拼這輩子就想躺贏,可這畫風突變成了女首富是鬧哪樣? 看著自家變成了四歲小娃的弟弟,蘇以安拍拍他的頭:弟啊,咱姐弟這輩子就安心做個富二代可好? 某萌娃一把推開她:走開,別耽誤我當神童! 蘇以安:這日子真是沒發過了! 母胎單身三十年,蘇以安磨牙,這輩子必須把那些虧欠我的愛情都補回來,嗯,先從一朵小白蓮做起:小哥哥,你看那山那水多美。 某冷面小哥哥:嗯乖了,待你長發及腰,我把這天下最美的少年郎給你搶來做夫君可好? 蘇以安:這小哥哥怕不是有毒吧!
87.4萬字8 47099 -
完結159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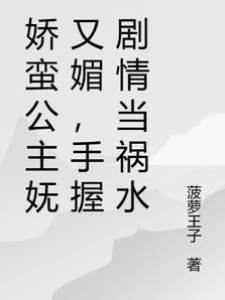
嬌蠻公主嫵又媚,手握劇情當禍水/嬌蠻公主以色爲誘,權臣皆入局
【釣係嬌軟公主+沉穩掌權丞相+甜寵雙潔打臉爽文1v1+全員團寵萬人迷】沈晚姝是上京城中最金枝玉葉的公主,被養在深宮中,嬌弱憐人。一朝覺醒,她發現自己是活在話本中的惡毒公主。不久後皇兄會不顧江山,無法自拔地迷上話本女主,而她不斷針對女主,從而令眾人生厭。皇權更迭,皇兄被奪走帝位,而她也跌入泥沼。一國明珠從此被群狼環伺羞辱,厭惡她的刁蠻歹毒,又垂涎她的容貌。話本中,對她最兇殘的,甚至殺死其他兇獸將她搶回去的,卻是那個一手遮天的丞相,裴應衍。-裴應衍是四大世家掌權之首,上京懼怕又崇拜的存在,王朝興替,把控朝堂,位高權重。夢醒的她勢必不會讓自己重蹈覆轍。卻發覺,話本裏那些暗處伺機的虎狼,以新的方式重新纏上了她。豺狼在前,猛虎在後,江晚姝退無可退,竟又想到了話本劇情。她隻想活命,於是傍上了丞相大腿。但她萬萬沒有想到,她再也沒能逃出他掌心。-冠豔京城的公主從此被一頭猛獸捋回了金窩。後來,眾人看著男人著墨蟒朝服,明明是尊貴的權臣,卻俯身湊近她。眼底有著歇斯底裏的瘋狂,“公主,別看他們,隻看我一人好不好?”如此卑微,甘做裙下臣。隻有江晚姝明白,外人眼裏矜貴的丞相,在床事上是怎樣兇猛放肆。
27.8萬字8 5722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