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小姐進京了》 第118章 第118章
賬單不要,只要能看到小白就好了,所以一手痛快接下賬單,一臉掩不住的興:“小白。”這個時候頗有些像是個二傻子,見到白蓮心后所展出來的表,跟他這張邪魅狷狂的臉一點都不相稱。
所以白蓮心看了眼也頗有些嫌棄,“既然如此,你早些將銀子補上。”然后便要轉回去,還要給王妃炒蕨菜涼拌蕨菜呢。
夏侯緋月看要走,急得不顧男之別,眼疾手快一把將拉住,“你怎麼就要走了?我知曉你在這里過得并不好,跟我走吧,我會好好照顧你的。”
白蓮心聽到這話,只覺得好笑,心想這麼多年了,他仍舊是這般稚,一面忍不住轉頭冷笑,問道:“殿下可知曉,無為憑,為私奔,我是出生低位,但你既然口口聲聲說喜歡我,可你就這樣喜歡我的?我無名無份?”
夏侯緋月一怔,他從來沒有考慮這些,畢竟他想要見白蓮心一面都艱難,一時間也是被白蓮心這話堵得半句話都說不出來。
但一想到白蓮心想要給夏侯瑾做妾,寧愿給夏侯瑾做妾,也不愿意與自己在一起,現在又和自己說什麼無為憑?他就不服氣了,“那你既然做得他的妾,為何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為什麼?因為他不靠譜啊,陛下就算再怎麼不喜歡瑾王,但最起碼不會直接要了他的命,可是夏侯緋月不一樣,陛下一走,新皇登基,哪個都不會容下他,自己為何要與他一起死?
但是這些話,哪一句說出來都是大逆不道的,白蓮心也只能嘆氣,“你既然能說出這番話,那就仔細想想,我為什麼寧愿要給瑾王爺做妾,也不愿意追隨你。”因為就想活著啊。
Advertisement
可現在不但想活著,想要活得更好,不求能像是王妃那樣,為一顆熾熱的太,高照著這西南,但也求這一輩子不要碌碌無為。
不過說完這話,又添了一句,“我如今,不想與誰做妾,我只想做我自己。”
夏侯緋月卻是抓著不放,“做你自己?就是替他們做牛做馬麼?我都看到了,你在這府里過得并不好,這樣的下雨天,你還要進山去采摘野菜,府里這麼多人,難道就沒人使喚了,一定要你去麼?還有我都看到了,那沈羨之連裳都要你一針一線來,他們這樣對你,你難道就……”
這一次換白蓮心震驚了,滿臉驚詫地看著夏侯緋月,“你胡說什麼?這些我都是心甘愿做的。”天曉得,王妃今日穿著自己親手制的裳,是多麼高興。
怎麼到了這夏侯緋月的口中,竟然變了這樣?
但夏侯緋月不信,“你別騙我了,你是不是不想拖累我?”
白蓮心覺得,夏侯緋月八是有病,才會臆想這些有的沒的,只一把甩開他的拉扯,義正詞嚴道:“殿下雖是不順,但從未短缺吃,仍舊有人庇佑著,可我只是孤一個,我知曉那吃不飽穿不暖的日子是怎樣的。這西南如今在外名聲還一如從前,那殿下該知道,這里曾經是什麼樣子的,現在又是什麼樣子的?所以我敬重瑾王爺瑾王妃,我沒有別的本事,所以只能在這些小事上,盡自己的力,讓王妃過得好一些。”
說完,便頭也不回地轉走了。
夏侯緋月愣在原地,好半天才回想起這西南在外面的人口中,是何等的貧窮落后,大部份的老百姓都不蔽食不果腹。
可是如今城門雖破敗,但在修葺之中,所修建好的地方,堅如銅墻鐵壁,而破爛的街道如今鋪滿了青石板,街道兩旁的鋪子房屋都重新修葺過,來來往往的行人沒有面黃瘦,也沒有愁眉苦臉,小孩子們還都胖乎乎的,每日都有歡聲笑語。
他忽然有些說不上來心里是什麼覺,但總覺得口堵住了什麼東西一樣,卻又吐不出來,很是人難,只失魂落魄地從王府里出去。
街道人形來來往往,耳邊熙熙攘攘的賣聲和談話聲。
他最后找了間熱鬧的酒樓坐下來,耳邊聽著有人說要去清河縣承包山地種植棉花,順便養些高山綿羊,西南王府會有補,細算下來比種地要劃算些。
而且如果棉花和樣貌大賣,明年沒準就能大賺一筆了。
但是他的朋友卻勸說他去鲖縣做水果生意,說那邊一縣有四季,可從那里運果子經過古蘭縣送到這潯州城來,肯定好賣。
又有人說還不如老老實實種菜,反正蠻人們暫時沒打算遷移下山,他們山上只能狩獵,還是沒法種植蔬菜瓜果,到時候這市場開了,就專門賣這蔬菜瓜果,既不心,也不怕貨積,反正對方要多,再去給農戶們收購就好了。
然后還聽人說,孩子送去了日月書院里,家里的人們得了空閑,也去養場,或是到王府的菜園子里干活,反正家里又有銀子進賬,手頭寬裕了不,盤算著過兩年想辦法盤個鋪面,也做生意。
都是欣欣向榮,老百姓們對待著未來的生活都充滿了積極,沒有一抱怨。
這就是阿瑾哥所管理的西南王府麼?如果每一個州府都將如此,這天下又將是什麼樣子的?
甚至他還發現了一個很奇怪的問題,這潯州城沒有衙門,聽說刑事案件幾乎都是由日月神教那邊的刑罰堂理。
但是這麼大一個城里,都一天了,就沒有一件案子,著實他覺得詫異。
街上沒有驚馬,人人的鬧市也沒有小,那些還年的孩們,更無人販子敢手。
他有那麼一瞬間覺得,這里好得有些不像是真的。
還聽掌柜跟客人說,老家在某州,雖也是繁華熱鬧的大州府,酒樓里也是每日人滿為患,但還是打算勸著親戚想辦法搬遷到這潯州城來。
夏侯緋月離柜臺并不遠,聽得清楚,所以忍不住問,“你親戚和你有仇麼?既然他酒樓每日都客滿,又在大州府,為何還要勸他來此?”這西南如今是好,但比起他所說的大州府,還是差遠了,基礎擺在這里,沒有個幾十年,哪里追得上那個大州府?
掌柜的見他儀表不凡,只怕份也不低,所以有些不敢說實話,但轉頭一想這里是潯州城,怕什麼權貴?便道:“雖是客滿,每日所接待的也都是富貴王權們,可是這些哪個不是祖宗,有時候一兩個月不到,那欠下賬單上千兩,從不付現銀,我親戚又不敢上門去討要,只能吃了這啞虧,每月哪怕是客滿,可掙來的銀子,還不夠補這些空缺,往日還有那些喝醉了故意找茬的客人們打砸,桌椅碗碟,哪樣是不要錢?”
偏偏對方不賠償,這種小案子,衙門管一兩次后就不耐煩了,最多也就只是拉了人進去關今天大牢罷了。
過幾日放出來了,還來酒樓里打砸報復,真想要衙門里正經給他們治罪,還要往上面送錢。
這樣下來,每年還不知道倒多銀子呢!只能掙得一兩分面子,人看著面上風罷了。
可實際上,比那些普通老百姓都窮。
這就是沒有后臺背景的人開店。
夏侯緋月不由得想起自己上的賬單……王府尚且如此,打砸破壞的任何件都需要賠償,外面這些酒樓客棧,只怕亦是如此了。
這樣說來,此就算是客人只有那大州府的一半,那好像也會賺錢。
而且也無任何權貴賒賬一說。
他后來沒再說話,繼續坐在客棧里喝酒,送走一波又一波的客人,把客人們的夢想聽了一遍又一遍。
最后店家終于要打烊了,他拖著有些醉醺醺的步子從酒樓里回去。
踉蹌一步,險些要摔倒,卻被破軍一把給扶住,“殿下沒事吧?”
沒事吧?應該,夏侯緋月覺得。
第二天醒來,頭還有些暈乎乎的,白蓮心在房間里,聽著他醒來的靜,走了過來,沒好氣地將那粥放到旁邊的小桌上:“還熱著,你趁熱吃。”
夏侯緋月沒敢去看他,昨晚自己喝了那樣,一定很狼狽吧?
眼見著白蓮心出去后,他才端起這白粥,隨著黏稠濃郁的白粥口,胃里一陣暖意。
半個時辰后,他坐在夏侯瑾的書房里,“阿瑾哥,我想了很久,如果那個人是你,我可以傾盡全力來幫你。”自己的那些兄弟,誰上位了都不會繞過自己。
公孫府全是眷,可們都是將門之妻,手里的人脈,還是有那麼一點的。
“我沒有興趣。”夏侯瑾沒有抬頭,似乎一點都不意外他會來這里和自己說這些話。
夏侯緋月一怔,以為自己聽錯了又聽得夏侯瑾問道:“十七如何?”
“十七?”夏侯緋月不由得想起前陣子十七遞上去引得朝堂震的那封奏章,難道那個時候,阿瑾哥就決定了麼?但他卻搖著頭,“不可,他后沒有任何后盾。”寵這種東西,在權力面前形同虛設。
更何況大家都懂,父皇對十七母子倆為何好。
那份好,又有幾分真摯?倒是借著寵他們母子倆,懲治了不人,給十七母子倆樹敵不。
作者有話說:
猜你喜歡
-
完結108 章

白日提燈
賀思慕在戰場上撿人吃,沒成想被人撿回去了。撿她回去的那位少年將軍似乎把她當成了戰爭遺孤弱質女流,照拂有加。賀思慕于是盡職盡責地扮演著弱女子——哎呀血!我最怕血了,我見血就暈——水盆好重我力氣好小,根本端不動——你們整天打打殺殺,好可怕哦暗戀小將軍的女武將氣道:“段哥哥才不喜歡你這樣嬌滴滴的姑娘!”賀思慕一偏頭:“是麼?”某日少年將軍在戰場上馬失前蹄,被人陰了。肩不能挑手不能提見血就暈的賀思慕松松筋骨,燃起一盞鬼燈:“讓我來看看誰敢欺負我們家段將軍,段小狐貍?” 段胥想過,他不該去招惹鬼王。他花了好幾個月的時間才知道她的真名叫賀思慕。但是或許他用一生的時間,都不能讓她在她四百年漫長的生命中,記住他的名字。“我叫段胥,封狼居胥的胥。” —————— 日常裝柔弱超強鬼王女主*狡詐專兵少年將軍男主
33.9萬字8.46 26117 -
完結2059 章

獨寵太子妃
前世,她助他登上皇位,換來的卻是,被廢後位,痛失愛子,失去家人,被砍掉一雙腿。一覺醒來,她回到了十五歲那年,冷情冷心,封鎖了心門。某太子:“我丟了東西,你把心門鎖了,我怎麼要回?” “……” “我的心,丟在了你身上……”
282.4萬字8.09 186053 -
完結743 章

侯門醫女:我勸將軍要善良
被逼嫁給一個兇殘暴戾、離經叛道、罄竹難書的男人怎麼辦?顧希音表示:“弄死他,做寡婦。”徐令則嗬嗬冷笑:“你試試!”顧希音:“啊?怎麼是你!”此文又名(我的男人到底是誰)、(聽說夫人想殺我)以及(顧崽崽尋爹記)
127.2萬字8 52202 -
完結138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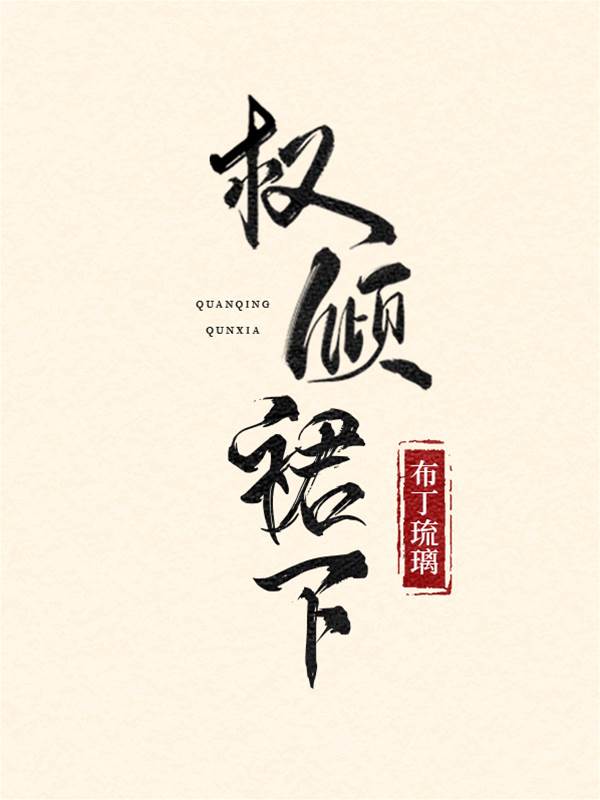
權傾裙下
太子死了,大玄朝絕了後。叛軍兵臨城下。為了穩住局勢,查清孿生兄長的死因,長風公主趙嫣不得不換上男裝,扮起了迎風咯血的東宮太子。入東宮的那夜,皇后萬般叮囑:“肅王身為本朝唯一一位異姓王,把控朝野多年、擁兵自重,其狼子野心,不可不防!”聽得趙嫣將馬甲捂了又捂,日日如履薄冰。直到某日,趙嫣遭人暗算。醒來後一片荒唐,而那位權傾天下的肅王殿下,正披髮散衣在側,俊美微挑的眼睛慵懶而又危險。完了!趙嫣腦子一片空白,轉身就跑。下一刻,衣帶被勾住。肅王嗤了聲,嗓音染上不悅:“這就跑,不好吧?”“小太子”墨髮披散,白著臉磕巴道:“我……我去閱奏摺。”“好啊。”男人不急不緩地勾著她的髮絲,低啞道,“殿下閱奏摺,臣閱殿下。” 世人皆道天生反骨、桀驁不馴的肅王殿下轉了性,不搞事不造反,卻迷上了輔佐太子。日日留宿東宮不說,還與太子同榻抵足而眠。誰料一朝事發,東宮太子竟然是女兒身,女扮男裝為禍朝綱。滿朝嘩然,眾人皆猜想肅王會抓住這個機會,推翻帝權取而代之。卻不料朝堂問審,一身玄黑大氅的肅王當著文武百官的面俯身垂首,伸臂搭住少女纖細的指尖。“別怕,朝前走。”他嗓音肅殺而又可靠,淡淡道,“人若妄議,臣便殺了那人;天若阻攔,臣便反了這天。”
52.5萬字8 22512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