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娛樂圈私密日記》 第五十二章 復仇計劃
一路上也沒再說話,逸雯爸爸聯系的醫生要明天才上班,所以我們還是直接回了家。到家門口時我看爸爸并沒有留下我的意思,逸雯也沒看我就進去了。所以我和金的朋友一起離開了。金他們還是在那家常去的街邊攤,我們趕過去的時候滿桌的菜幾乎沒怎麼,已經涼了,啤酒倒是喝了不。
我到了之后氣氛更加沉悶,都知道我心不好,其實誰心都不好。悶頭喝酒,我越喝越覺得心里委屈,明明知道有問題,就是控制不住!喝著喝著,眼淚就落下來,掉到酒杯里。
“我早就說他是個騙子,就是不聽我的!我他媽白天要是不說分手一直守著就不會發生這事了!”
哥拍我的肩膀,“別自責了,已經這樣了,誰也不是故意的。”
“可是我***憋屈,連報警都不能報,看著那王八蛋逍遙。”
金搖晃著他那瘦的像木似的胳膊:“不能報警又沒說不能搞他?咱找人整他一頓不就好了!”
“對!對!”好幾個人都應和著。從小咱就是老實孩子,這方面沒什麼經驗,但我是事主,毫不能落后。于是用力的點點頭,“干他!”
這時一直沉默的小珊的男朋友小劉說話了,“我覺得咱整他一頓也沒多大意義。”
金狠狠的瞪了他一眼:“你是他朋友才覺得沒意義吧!”
小劉尷尬的臉都紅了:“我不是那個意思,我和他并不,才認識沒多久!而且這次連我朋友也差點掉進去。”
我示意金別沖,“大家都心不好,你也別誤會,那你說說怎麼才能有意義。”
“我覺得你打他一頓最多也就是點皮外傷,以后他還是逍遙法外,繼續騙人害人!咱最好想辦法揭穿他的本質面目,最好把他搞到監獄里去!”
“我也想,但是怎麼弄?又不能報警!”金沒好氣的說。
小劉四下看了看,太晚了,附近本就沒人,老板都躺在躺椅上睡著了,他還是低了聲音說:“你們要是真想干我倒有個想法。”
我們都沒有頭緒,而且和張目都不認識,即使揍他一頓也要靠小劉幫忙找人。所以都豎起了耳朵聽著。
“前段時間張導開辦了一家藝人培訓班,就在新界那邊,我去過一次,當時說讓我去幫忙的,但又不提給薪水,所以我就婉拒了。本來說明天給們幾個孩子試鏡也是去那。要沒今天的事我也沒大注意,現在想想那里肯定有問題。第一,蔽。在一家寫字樓后面的小胡同里,我去的時候里面明明有人卻鎖著門,我進去之后又把門鎖上。一個培訓班不應該這樣吧。第二,那培訓班只招孩子,這個也奇怪吧?是張導親口對我說的。第三,那里面我并沒看到什麼教學用品,連一本正規的表演教材都沒看到,不過攝像材卻很齊全。”
“你是說他利用培訓班的名義騙孩子?”我們都聽出了門道。
“我只是今晚的事之后覺不對勁兒。”
“說說你的計劃。”
他又疑神疑鬼的四下看看才說:“我的計劃就是我們想辦法盯著那里,看能不能發現什麼問題,一旦發現了我們就報警抓他!就算沒構坐牢的罪也把他的生意攪了。”說完他惡狠狠的咬了咬牙。
我們不約而同的點了點頭,“通過!”“就這麼干他!”其實現在也沒有別的想法,而且這個也還是很有可行的。以張目的為人,再按照小劉的說法那地方那麼神一定有問題。多半是個騙迫害孩子的基地。
第二天我們幾個跑去勘察了一下地形。確實如小劉所說,那小胡同連汽車都開不進去,只有一個小門,地關閉著。我們四下轉了轉,那地方太蔽了,實在不好窺探。胡同的另一面倒是一座小樓,位置很不錯,但進去問了問本沒有房間出租。最后我們在胡同口對面的三樓租了個小房間,斜斜的能看到那個門口和一扇小窗。雖然不是很清晰,但也算蔽了。
我和哥兩個大閑人當天就住了,小劉是學攝影的,還弄了臺高變焦的相機和一個小遠鏡。而我則采購了些生活必需品扛上去,礦泉水啤酒速食面,面包火腸。準備長期作戰。
我和哥兩個人是主將,白天一邊監視一邊閑聊,誰累了誰休息,晚上金也會過來,每人兩個小時。小劉閑下來也會過來幫忙,他們倆的朋友沒事的也來湊熱鬧。幾乎每天都有好多人,倒也不寂寞。
我舉著遠鏡的時間要多一點,畢竟關心。第一天沒什麼,那扇門始終沒開過,也沒人來。我用遠鏡試著窺探了下鐵門上面的那扇窗子,角度不好,只模模糊糊的看到一條窗簾。門不用一直盯著,我也是閑著無聊,沒事的時候就那扇窗。
開始的時候那窗簾一不,一次我剛把遠鏡對正就看到窗簾了。里面有人!過了好一會兒,窗簾拉開一條隙,一直男人的手出來把窗戶也打開了一條。能模糊的看到一個人影站在窗前,不一會兒,一縷煙從窗口的隙飄出來,那家伙在煙!看來他也是閑著無聊。
大約十分鐘,那只手又出來關上了窗子。那個人影也消失了,之后就再也沒出現過,不過那窗簾的隙始終開著。
一直到傍晚的時候,我正躺在床上看哥和兩個朋友打牌,剛接班不就的金續突然喊了一聲:“來人了!”
我立刻從床上跳起來趴到窗前,向窗外看去。只見一輛商務車停靠在胡同口,“那王八蛋的車?”
果然,車門打開,“冒牌導演”張目那臃腫的影從駕駛座跳下來。我舉起照相機調了調焦距,那家伙油亮的臉出現在鏡頭里。“媽的!”我低低的罵了一句,恨不得沖過去狠狠的在他臉上來幾下!哥拍了拍我后背,似乎在安我別沖!這點我還是忍得住的。
那家伙打開后車門,提了一大包快餐出來,又拿出另一個塑料袋,里面似乎裝的飲料啤酒水果之類的東西。他鎖好車,又警惕的四下看了看,才溜進胡同。站在門前沒有敲門,而是拿出手機打了個電話。過了一會兒鐵門才打開,但只開了可供一個人進出的,看不見里面的人的樣子。張目又警惕的兩邊看了看,才鉆進門。他看向我們這邊時,我看到他的目一閃。我以為他發現了我們,趕向后側,躲在窗簾后面。
金續沉著:“看來真有問題啊,你看那混蛋的警惕勁兒。”
我點了點頭,“里面肯定有見不得人的勾當。”
“看那王八蛋那德行!咱去把他的車砸了怎麼樣?”后一個朋友說。
我連忙制止:“別,那樣就打草驚蛇了。”
朋友嘿嘿的笑著,“我就是想解解恨!”
大約就五分鐘的樣子,鐵門又開了,那混蛋導演張目出脖子,兩邊看了看才扭著屁出來。扭搭著上車離開了。
天黑下來,第一天就這麼過去了。晚上我們三個倒班盯了一晚上,也沒看到什麼特別的現象,那扇門一直閉著。倒是那扇窗子里亮了燈,到半夜才熄掉,然后一直黑乎乎的。
第二天一早我請了會假,到逸雯家看了看。爸爸媽媽都在,還有閨。閨真是一種很不尋常的關系,有時會比親姐妹更親近。我去的時候正靠在沙發上假寐,臉格外蒼白,看來也沒休息好。
逸雯爸爸客氣的讓我坐下,逸雯臥室的門閉著,我挑了挑臉,爸爸點了點頭,長嘆了一聲:“一直在里面,到現在都沒好好吃飯!要不是小姐妹一直陪著,我都不知道該怎麼辦!小吳也要謝你,一直忙前忙后的,幫了這麼多忙!”
我沒說話,呆呆的看著那閉著的米黃的房門。那里面曾經關著深深令我沉醉的溫!但現在卻死一般沉寂!而且我現在心有些不知該怎麼面對了!“不,我不會,對不起!我不能放棄。”的話還在耳邊,還是像一把刀子一般刺著我的心。而在酒店房間里剛看到痛苦的影子時我的心出了憤恨痛苦之外還有很多憐憫。唯獨沒有多!像我這樣的人那還會有呢?那天我生氣在的理想面前是那麼脆弱,但現在看來我的也不是很經得起考驗。至的不幸也沒換來我復合的!并不是因為的失節!
我凝著那扇門令閨誤會了,以為我想見見逸雯。起走進房間,是去問逸雯吧。我心里立即有些張,想見,卻又有些抵!不知道該說什麼。過了一會兒閨就出來了,對我憾的搖了搖頭。“抱歉小吳,不想見人。”
我松了口氣,這樣也好,“沒事,沒事。”我轉向逸雯爸爸,“伯父,真不準備報警了?”這句話問的有些多余,要報警早就報了,而且現在已經超過有效時限了。
逸雯爸爸搖了搖頭:“不報了,我們就希逸雯好好的,這孩子從小就單純!我們一直像掌上明珠一直護著,還不知道這一關能不能過呢!”說著他的眼睛就潤了,媽媽也開始流淚啜泣。我也默默的祝福,希能闖過這一關,盡快好起來。
猜你喜歡
-
完結48 章

霸上嫂子
小說的主人公是楊浩和沈思慧,此書主要講述的是在哥哥不在家的時候,楊浩與自己的美豔嫂子沈思慧之間發生的那些事,楊浩對沈思慧早就有著非分之想了,恰巧碰上這一次千載難逢的好機會,他會如何呢?
4.3萬字7 374334 -
完結265 章
穿進肉文被操翻了怎麼辦
(全文終,結局1v1。本文各種天雷滾滾、瑪麗蘇、肉到吐請自帶粗長避雷針)女大學生薛知曉有個小秘密,就是夜深人靜的時候躲宿舍被窩裡如饑似渴的看肉文,並把自己代入女主。。結果自己掉進看過的肉文各種各樣的play裡。。。 ========================================================= 人前知性賢慧、聰明能幹的大學學生會主席薛知曉,內心卻極度悶騷極度性饑渴。 走在路上,視線會瞄向男人下體,想像這個強壯帥氣的男生被自己的美色誘惑,雙眼泛綠光的把她就地撲倒,撕爛她的衣服並把大雞巴捅進她滴水饑渴的淫穴裡頭。。。 因緣際會,她終於得償所願被投進了一部又一部她無數個深夜裡擼過的肉文裡頭,過上她渴求的沒日沒夜和各類帥哥型男各種啪啪啪、幹得她淫水直流爽上天的日子。。。 然而,這些日子她只想存在於她的性幻想裡頭,並不想成為其中的女主角被這樣那樣的狠狠操翻啊親~~~~~~~ =================================
26.7萬字5 329650 -
完結614 章
快穿之【枕玉嘗朱】
此為快穿之[玉體橫陳]第二部,單看並不影響閱讀,大家也可以選擇補一,也可選擇直接看二哦~要看第一部在下方連結 黎莘作為一個被砸進快穿系統的OL, 執行的任務就是破壞原著劇情,勾搭男配男主。 經歷了系統1.0的折磨(誤),黎莘自認已經養成了百毒不侵的體質。 然而一次解密世界,卻將她置於兩難境地。 為了解開最後的謎團,她躊躇滿志的面對全新的挑戰,然而係統無情的告知,這一次,她不僅要得到攻略人物們的身,還要得到他們的心…… 已完成CP: 正在進行時CP:【穿書•現代篇】心有明月 (偽白蓮腹黑大小姐×面癱呆萌鬼畜殺手by萬俟月醴) 預告: 黎莘是紹澤煬心中的白月光,是他可望而不可及的夢中情人。 當她因黎家人的過失意外故去後,紹澤煬瘋魔了。 他囚禁了與黎莘有七分相似的黎妤,親手毀去黎家家業,並從此走上與黎妤相愛相殺,虐心虐身,你追我趕的道路。 ——對此,黎莘只想表示。 (豎中指) 沒錯,她穿書了。 穿到了一本
48.5萬字8.43 210360 -
完結50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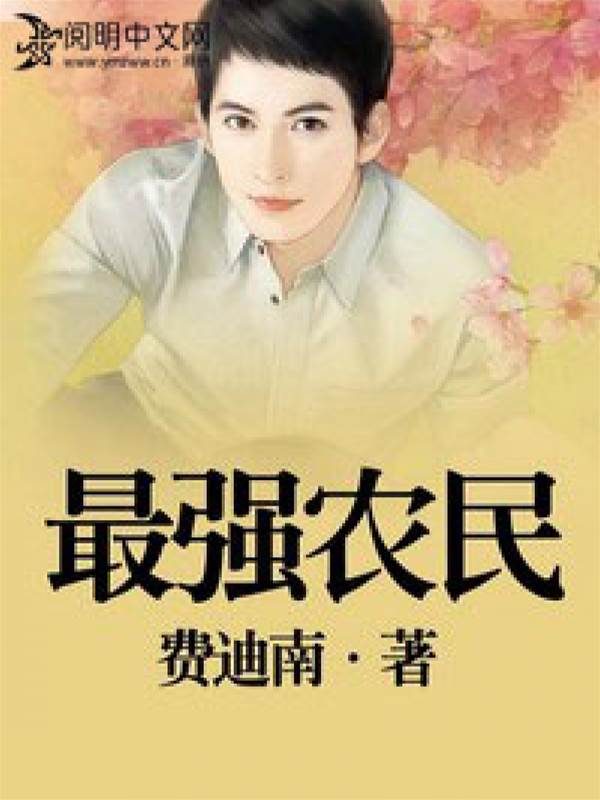
最強農民
作為世界上最牛逼的農民,他發誓,要征服天下所有美女!
14.3萬字8.18 12613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