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嫁/公府長媳》 第55章 第 55 章
蕭元朗將碟子傾倒干凈, 擱在花壇邊一個小簍子旁, 自有人來收,他輕輕拍了拍手上灰塵,正覺外頭風太大,打算轉回去, 只見燕翎立在廊廡高柱側, 墨的鶴羽襯得他長玉立,氣度威儀。
蕭元朗微愣了一下, 從容折回臺階,來到廊蕪下朝燕翎施禮, “請世子安。”
燕翎視線與他相, 蕭元朗神分外平靜, 談不上溫和, 談不上冷漠, 也沒有半分被抓包的尷尬。
燕翎默了片刻, 拱手朝他行了家禮,
蕭元朗眸微微一挑,連忙避了一下, “世子尋在下可有事?”
蕭元朗是敏銳之人,燕翎不可能無緣無故等在這里。
燕翎頷首,神變得有幾分復雜,“上回子拜請表兄幫忙, 燕翎今日特此道謝。”
蕭元朗聞言角微微溢出一抹苦笑,這哪里是來道謝的, 是來宣示權利的。
他神含笑, 眼底的冷淡一瞬間散去, 慢慢浮現一抹潤無聲的謙和來, “世子客氣,我母親總是憐惜寧三表妹孤苦,那一夜下人稟報來訪,母親二話不說吩咐我幫三表妹跑一趟,遵母命而已,況且,我雖與表妹不,到底是至親骨,有用得上我的地方,自然在所不辭。”
三言兩語告訴燕翎,他是因為母親吩咐才幫寧晏,他與寧晏不。
蕭元朗的話并未讓燕翎好半分,他若還不清楚是怎麼回事便是傻子,無論他介意與否,蕭元朗曾與寧晏有他不知的過去是事實,或許只是不經意的淺笑,或許只是舉手之勞的一次照拂,但凡這些在心里滾過一遍,都是不好的。
原先崔玉等人常常在他面前嘮叨男之事,他心中嫌棄至極,而今自己親經歷,才懂得個中滋味。
Advertisement
他燕翎也有今日...
他再次施禮,旋即轉回了廳堂。
尚在門檻,便聽得里面傳來幾道朗笑聲,有些陌生,卻又不完全陌生,燕翎猜到是自己那位岳父回來了。
寧晏的父親寧三老爺姍姍來遲,寧老爺子正在當庭呵斥他,直到燕翎進來,才止住話頭,燕翎看了一眼寧三老爺,一修長的白袍,頗有幾分疏狂之風,原還氣勢與寧老爺子辯駁,這會兒瞧見燕翎,嗓音戛然而止,愕然地愣著。
燕翎朝他行了家禮,寧一鶴回過神來,冷淡又尷尬地應付了一下。
遙想當年燕翎隨國公爺來寧府,寧一鶴以為他是要娶寧宣的,與他相談甚歡,如今了自己婿,反而不說話了。
他不喜寧晏,沒對上過心,自然也沒想過去沾的,前幾日在茶樓遇見幾位同僚,有人提起燕翎娶了寧氏,問他是哪位,被寧一鶴含糊過去。
寧一鶴不搭理他,燕翎也不會去湊趣,寧晏從未與他提過寧一鶴,可見父倆有多差勁,不對,這一會兒燕翎忽然意識到,寧晏從未與他提過寧家,也不曾告訴他,在寧家過得好與不好。
他不僅不知道的過去,甚至連生活習都不知曉。
燕翎坐在圈椅里,心中五味陳雜,一時便有些走神。
翁婿二人因為份的緣故坐得近,卻又如同陌人,
反倒是寧大老爺時不時與燕翎搭訕,三皇子也偶爾一句,場面不至于冷清。
寧老爺子在這樣的場合,手里依然擰著一只鳥籠,里頭攀著一只金雀偶爾細細啼幾聲,眾人心有嫌棄卻無人敢說什麼,寧老爺子也不在意晚輩的看法,問起燕翎國公爺最近閑暇與否,他要尋國公爺去釣魚遛鳥。
燕翎對他老人家倒是溫和,耐心回答他。
末尾老爺子忽然笑問道,“晏丫頭沒給你添麻煩吧?”
燕翎聽了這話,心中忽然一頓,竟有些無從說起,新婚夜是他怠慢了,后來種種兩人從陌生到如今心意相通,過多壁,又有多艱難,不足為外人道,在這慢慢融洽的過程中,有一條始終沒變,寧晏最初如何悉心照料他,如今亦然,倘若現在回到大婚那一夜,他定不會失約,哪怕先去探外祖母,回了明熙堂也不會再離去。
紛繁復雜的緒涌上來,最后匯一句,“很好,特別好。”
屋子里眾人都跟著愣了一下。
寧老爺子卻是笑容不改,漆灰的眸眼藏著幾分看世間滄桑的灑,“呀,外表溫順,子卻倔得很,看著事事周全,實則極有事能的心,以后但有怠慢,還世子多多海涵。”
燕翎清雋的眸子慢慢凝聚一抹灼然,并沒有把老爺子的話當回事,寧晏怎麼可能怠慢他,不會。
寧晏帶著如霜與如月進側廳的眷席中,居然看到了父親的妾室蓮姨娘。
自小最厭惡二人,便是蓮姨娘與其寧溪,這對母在出嫁之前的十六年,想盡法子對付,雙方便如針尖對麥芒。
吃驚的是,這樣的場合,寧家居然讓一個妾室坐在席中,寧晏臉便垮了下來。
冷冷淡淡看了一眼坐在上座的祖母,草草施了一個禮,老太太原本念著燕翎位高權重,想要給寧晏一回好臉,見寧晏如此態度,眉頭也跟著皺了起來。
蕭夫人笑著朝寧晏招手,示意坐過去,寧晏也不好無緣無故怒,便挨著坐下,蕭夫人告訴寧晏,年前送的那幾匹香云紗極好,今日正好穿了一件,兩個人便聊起做裳的料子,寧晏今日上披著那件孔雀翎,惹得寧家幾位姑娘頻頻扔來驚艷又艷羨的眼神,后來四小姐寧溪實在忍不住了,酸溜溜問道,
“姐姐,你這件孔雀翎可好看哩,我聽人說淳安公主也有一件,公主視你為摯友,該不會是公主賞賜的吧?”
寧宣就坐在寧溪旁,二人自小合伙算計寧晏,但寧宣骨子里瞧不上寧溪,這會兒癟癟不告訴真相,等著看出丑。
寧晏原先不得不應付蓮姨娘母,如今已不在一個屋檐下,本不可能委屈自己與這等嫌惡之人搭腔,只與蕭夫人說,“是我鋪子里從蘇杭得來的好貨,姑母喜歡,回頭我再遣人給您送幾件。”
蕭夫人哪里是真要,笑著回,“上回送的還沒用完,對了,開年我們府上請酒吃席,回頭你得空過來玩。”寧晏應下了。
寧溪被晾得徹徹底底,頓時有些傻眼,面子上掛不住,便惱怒道,
“三姐,我問你話呢。”
站在寧晏側的如月已蓄勢許久,俏生生開了口,“四小姐,沒瞧見我們夫人正與姑說話呢,您是晚輩,怎麼能無緣無故呢。”
寧溪平日派頭在寧家等同嫡,被一個丫鬟兌,越發了怒,“放肆,我與你主子說話,哪有你的份?你們燕家是這樣沒規矩嗎?”
如月就等著這句話,皮笑不笑,“哎喲,還請四小姐見諒,我們燕家規矩極大,平日別說丫鬟不能在主子跟前話,便是妾室也從不出院子門,到了寧家,奴婢瞧見蓮姨娘坐在此,只當寧家是不論這些規矩的,是以一時失了分寸,還四小姐見諒。”
如月以前哪有這等膽啊,現在不一樣了,可是閣老夫人的一等侍,旁人家的庶看到還要客客氣氣,寧溪算哪蔥?
寧溪被這話給堵得面發綠,虎著臉正想回斥,蓮姨娘按住,著腰弱弱站了起來,含著淚道,“老太太,是妾的錯,原本念著今日是好日子,想給諸位主子們請安,老太太憐惜妾懷著孕,擔心下雪路,就吩咐在此用膳,不想被三姑娘如此嫌棄....”
如月那番話何嘗不是打老太太的臉,老太太面鐵青,看著蓮姨娘隆起的小腹瞇起了眼,前不久有一道姑看相說蓮姨娘懷的是男胎,老三快四十了,膝下還沒個兒子,老太太心里急,這回得了道姑的話,越發把蓮姨娘放在手心里疼,甚至許了一旦誕下兒子便扶正的話。
老太太不能發作寧晏,還不能料理一個丫鬟麼,當即寒聲吩咐嬤嬤,“將這個以下犯上的婢拖出去。”
“我看誰敢?”冷風拍打著明亮的軒窗,寧晏清越的嗓音不輕不重住這片戾氣,
慢悠悠將茶盞放了下來,含笑看著老太太,“祖母,若今日要論尊卑上下,孫可以陪祖母好好說道說道。”
老太太深深與寧晏相視,這些年蓮姨娘母做下的事,確實稱得上以下犯上,想起隔壁坐著那位,權衡一番利弊,眼底的怒慢慢收了起來,默了片刻,直截了當道,“來人,小心扶著蓮姨娘回房。”
寧溪不可置信,漲紅著臉,期期艾艾著老太太,“祖母....”
一旁的二夫人方氏撂了個狠眼神給寧溪,示意閉。
蓮姨娘看了一眼寧晏,委委屈屈離開了。
寧晏太清楚老太太的脾,從不是這麼容易低頭的人,總覺得有些不對勁。
宴席過后,寧晏匆匆要告別,果然被老太太攔住,
“晏兒,祖母還有事待,你跟我過來。”
老太太去到隔壁廂房坐著,寧晏只得隨過去,進去時,大夫人與二夫人皆在,而二夫人方氏邊還有一個亭亭玉立的,寒天雪地的,只穿了一件對襟的水紅褙子,褙子剪裁十分得,將那玲瓏段勾得楚楚人,生得弱貌,怯怯地瞥著寧晏,自是三分嫵,四分妖嬈,還有幾分我見猶憐。
但凡是個男人看一眼,骨頭都能給了去。
寧晏只消一眼便知葫蘆里賣了什麼藥。
鐵定是上回寧宣在這里吃了虧,氣不過攛掇著老太太玩這些把戲,而老太太呢,眼見燕翎閣,而不好控制,便使了這等險的招兒。
寧晏心里門兒清,八風不坐了下來,“祖母有何吩咐?”
老太太臉寡淡,帶著命令式的口吻道,“你過門這麼久,肚子也不見靜,祖母憐惜你孤苦,特意挑了一個人來幫襯你。”
朝二夫人使了個眼,二夫人立即接過話茬,“這是我從揚州帶來的姑娘,樣樣出眾,你若能得世子心是最好,若不能,也有給你固寵,絕不旁人搶了你風頭去。”
如霜在一旁聽著,角搐著,險些沒咬出一口來。
打著冠冕堂皇的旗號,干著最險的勾當。
掐著手帕,只期主子能想法子回絕了去。
寧晏面上沒有半分波,淡淡看著二夫人,“揚州來的?”揚州出瘦馬,而老太太的娘家也在揚州。
二夫人眼神微微瑟了下,“自然是的....”
年前三皇子出事,寧家被迫舉辦壽宴,寧宣便與老太太訴苦,讓老太太治一治寧晏,老太太便想了這個法子,吩咐從老家挑個可信好拿的人回來,二夫人心里記恨老太太與大房的人,總是讓做這些見不得人的勾當,暗自又琢磨著,既是給燕翎當妾,若哪一日生下一兒半,也是個靠山,故而水不流外人田,將自己的表侄打扮一番,偽裝揚州瘦馬送了來。
此事只有與侄曉得,老太太與大夫人皆不知。
寧晏與這些牛鬼神蛇打道十幾年,又怎麼不知們的底細,面龐如水地頷首,“,多謝祖母與二伯母好意,人我收下了。”
如霜與如月一聽傻眼了。
老太太也微微愣了下,原以為寧晏要掙扎一番,甚至連說辭都準備了幾套,還打算拿老爺子來,寧晏竟然這般乖巧聽話?是有什麼計倆,還是著實在燕家遇到難關?
寧晏笑看著老太太,解了心中的疑,“前段時日燕家二房的嬸嬸也打算給世子安排侍妾,孫琢磨著與其用旁人還不如自家人來的可靠,我想,以祖母之能必定挑個好拿的,如此我也省事了。”
猜你喜歡
-
連載2084 章
王妃又逃跑了
天才醫學博士穿越成楚王棄妃,剛來就遇上重癥傷者,她秉持醫德去救治,卻差點被打下冤獄。太上皇病危,她設法救治,被那可恨的毒王誤會斥責,莫非真的是好人難做?這男人整日給她使絆子就算了,最不可忍的是他竟還要娶側妃來噁心她!毒王冷冽道:「你何德何能讓本王恨你?本王隻是憎惡你,見你一眼都覺得噁心。」元卿淩笑容可掬地道:「我又何嘗不嫌棄王爺呢?隻是大家都是斯文人,不想撕破臉罷了。」毒王嗤笑道:「你別以為懷了本王的孩子,本王就會認你這個王妃,喝下這碗葯,本王與你一刀兩斷,別妨礙本王娶褚家二小姐。」元卿淩眉眼彎彎繼續道:「王爺真愛說笑,您有您娶,我有我帶著孩子再嫁,誰都不妨礙誰,到時候擺下滿月酒,還請王爺過來喝杯水酒。」
352.4萬字8.17 497707 -
完結777 章
玄醫梟後
青南山玄術世家展家喜添千金,打破了千年無女兒誕生的魔咒。 滿月宴上言語金貴的太子殿下一句「喜歡,我要」,皇上欣然下旨敕封她為太子妃。 這位千金從出生開始就大睡不醒,一睡就是三年。都傳是因為她三魂七魄隻覺醒了命魂,是名副其實的修鍊廢物。 不但如此,這位千金還被展家給養歪了,是紈絝中的翹楚。沒有修為但各種法寶層出不窮,京城中金貴公子沒被她揍過的屈指可數,名門閨秀見到她都繞道走,唯恐避之不及。 所有人都不明白,生在金玉富貴堆、被展家捧在手心裡長大的千金小姐,怎麼就養成了這幅模樣,都很佩服展家「教女有方」。 展雲歌,玄術世家展家的寶貝,玉為骨、雪為膚、水為姿,名副其實的絕世美人。出生以來隻喜好兩件事,看書、睡覺,無聊時就去鞏固一下自己第一「梟」張紈絝的名頭。 南宮玄,華宇帝國太子,三魂七魄全部覺醒的天才。容貌冠蓋京華、手段翻雲覆雨、天賦登峰造極、性子喜怒不形於色,嗜好隻有一個,就是寵愛他從小就看入眼的人兒,從三歲開始就勵誌要在她的喜好上再添上一個南宮玄。 自從展雲歌知道自己滿月時就被某太子貼上屬於他的標籤後,就發誓,既然這麼完美的男人,主動投懷送抱了,而且怎麼甩也甩不掉,她自然是要把人緊緊的攥在手心裡。 世人皆知她廢材紈絝,隻是命好投胎在了金玉富貴頂級世家裡,唯獨他慧眼識珠,強勢霸道的佔為己有。 「梟」張是她前世帶來的秉性。 紈絝是她遮掩瀲灧風華的手段。 看書是在習醫修玄術,睡覺是在修鍊三魂七魄。 當有一天,她的真麵目在世人麵前展開,驚艷了誰的眼?淩遲了誰的心? 心有錦繡的世家貴女展雲歌和腹黑奸詐的聖宇太子南宮玄,在情愛中你追我逐,順便攪動了整片大陸風雲。 他以江山為賭,賭一個有他有她的繁華盛世。 --------------------- 新文開坑,玄幻寵文,一對一,坑品絕對有保證!陽光第一次這麼勤奮,昨天文完結,今天就開新文,希望親們一如既往的支援陽光,別忘記【收藏+留言】外加永不刪除。 推薦陽光的完結文: 絕品廢材:邪尊的逆天狂妃:玄幻 婿謀已久之閑王寵妻:古言、架空 浮世驚華之邪王謀妻:古言、架空 霸道梟少狂寵妻:現代、豪門 絕戀之至尊運道師:玄幻
213.4萬字8 68793 -
完結781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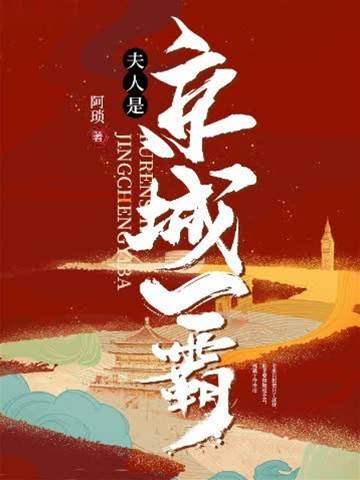
夫人是京城一霸
七姜只想把日子過好,誰非要和她過不去,那就十倍奉還…
123.2萬字8 19066 -
完結687 章

腹黑萌寶神醫娘親惹不起
【本書又名《我假死後,冷冰冰的王爺瘋了》假死追妻火葬場後期虐男主白蓮花女主又美又颯】一朝穿越,蘇馥竟成了臭名遠昭醜陋無鹽的玄王妃,還帶著一個四歲的拖油瓶。 玄王對她恨之入骨,要挖她的心頭血做藥引,還要讓她和小野種為白月光陪葬。 她絕處逢生,一手醫術扭轉乾坤,將日子過得紅紅火火。 一心盼和離時,誰料玄王卻後悔莫及。 曾經冷冰冰的王爺卑微的站在她身後「阿馥,本王錯了,你和孩子不要離開本王,本王把命給你好不好?」 等蘇馥帶著兒子假死離開后,所有人以為她們葬身火海,王爺徹底瘋了!
67.5萬字8 104152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