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嫁/公府長媳》 第45章 第 45 章
這是一道名為“山河盛宴”的軸大菜, 用一條重達二十斤的碩大鱖魚為底,頭尾煎翹型,如一幅巨畫徐徐展開, 那掌勺之人巧思妙工, 以魚脊為梁,將那魚腹勾勒出山河阡陌之狀,再輔以用刀工雕刻的蔥蒜,豆腐, 蕨菜之類,形一副壯麗的山河圖。
這還不是讓皇帝驚訝的地方,真正撼皇帝的是這幅圖的寓意, 也不知那掌勺之人是妙手偶得,還是當真有閱過那自泰西傳來的堪輿圖,此圖以大晉為天下之中,雕刻出附屬諸國之狀, 旁人或許不曉得,但落在皇帝與諸位使臣眼里, 這便是萬國朝貢之景,十分壯麗。
更有可圈可點之, 便是那魚四周用蓮藕,馬鈴薯,蘿卜之類雕刻出形態各異的人偶, 有八仙過海,有山海鬼神,形態真, 那魚尾更有用蘿卜切的水簾, 可瞧見那尾里藏著一活靈活現的猴兒, 彰顯泱泱大國之底蘊。
這哪里是一道菜,分明是大晉的華天寶,天國氣度。
使臣們嘆為觀止,嘖嘖稱奇,大晉朝臣更是引以為傲,拍案絕。
這才軸大戲。
皇帝心的震撼無以言喻,一屆小小廚竟有如此之懷眼界,能用一道菜繪聲繪描繪出中原文典章,震懾住這些野心的夷邦,可謂是“簡在帝心”,他一定要將此人留在皇宮,專司國宴。
這麼一道可堪稱盛宴的佳肴,誰也舍不得筷,總歸是用來吃得,吳奎請示了皇帝,皇帝雍容含笑,點了太子,“你替朕取第一勺來。”
又吩咐燕翎,“你便替諸國使臣分食。”
燕翎與皇帝換了個眼,猜到皇帝用意,起來到食車旁,侍用紅漆盤捧著銀勺與碗筷侍候在側,燕翎一面等著太子替皇帝取,一面近距離觀賞這幅“山川輿圖”,這廚竟是如此工巧妙,將那些藩國點綴其中,他一貫不在吃食上費心,今日卻不得不為這道菜折服。
Advertisement
待太子取完魚頭下的一塊送與皇帝,燕翎特意將那代表附屬諸國的魚給挖下來,贈予諸位使臣,使臣心知肚明,此刻卻也心服口服接了這道菜,待那魚口時,更是目,都顧不上使臣禮節,捧起碗直往食車前奔,
“不勞世子大駕,我等自己手。”
有一便有二,片刻那食車四周聚滿了人,能讓使臣豁下面奪食,可見這道魚味道奇佳,朝臣也耐不住子,爭相上前自取。
燕翎反倒被去一旁,他早就酒足飯飽,也不屑于與眾臣搶奪一口魚食,便退回了席位。
這已經是崔玉第三奔向食車了,沒法子,他就好一口吃的,況且他在那點魚湯中嘗到了明宴樓的味道,可惜奪食之人太多,他無暇細想,第三進去時,碩大的瓷盤里只剩下零星幾塊做人偶的藕片蘿卜,再小的蚊子也是。
崔玉將那截蓮藕,與那片蘿卜給夾在了碗里,路過燕翎席位時,瞥見他盤中空空如也,再瞅了一眼碗里,踟躕再三,將那截蓮藕夾給了他,
“好歹是膳房年度魁首,吃不到魚,一口魚也是的。”
那截褐的蓮藕沾了滿滿的魚。
燕翎并不在意,也未拂了崔玉好意,漫不經心夾起那截蓮藕,往里一送,蓮藕極脆,又夾雜了魚里的鮮,嚼在中,就如飲了一杯爽口的青梅,角不自擒著一抹滿足,就連眼尾也拖曳出幾分怡然自得的愜意來。
寧晏穿著那宮裝,跟在韓公公與掌膳后來了天星閣,悄悄躲在甬道之,過珠簾靜靜注視著那道菜,見皇帝與眾臣贊不絕口,這才長長吁了一口氣,
左膳使原打算做一道魚躍龍門的大菜,回想曾跟隨外祖父瞧見那泰西傳來的萬國輿圖,一時心,便做出這番構想,別看平日做事四平八穩,一旦上了灶,便十分膽大,挑戰難度極高的大宴,當那條魚擺在面前時,腦海便是勾勒出這樣的畫卷來,幾乎是不假思索便了手,待做完整道菜,自個兒都出了一冷汗,甚至有些后悔,過于冒險了。
眼下瞧見殿歡聲如雷,大家吃得熱火朝天,爭相奪食,欣然一笑,哪怕回去被燕翎罵一頓,也值了。
宴席接近尾聲,寧晏與韓公公如釋重負一笑,又在韓公公掩護下,悄然退去延慶宮換裳。
彼時吳奎手下一名得力干將已將事始末查出,吳奎聽得那名諱,一口茶嗆在里,險些噴出來,
“你說什麼?你沒誆我?”手肘里擱著的拂塵了下來,白皙的尾掃在地上,那小使不慌不忙將拂塵拾起,拍了拍灰塵,又恭敬遞給吳奎,“千真萬確。”
吳奎深深吸了一口氣。
皇帝已退到天星閣側殿歇息,留下百陪著使臣豪飲,燕翎擔心寧晏,打算與皇帝告罪先去后宮接了出來,將人送回去,這會兒剛走到側殿門口,隔著一扇嵌翡翠的紫檀座屏,聽到里面傳來“寧氏”二字,眸微的閃爍了下,腳步頓住。
吳奎這廂也是滿頭大汗,氣不勻,“陛下,那山河盛宴當真出自世子夫人寧氏之手,”他語含三分不解,三分吃驚,余下還有幾分折服。
皇帝眼中驚迭起,當真被嗓中殘余的酒氣嗆住了,猛地咳了幾聲,
“怎麼可能?”
吳奎苦著臉,“人家擔心出岔子,剛剛還跟來了天星閣,奴婢悄悄窺了一眼,那走路的儀態,神,嘖嘖,哪里是明宴樓的廚子,分明就是燕夫人。”
皇帝拂了一把汗,“人現在何?”
吳奎道,“回了公主寢宮,想必是換裳去了。”
皇帝吐了一口氣濁氣,愣愣看著桌案,心中憾竟是大過驚訝,“可惜啊,竟是那寧氏,朕還當是一普通廚子,便將其招皇宮來。”
那口魚太好吃了,他為皇帝都沒能吃上第二口,眼瞅著百不顧禮節爭搶,愣是住饞的心思,保持著帝王威儀,暗想,待會尋到人,夜里想吃什麼沒有,這會兒算是竹籃打水一場空。
寧晏今日救場已是萬幸,他絕不可能讓外甥媳婦給他這個當皇帝的做吃的,除非偶爾去人家府上蹭一頓,這事皇帝也干不出來。
“不過,這寧氏當真不錯,如此懷與眼界,非常子也,無論如何,今日國宴大漲國威,居功至偉,朕要賞。”
吳奎斟了一杯茶,往皇帝手邊遞過去,笑著應是。
皇帝想起什麼,未接他的茶,又待道,“此事必須瞞著,不旁人曉得,對了,也要瞞著燕翎,以他那脾氣,不得回去責罵寧氏....”
話未說完,瞥見門口那小侍清了清嗓子,拼命鼻子,皇帝眉頭皺了皺,吳奎也發現了不對勁,連忙踱步過去,一道修長拔的緋影,從眼前一閃而過,正朝后殿方向大步離去,瞅著那腳步帶風的架勢,吳奎心肝一,連忙折回來,手中的茶水也灑落一地,
“陛...陛下,不好了,剛剛的話被世子聽到了,看樣子,世子尋夫人算賬去了。”
*
寧晏回到延慶宮,草草用了些吃食墊肚子,重新梳了妝容,換回自己的衫,裹著那件銀紅的雪狐大氅邁出門檻,當空一縷冬暉灑下來,照得如清致明麗的仙子,眉梢那一抹快意竟也被芒染得有幾分炫目,午明,帶著雪后特有的汵汵涼意,撲灑了一臉,翩躚而笑,踏明里。
出延慶宮的宮門,往西過清暉殿,出清暉殿側門,往南有一條宮道直通養心殿,養心殿的右前方便是天星閣,寧晏打算去那里尋燕翎,也不知淳安公主糊弄過他沒有,倘若被他猜到,不得與他認個錯,只要不被旁人發現,想必他也不會為難。
皇帝午后在養心殿午歇,尋常這段時間,這條宮道是無人的。
寧晏被午照得渾暖烘烘的,到底是十幾歲的姑娘,做出一件出眾的作品,心總歸是不錯的,恰才路過延慶宮與清暉殿叉的園子,順手就扯了一狗尾草,頑皮地在手里折一圈花,走到清暉殿角門時,隨手在那門里,明明是氣派恢弘的皇宮,闊的門廊,綺麗的雕花藻井,繁華可鑒,偏生被了一不合時宜的狗尾花。
寧晏抿自得其樂一笑,倚著門檻正要出去,抬眸,一道頎長清俊的影立在宮墻下,鮮紅的緋袍與那深紅的宮墻融為一,他仿佛是鐫刻在墻面上的畫,袍角被風掀得翻滾,墻猶堆有一片雪,明晃晃的落在雪面,亮反襯在他面頰,那張臉從未這般..俊得近乎妖艷。
有那麼一瞬,寧晏是沒認出他來的。極瞧見他穿袍,僅有的兩次也是宮之時,他穿著這袍太好看了些,寧晏螓首歪歪,多看了幾眼,直到那悉的鋒利的芒在那深邃的瞳仁里閃爍,這才回過神來。
是燕翎。
寧晏心下一,當即涌上幾分心虛,
“世子,您怎麼在這?”
燕翎眉梢織著一抹薄怒與煩悶,他無法形容聽到真相時的心,稽,燥郁,又涌上一抹后知后覺的失落與自嘲。
他一直都知道明宴樓是的產業,卻不知才是真正的掌廚。
他才意識到,數月前邀他用晚膳,他失約錯過了什麼。
更不消提,兩刻鐘前,他看到那樣一幅絕無僅有的“作品”,僅僅是抱著一種欣賞與贊嘆,任由旁人將他妻子的杰作一搶而空,而他直到最后才被崔玉施舍了一塊蓮藕。
那滋味,至今在他齒繾綣,回味無窮。
明明唾手可得,卻了被施舍的那個。
燕翎角自嘲地牽了牽,這才緩慢走過來,隔著門檻打量,目又在的鞋面掠了掠,
“腳好了嗎?”
寧晏手還搭在門框,那朵枯萎的狗尾草在二人當中搖晃,輕聲道,“無大礙,涂了些藥便好了...”
也不擅長說謊,這會兒底氣不足,顯得整個人都弱幾分。
太已漸漸西斜,越過門廊投下一片,燕翎就矗立在那團暈里,耀眼又出眾。
寧晏恰恰站在門廊下的影,兩個人目錯,寧晏鎮定一問,“您是來接我的嗎?”
燕翎到底是外臣,并不能隨意在后宮走,這會兒也不可能是去見太后,肯定以為了傷,特意來瞧的。
燕翎先是頷首,清銳分明的眼神直勾勾看著,門廊上有華麗花紋,下有雕紋的木檻,似將框了一幅窈窕秀逸的人畫,就這麼倚在門檻,眼神如銀湖似的帶著鉤子,不如往日那般沉靜。
為何,定是心虛了。
燕翎冷聲一笑,笑意轉瞬即逝,問道,
“晏兒,你可有什麼事要與我說嗎?”
寧晏稍愣,眼中錯的那抹費解與疑漸漸落在實,能這麼問,定是曉得了真相。
他眉間有怒火,寧晏只能以為他是生氣了。
目如壁的芒,折了下來,溫吞道,“對不起,我這麼做,會不會讓你沒面子?”
眼底的驟然有些昏暗,令燕翎心中一折,“為什麼會這麼覺得?”
寧晏輕聲不滿道,“你們世家應該不太喜歡妻子做這樣的事。”在家里該為丈夫洗手作羹湯,在外卻不要拋頭面,雖然寧晏有自己的堅持,卻不能改變世俗的觀念。
燕翎驀地一笑,“那如果我也這樣覺得,你還會做嗎?”
寧晏抬眸看他,眼神異常平靜,甚至平靜中有一抹鋒芒,“會。”
猜你喜歡
-
完結913 章

步生蓮:六宮無妃
她是名滿京城的才女,他是當今炙手可熱的皇位繼承人。他曾許諾,六宮無妃,隻有她一個皇後。可是慢慢的,誓言一點一點的變了,難道真的是色衰而愛馳嗎?他殺了她滿門,滅了她家族,一步步將她推向了深淵。情是甜蜜的源泉,也是斷腸的毒藥。她恨,可是到頭來才發現,一切都是宿命罷了!
163.4萬字8 9116 -
完結990 章
大佬們的團寵又嬌氣了
重生前, 阮卿卿:顧寒霄嘴賤又毒舌,就算長得好看,身材又好,我也不會喜歡上他! 重生後,真香! 前世她遇人不淑,錯把小人當良配。 現在,阮卿卿發現顧寒霄和自家哥哥們都把自己寵上天。 渣男敢厚著臉上門? 是大佬的愛不夠深,還是哥哥們的寵不夠甜,統統踢出去! 白蓮花們看不慣? 有能耐讓你爸媽再生幾個哥哥寵你們啊!
91萬字8 14558 -
連載432 章

將軍懷里的小嬌嬌是玄學大佬
【1v1+高甜+團寵+追妻火葬場!】 謝家老太太從外面買了個小姑娘,說是要給謝將軍做夫人,得知此事的謝將軍:我就是這輩子都站不起來,也不會娶這樣心機深沈的女人! 小姑娘紅著眼眶點頭:我明白的,將軍。 謝將軍的親祖母:他看不上是他沒福氣,衍都青年才俊多得是,我回頭給阿拂好好物色物色,他腿都斷了,還配不上我們阿拂呢。 謝將軍的親弟弟:那只好我將來長大後娶阿拂姐姐為妻啦~ 謝將軍的親妹妹:原來哥哥竟是傷了腿,我還以為哥哥是傷了眼睛,怎麽如此沒眼光! - 後來,謝將軍瞧著姜拂對著旁人笑,覺得異常刺眼。 他將人按在門口,委委屈屈道,「阿拂,別怕我。」
38.8萬字8 19113 -
完結114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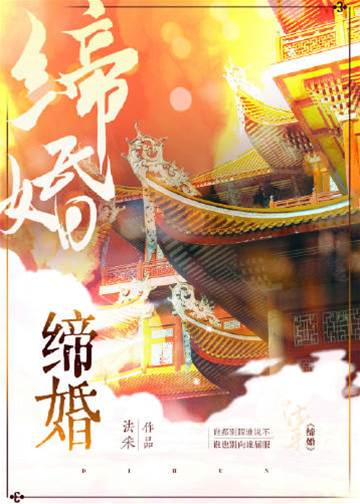
締婚
家敗落之後,項家老爹成了人人喊打的奸佞,項宜帶著幼年的弟妹無依無靠、度日艱難。 她尋來舊日與世家大族譚氏的宗子、譚廷的婚約,親自登了譚家的門。 此事一出,無人不嘲諷項家女為了算計、攀附譚家,連臉面都不要了。 連弟弟妹妹都勸她算了,就算嫁進了譚家,...
45萬字8.33 82137 -
完結170 章

娘娘嫵媚妖嬈,冷戾帝王不禁撩
一紙詔書,廣平侯之女顧婉盈被賜婚為攝政王妃。 圣旨降下的前夕,她得知所處世界,是在現代看過的小說。 書中男主是一位王爺,他與女主孟馨年少時便兩情相悅,孟馨卻被納入后宮成為寵妃,鳳鈺昭從此奔赴戰場,一路開疆拓土手握重兵權勢滔天。 皇帝暴斃而亡,鳳鈺昭幫助孟馨的兒子奪得帝位,孟馨成為太后,皇叔鳳鈺昭成為攝政王,輔佐小皇帝穩固朝堂。 而顧婉盈被當作平衡勢力的棋子,由太后孟馨賜給鳳鈺昭為攝政王妃。 成婚七載,顧婉盈對鳳鈺昭一直癡心不改,而鳳鈺昭從始至終心中唯有孟馨一人,最后反遭算計,顧婉盈也落了個凄然的下場。 現代而來的顧婉盈,定要改變命運,扭轉乾坤。 她的親夫不是癡戀太后嗎,那就讓他們反目成仇,相疑相殺。 太后不是將她當作棋子利用完再殺掉嗎,那就一步步將其取而代之。 如果鳳鈺昭命中注定要毀在女人手上,那麼也只能毀在她顧婉盈的手上。
32.1萬字8 104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