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上帝寵》 第122章 第 122 章(if)
第一百二十二章
桓崇郁從未見過這麼笑的小孩兒,剛滿月的孩子,凝視著他,靜靜地笑,因這小姑娘皮白,眼神溫潤又明亮,笑起來如花照水,很討喜。
譚若貞抱著雪昭往桓崇郁邊走。
十二殿下雖是皇子,但也畢竟只是個孩子,沒有那麼大的防心,忍不住想將自己的兒給五歲的小殿下看一看。
桓崇郁明白譚若貞的好心。
然而他只是淡淡看了一眼雪昭,沖晉國公夫人和譚若貞微微點頭示意,就帶著鄭喜走了。
晉國公夫人見人走遠了,才攬著譚若貞進屋,說:“十二殿下從小就這個子,七個皇子里頭,就他自打生下來便不說話,別管他了。”
譚若貞抱著兒,輕輕地拍了拍孩子的背,臉挨著雪昭,笑著和母親說:“我只是覺得殿下年紀小小,卻不像個小孩兒……”
晉國公夫人說:“宮里皇子那麼多,子憑母貴,十二殿下的生母位分低,宮里頭的太監、宮不也是捧高踩低的。”
譚若貞慨道:“皇上的孩子也會這樣啊……”、
晉國公夫人一下子就心疼起來,覺得兒可能想到了什麼委屈的事,才同,眼一紅,抱了抱兒。
母連心,譚若貞趕笑道:“娘,兒沒事。”
晉國公夫人又去看孫,牽了牽雪昭的小手,說:“這孩子,怎麼從小就這麼笑,瞧笑得,眼睛像月亮……來祖母抱抱。”
譚若貞將兒給了母親抱。
-
桓崇郁在國公府里用過雪昭的滿月宴,就和皇兄們一起回了皇宮復命。
同回宮中見嘉延帝的,還有大高玄殿的道士。
“皇上到東苑看親衛們擊球去了。”
皇子們到乾清宮時,侍這般告訴他們。
Advertisement
皇子們又都一起去了西苑。
嘉延帝聽說兒子們來了,正好在外面也曬熱了,移駕殿,見兒子們,問他們晉國公孫的滿月宴辦得怎麼樣。
皇子們一一到前敘述所見所聞。
到桓崇郁,他剛起了個頭,嘉延帝似乏了一般,吩咐侍:“把東西拿過來。”
侍托了托盤近前。
桓崇郁緩緩退回兄弟中間,將之前未說完的話,全咽進了肚子里。
嘉延帝和兒子們說:“西苑新建的大殿要竣工了,禮部擬了幾個字送過來,來,都幫朕挑一挑,看看哪個字好。”
皇子們序齒上前,桓崇郁仍是最后一個,一共五個字,兄長們選了四個,還有一個沒有人選,是個“泰”字。他沒得選,就選了這個沒人選的字。
侍將十二殿下選的字,呈到嘉延帝面前。
嘉延帝認真看了看,念了出來:“泰……十二為什麼選泰字?”
桓崇郁欠道:“回父皇,泰字吉利,否極泰來,國泰民安。”
“國泰民安?”
嘉延帝怪異地笑了一聲,撂下‘泰’字,說:“年紀不大,心倒是寬,已經將國、民都往心里裝了?”
桓崇郁的頭也越發低,稚的臉龐上,顯出惶恐:“父皇息怒,兒臣失言。”
音落,稚的膝蓋幾乎是砸在了石磚上。
嘉延帝冷淡地說:“的確笨拙舌。”
似乎暴風雨將來。
殿跟著跪了一片,靜可聞針。
氣氛抑至極,嘉延帝又突然和和氣氣地道:“就這個‘泓’字,送去工部,讓他們快點把牌匾做好。”
“是。”
其余皇子都紛紛道:“‘泓’字好,恭賀父皇喜得新殿。”
桓崇郁也說:“恭賀父皇。”
嘉延帝懶懶地“嗯”了一,揮著寬袖,說:“都下去吧。”
“兒臣告退。”
嘉延帝還在等人,他撐著臉,朝近的宮人示意一眼,就閉眸休息了。
等聽到腳步聲,才睜開眼。
宮人說:“回皇上,幾位皇子出了殿后,沒什麼異常的臉。”
嘉延帝挑眉問道:“十二也沒有?”
“沒有。”
嘉延帝擰了擰眉,眉心豎紋十分深重。
這兒子有飛龍之命,將來必定要克他,現在卻一點苗頭都沒有,也不知是道士斷錯了,還是這小子藏得深。
但是,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
道士來了,走上前來,跪道:“參見皇上。”
嘉延帝懶洋洋地問:“相面相出什麼了沒有?”
道士言又止……他早聽說過嘉延帝晴不定、疑心重。
他一會兒看出皇子上的紫氣,一會兒又看出命,只怕說出來嘉延帝以為他信口胡謅,會掉腦袋。
嘉延帝聽不到聲音,眼睛瞪了瞪,犀利地盯著道士,質問道:“朕面前,有什麼不可說?”
道士惶恐道:“回皇上,貧道看出……看出……晉國公的孫有……有命。”
說完,他兩抖如篩糠,伏在地上直不起子。
哪知嘉延帝突然放聲大笑,拍著椅子說:“妙,妙,妙。”
道士和侍都一臉發蒙。
妙在哪里?
嘉延帝心愉悅地說:“朕就知道和譚禹亮要做親家,再過些日子,朕得先看看朕的孫媳婦長什麼樣子。”他起慢步出去,笑著吩咐侍:“等這孩子大些了,記得提醒朕見一見。”
“是。”
等嘉延帝走遠了,道士才敢從地上爬起來,額頭上的冷汗,著雙走出去。
螳螂捕蟬,黃雀在后。
道士走了,鄭喜才趁著天黑面,悄悄從東苑溜回了宮中。
桓崇郁在燈下看書。
鄭喜灰頭土臉地回來,滿的泥,膝蓋上泥印很深,他臉凝重地說:“殿下,那道士和皇上說,晉國公的孫,有命!”
桓崇郁淡淡問道:“父皇怎麼說?”
鄭喜也一頭霧水:“皇上高興得很,好像很樂意和晉國公做親家,不過皇上說的是……‘孫媳婦’。”
桓崇郁目微凝。
這個孫媳婦,很耐人尋味。
若嘉延帝信道士的斷言,晉國公的孫,命就不該應在皇孫上。
若嘉延帝不信,就不會這般高興。
鄭喜后背發寒。
皇上本沒想放過小殿下。
虎毒不食子啊!
桓崇郁只是看著鄭喜的雙膝,說:“你以后不用再去了。”
東苑主殿后面有個狗,掩映在深厚的雜草里,誰都不知道。
只是那狗常年積水,泥土潤,要躲過殿宮人的視線,得在狗附近跪好長時間。
鄭喜每次都從里面鉆進去聽,回來的時候,膝蓋又又冷。
鄭喜嘿嘿一笑:“殿下別心疼奴婢,奴婢子好著呢,不怕冷,不怕疼。”
桓崇郁轉過臉,說:“回去吧。”
鄭喜趕回去洗漱,回房時,桌上擺著幾瓷瓶的藥。
他撥開一聞,都是主子平日里都舍不得用的藥,他抬起袖子,了眼淚。
沒過多久,鄭喜果然不用再去鉆狗了。
皇子們在東苑學習騎時,不知道誰的馬踢到了桓崇郁的嚨,他失語了。
嘉延帝聽說之后,特地來太醫詢問:“果真不能言語了?”
太醫憂心忡忡道:“皇上,微臣無能……十二殿下的確不能開口說話了。”
嘉延帝并沒有發怒,只是說:“下去吧。”
過了些日子,桓崇郁傷好繼續和皇兄們一起上課,嘉延帝特地過來看他。
桓崇郁整個脖子還腫著,在廊下沖嘉延帝行禮,張著說話,卻沒有聲音。
嘉延帝沒注意兒子說什麼,只盯著他腫大的脖子。
直到兒子起,他才反應過來,兒子在和自己行禮,便說:“你傷都沒好,起來吧。”
桓崇郁直起子,腦袋卻低著。
嘉延帝不知在忖量什麼,就看了這麼一遭,轉回了乾清宮。
這一日,他都心神不寧,到了晚上,忍不住問近侍:“你說,五歲的孩子有沒有可能裝啞?”
侍心一驚,為難地說:“……這、這,醫診斷過的傷,奴婢一個太監,又不懂醫,不敢胡說。”
嘉延帝點了點頭,可能他想多了,又篤定地說:“假以時日,他必定學會語。”
以后連瓣一,都要小心提防這個兒子。
-
鄭喜為桓崇郁換藥的時候,眼淚直掉。
有什麼好哭的。
桓崇郁睨著鄭喜,嗓子實在疼,也說不出什麼,索不說。
鄭喜也懂主子的眼神,掉了眼淚,說:“殿下,等您長大了就好了。都會好的……”
桓崇郁的眼眸中,極罕見的,出了一暴戾之。
養傷三月,桓崇郁才徹底痊愈。
他的嗓子能勉強說話了,但長久沒開口,甫一開口,沙啞糲,幾乎不像一個五歲孩子的聲音,而且只能一個字一個字地往外蹦:“鄭、喜,從、今、以、后、只、有、你、一、個、人、能、聽、到、我、說、話。”
鄭喜目如刃,應道:“奴婢省得。”
殿下您放心,奴婢會為您小心提防和善后的。
雪昭周歲時,晉國公府為辦了周歲宴。
嘉延帝這回沒派兒子們過去,而是直接讓譚禹亮將孩子抱進宮,給他看看。
晉國公帶著雪昭去面圣。
嘉延帝又問侍:“皇子們都在干什麼?不忙的都過來。”
侍去人時,桓崇郁避開了。
鄭喜想起晉國公府的小千金,笑著說:“不知雪昭小姐長什麼樣了,奴婢記得剛滿月的時候,就長得比別家的小孩兒都好看。”
寢宮中沒有別人,桓崇郁才淡淡地道:“離遠點。”
鄭喜肅然道:“奴婢知道。”
大高玄殿里的道士批了命的姑娘,離太近,等同于自戕。
桓崇郁的視線,也從鄭喜的瓣上挪開了。
如嘉延帝所猜,短短幾月,他便學會了語,還有手語。
猜你喜歡
-
完結556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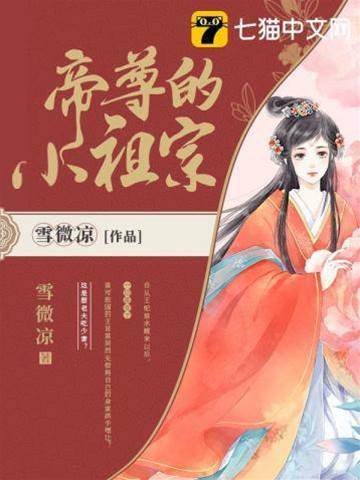
帝尊的小祖宗
自從王妃落水醒來以后,一切都變了。富可敵國的王首富居然無償將自己的身家拱手相讓?這是想老夫吃少妻?姿色傾城,以高嶺之花聞名的鳳傾城居然也化作小奶狗,一臉的討好?這是被王妃給打動了?無情無欲,鐵面冷血的天下第一劍客,竟也有臉紅的時候?這是鐵樹…
99.6萬字8 11327 -
完結506 章

媚婚之嫡女本色
陌桑穿越了,穿越到曆史上沒有記載的時空,職場上向來混得風生水起的白領精英,在這裏卻遇上讓她恨得咬牙切齒的克星,高冷男神——宮憫。 他嫌她為人太過陰詭狠毒。 她嫌他為人太過高冷孤傲。 本想無事可做時,虐虐渣女渣男,逗逗小鮮肉。 豈知一道聖旨,把兩個相互看不順眼的人捆綁在一起,組成嫌棄夫婦。 自此兩人過上相互猜測,彼此防備,暗裏算計,夜夜心驚肉跳的生活。 豈知世事難料,兩個相互嫌棄的人看著看著就順眼。 她說“你是護國賢臣,我是將門忠良,為何跟你在一起,總有種狼狽為奸的覺悟。” 他說“近墨者黑。” 陌桑點點頭,確實是如此。 隻是,到底是誰染黑誰啊? 再後來…… 她說“宮憫,你是不會笑,還是從來不笑?” 他看了她十息,展顏一笑“陌桑,若知道有一天我愛你勝過愛自己,一開始就不會浪費時間防備你、猜疑你,而是把所有的時間用來狠狠愛你,因為一輩子太短,我怕不夠愛你。” 陌桑咽著口水道“夫君,以後千萬別隨便笑,你一笑,人就變得好風騷……” 宮憫麵上黑,下一秒就露出一個魅惑眾生的笑容“娘子放心,為夫隻對你一人笑,隻對你一人風騷。” 某女瞬間流鼻血…… 【這就是一個白領精英穿越到異世古國,遇上高冷男神,被帝王捆綁在一起,相殺互撕,最後相親相愛、強強聯手、狼狽為奸的權謀愛情故事。】
187.7萬字8.18 335163 -
完結639 章

萬毒狂妃懷個寶寶來虐渣
她,本是藥王谷翹楚,卻因圣女大選而落入圈套,被族人害死。 一朝身死,靈魂易主。 楚斐然自萬毒坑中醒來,一雙狠辣的隼目,如同厲鬼蒞臨。 從此,撕白蓮,懲惡女,不是在虐渣,就是在虐渣的路上。 她醫毒雙修,活死人,肉白骨,一手精湛的醫術名動。 此生最大的志向就是搞到賢王手上的二十萬兵馬,為她浴血奮戰,血洗藥王谷! 不料某天,他將她抵在角落,“女人,你懷了本王的孩子,還想跑路?”
110.9萬字8 12452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