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拯救偏執首輔后》 我只信她的話
沈芷甯在靈堂給李知甫上了三炷香,就一直待在靈堂,晚間時,才回了永壽堂。
沈老夫人見沈芷甯魂不守舍,整個人如行走般走進來,而那雙眼睛哭多了,已經流不出淚來,不由心疼,起拉坐于榻上,對一旁的許嬷嬷道:“你去拿塊熱巾來。”
許嬷嬷一直心疼地看着沈芷甯,哎了一聲:“老奴已經備好了,這會兒就讓們拿來,五小姐也一天未吃東西了吧,待會兒吃點墊墊肚子。”
沈芷甯一直低着頭,未說話,墨發垂于脖間,也遮擋着半邊臉。
“這才第一天守靈,還有六日,你這般下去,子可還吃得消?”沈老夫人拉過的手,歎了口氣道,“祖母知道,你不止因着李先生,還有那秦北霄,我知我現在說這話,你許是要傷心,但有些話還是要說在前頭好。”
“你與秦北霄,就算李老夫人不阻撓,也難事。”
沈芷甯手指微。
沈老夫人繼續道:“那李家三人拿着老祖宗的規矩來搶,偏生沒法子治他們,今日我得知你确爲李知甫弟子,雖有了正當的名義,可還不足以讓他們退卻,唯有給你找個有力的靠山。我今日寫了兩封信去京都,一封寄去齊家、一封寄去顧家,爲的就是這個事。”
“寄去顧家的那封,是給顧老夫人的。顧家正在相看顧家三公子的親事,我求顧老夫人幫忙,這親事就與你定下,也并非真正讓你同他親,解的是如今的燃眉之需,待事過去後、或是等你三年守孝期過後,你再去京都,你可将親事解了,畢竟此事隻是一個幫忙罷了,到那時,一切已定局,那李家想拿也沒法拿了。”
“那寄去齊家的那封,是給你舅祖母的,定親還是個大事,如今我們沈家都不在京都,隻得靠齊家與顧家走,那再過些日子,婚書許是要下來了。”
Advertisement
聽到這裏,沈芷甯頭垂得更低,哽咽道:“祖母,真的沒有任何辦法了嗎?”
想等秦北霄回來的,想等他回來提親,可爲什麽安侯府落網後,一切都變了,先生死了,秦北霄也被困在京城出不來,這邊,竟還要跟從未見過面的人定親了。
雖說是假的,可秦北霄不會知道是假的,要與他斷絕關系了,也絕不能說是假的,隻能承認這是真的,那他要是知道了信誓坦坦等他回來的沈芷甯轉眼之間就要與他人定親,他會怎麽想啊。
沈芷甯想都不敢想,搭在擺上的雙手攥着,覺整個人都在彷徨無助的黑暗中。
“有舍有得,你選擇了師父,便好好放下這段吧。”沈老夫人一邊撥着佛珠,一邊慢聲道,“諸法因緣生,諸法因緣滅。你與他或許本就無緣,當初你一意孤行救下了他,與我說的是不能見死不救,救下他便好了,如今這不是已經達了?那其他的就不要奢求了……”
沈芷甯子一怔。
祖母說的不錯,與他确實本就無緣,上一世,與秦北霄不過那東門大街的一面之緣,這一世,開始也是的一意孤行與他牽扯到了一起,如今恩報了,願也達了,當初想要的、想改變的都已得到了。
他走他的權傾朝野之路,過平靜安甯的一生,這應該是原先想好的。
可,一想到他,就是鋪天蓋地的悲傷吞噬着,說話、走路,都得用盡力氣去掙紮。
沈芷甯垂眸,聽着自己蒼白的聲音道:“祖母,孫明白了。”
出了祖母屋子,沈芷甯停在廊檐下。
今夜空中無月無星,這幾日,沈府的燈火似乎都比平日裏黯淡許多,站了許久,随後去往西園守夜。
到了第七日,先生棺,出殡。
從西園出發,去往墓地,一行隊伍浩浩,沈芷甯扶着哭得子快撐不住的餘氏走在最前,旁側無數人撒着紙錢、拿着白幡,所經之路,滿眼的白茫茫。
從一個街巷走到另一個街巷,吳州的百姓皆在兩旁,也有随着隊伍一道行走,送殡隊伍越來越長,哭聲本抑着,後有一子從兩旁沖出,哭着跪倒在棺材旁:“先生!”
其聲撕心裂肺,聽得衆人更爲容,哭聲從抑變得釋放,連綿不斷,響徹上空。
沈芷甯回頭看着衆人,再落于棺材上,淚水直湧。
雲水蒼蒼,江水泱泱,先生之風,山高水長。
傍晚,京都秦家别院。
馬匹沿着大門口的大道飛馳而來,缰繩狠狠一勒,駿馬一陣嘶鳴,男人翻下馬,早就站于一旁候着的小厮忙接住缰繩。
“今日可有來信?”秦北霄徑直大步進大門,問迎上來的小厮觀文。
“今日未有來信。”觀文立即回道,“不過吳大夫今日來了。”
到底子傷着,吳大夫隔一段時間便來把脈一次。
秦北霄什麽話都未說,但臉冷淡了些許,按理說,應當來信了才是,這般想着,往主堂走去,進了主堂後,吳大夫給他把脈。
“秦大公子心火燥啊,”吳大夫道,“這兩日刑部是有何焦頭爛額之事嗎?”
秦北霄眉頭微微一蹙,吳大夫繼續道:“子比之前好上許多了,秦大公子也莫要多勞,好生休養才是。”
“你又不是不知我如今境況,”秦北霄收回了手,随意理着袖扣,眼角微起看着吳大夫,“這好生休養也得有命休養。”
吳大夫無奈道:“是,秦大公子,老夫再給你多開幾幅藥吧。”
“吳大夫請。”觀文引着吳大夫打算出屋門,未料到剛出門就撞到了蕭烨澤,觀文被撞倒在地,蕭烨澤來得又急又沖,本顧不上他,直接進屋門道:“秦北霄!你可知道吳州發生了什麽事?!”
秦北霄一聽到吳州兩個字,面一下凝重起來。
蕭烨澤甚至都未坐下來,看着秦北霄,想到方才聽來的消息,也是悲從心來,紅着眼眶道:“李先生去世了。”
秦北霄立即站起來,沉聲道:“去世了?”
蕭烨澤撇開頭,用袖子随意了下眼角:“是,楊建中的人快馬加鞭趕回京的、進京就直奔父皇那兒報信,我一聽聞消息就趕來了,說是被人刺殺,安侯府逃出來的那些個護衛幹的,了三箭而亡。”
說到後面那句,蕭烨澤已有些哽咽。
秦北霄整個人都開始沉:“安侯府?楊建中好個庸人!說什麽便信什麽,安侯府早就被查得幹淨,悉數相關人等不是被殺的殺、斬的斬,哪還有什麽流亡之人,他倒還真敢報上來!定是他勸李知甫來京,許是說了李知甫,此事被人知曉……不是安侯府,我親自去查!”
說着,就要出屋門,被蕭烨澤攔了下來:“你瘋了?你現在離不了京!整個京都都對你虎視眈眈,刑部和秦氏都盯着你,就等着你犯錯!你一離京就是一本參折,到時候着父皇罰你獄,誰救得了你!”
“難道就讓楊建中那廢人查?查不出來怎麽辦?先生就這麽死了?”秦北霄冷聲道。
蕭烨澤突然間沒說話,看了秦北霄許久,慢聲道:“先生的事,楊建中定會盡全力去查的,我來,還有另外一件事告訴你。”
蕭烨澤對上秦北霄的眼神,突然不敢将話說出口,他竟害怕秦北霄知道這件事。
可必須得讓他知道。
蕭烨澤輕聲道:“沈芷甯,與顧家定親了,定的是顧三顧熙載。”
這話說完,蕭烨澤就看秦北霄反應,他面與平常無異,眼神幽深,像是沒聽到這句話一樣,而後,他慢聲道:“我不信。”
“我今日特地趕來,爲的就是這兩件事,你應該知道我此刻所說并非假話,齊家的齊老夫人已上了顧家的門,已将婚事定了下來,過兩個整個京都就都會傳遍了!”
“我說了,我不信。”秦北霄的眼神狠戾至極,死死盯着蕭烨澤道,“說過會等我回去。”
“這定親乃事實!就算你不信,事實便是如此,你改變不了!沈芷甯說等你回去,改變心意了也說不定,這都是說不準的。”
話音剛落,蕭烨澤脖間就到一片冰涼,對上的是秦北霄凜冽的眼神:“三殿下,我警告你,此事莫要再胡說。”
蕭烨澤簡直要被氣笑了。
見蕭烨澤未再說話,秦北霄才收了袖刀,轉就往外走。
蕭烨澤突然有種不好的預,連忙跟了出去:“你去哪兒?”
秦北霄不說話,直往大門走。
“你不會要去吳州吧!”
聽到這句話,秦北霄停住腳步,沉着嗓子道:“我要去問個清楚,我隻信所說。”随後,大闊步走向門口。
“瘋子瘋子!你不能離開京都!你若是離開了,等你回來你就完了你知道嗎——”
蕭烨澤追到門口,隻見秦北霄淩厲翻上馬,手中馬鞭一揮,駿馬直奔碼頭方向。
猜你喜歡
-
完結42 章

嬌妻如蕓
杏花樹下,夫君許我一世安逸富足的田園生活,逍遙自在,濃情愜意;杏花落盡,往日的歡情在一次次的刀光劍影中,柔腸寸斷,痛苦不堪;我望著夫君,那個曾經的屠夫,現在的將軍;縱使萬人阻擾,天地不容,也只愿留在他的身邊,做他專屬的嬌妻。
34.4萬字8 10356 -
完結337 章

成為人生贏家的對照組[快穿]
她不是人生贏家,卻比人生贏家過的還好,你敢信?人生贏家歷經磨難,一生奮斗不息,終于成了別人羨慕的樣子。可她,吃吃喝喝,瀟灑又愜意,卻讓人生贏家羨慕嫉妒恨。在紅樓世界,她從備受忽視的庶女,成為眾人艷羨的貴夫人,作為人生贏家的嫡姐,也嫉妒她的人…
212.4萬字8 10567 -
完結236 章

卷春空
青梨跟著改嫁的娘親到了國公府。國公府外頭瞧著榮耀,內里的后宅卻是個骯臟地。娘親在時,青梨日子尚且能過下去,娘親死后,她徹底無依無靠,只好將目光放在了府上嫡長子俞安行身上。國公府世子俞安行,一身清骨,為人端方,對眼前一副凄慘模樣的青梨起了惻隱之心,處處照拂她。青梨倒也爭氣,在百花宴上憑一手制香技藝驚艷眾人,一時才名遠揚,京都來提親的人家幾欲踏破門檻。青梨相中了合眼緣的夫婿,不想才剛議親,遠在姑蘇的小姑卻突然來了京都尋她,快定好的婚事被推拒,還欲將她抬去給四五十的老色鬼昭王做側室。青梨無法,目光重又放回了俞安行身上。一夜荒唐,俞安行為了負責,同青梨成了婚。婚后兩人琴瑟和鳴,青梨對府中事務處理得宜, 俞安行甚是滿意。直到有一日,他不慎聽到了青梨同小姐妹的私房話。——“俞安行此人甚是無趣,若非當時急于自保,我如何會挑上他?”是夜。俞安行一字一句同她算賬。青梨眨了眨濕潤的長睫,帶著哭腔柔聲解釋。“那都是唬人的話,阿梨心里自然是有夫君的。”俞安行臉上笑意莫測。騙子。不過這也算不上什麼,畢竟,她已是他的人。而且,他也騙了她。俞安行抬手,輕捏住了青梨的下巴。“阿梨大抵不知,當初讓你嫁給昭王的主意,是我出的。”
34.9萬字8 13090 -
完結173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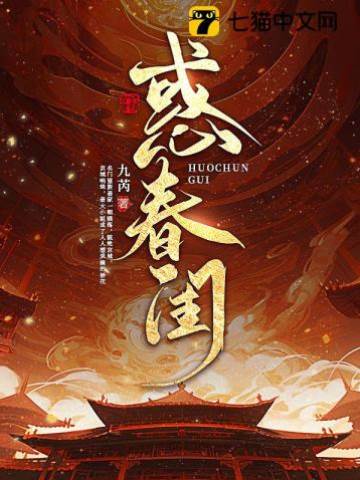
惑春閨
名門望族薑家一朝隕落,貌絕京城,京城明珠,薑大小姐成了人人想采摘的嬌花。麵對四麵楚歌,豺狼虎豹,薑梨滿果斷爬上了昔日未婚夫的馬車。退親的時候沒有想過,他會成為主宰的上位者,她卻淪為了掌中雀。以為他冷心無情是天生,直到看到他可以無條件對別人溫柔寵溺,薑梨滿才明白,他有溫情,隻是不再給她。既然再回去,那何必強求?薑梨滿心灰意冷打算離開,樓棄卻慌了……
31.5萬字8.18 7906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