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蜜桃咬一口》 第39章 升溫
簡桃還沒等到謝行川回復,彈幕先炸起來了。
【別人眼里:簡桃想贏。】
【缺德CP眼里:在撒。】
【編還是你們會編,我本來就一路人,看你們編了半小時已經心了。】
【簡桃只是天生長得漂亮吧,所以稍微語速放慢就像在撒,怎麼可能跟謝行川撒的,關系那麼差。】
【你大膽!這是你說實話的時候嗎!】
【是不是撒關我什麼事?!人生如戲不能演嗎?!@#¥%我辛苦了一天看點小撒調是我應得的!謝行川看似沒有表,心已經狠狠了,懂?】
【我不編料我怎麼活?!我不編料我嗑什麼?!他們必在我看不到的地方翻云覆雨,川の心已被老婆牢牢掌控,別問我怎麼知道的,我現編的。。。】
【會編多編,顴骨升天。】
.........
謝行川玩著手里的骰子,起眼皮看一眼,漫不經心道:“隨你。
能不能隔兩子跳棋也隨?
簡桃是真不記得規則了,撐著臉頰道:“隨我的話我可就贏了。”
話音剛落,作最慢的鄧爾也放下了手里的勺子。
看將最后一顆棋放進陣營里,謝行川挑了下眉尾,這才起道:“行了,走吧。”
眾人紛紛起收拾東西,簡桃頗為不舍地看了眼棋盤,不知他究竟是想走了還是怎麼。
一旁的攝像老師開始準備關閉機,大家跟觀眾道了別,準備離開。
走出兩步后,簡桃忍不住回頭,碎碎念道:“我獲勝了都沒戰利品嗎?”
謝行川結完賬,拿到個火鍋店贈的小玩,是個柴犬的掛件,遠遠朝拋來。
簡桃手接住:“贏的人就這個獎品啊?”
Advertisement
三兩步上前:“這個不適合我……”
走出火鍋店,夜已經深了。
星河流淌,大家上了各自的保姆車,驅車回去休息。
簡桃到酒店先洗完澡,這才放松地趴在床上,晃著小看劇本。
沒看一會兒,被人擒住腳踝。
約的水汽從那人皮上滲而來,漉漉的,還帶著浴室的霧和熱氣。
簡桃不滿地回過頭:“干嘛?”
謝行川:“東西呢?”
“什麼東西。”
“就那小禮,”他在包旁掃視一圈,“真扔了?”
“沒扔呀,”挲了一下,在枕頭的隙之間把它撈了出來,“掛你包上吧。”
謝行川垂眼看,又氣又好笑地道:“不是你鬧騰半天要戰利品?”
“我哪鬧騰了,你說可以隔子跳的。”簡桃振振有詞,又翻了個面,徹底起了。
把掛件勾在指間,任它吊著輕晃,又把它挪到謝行川臉邊,瞇著眼,仔仔細細地比對了一番。
“它長得好像你,”對比后頒布結論,大無疆道,“不如你認它做兒子吧。”
“……”
“你自己聽聽,你這說的是不是人話。”
一頭扎進枕頭里,小因慣翹起,按滅自己那邊的臺燈,委屈道:“也要罵?”
“……”
*
又忙了幾天,周三晚上,夢姐給發來消息,是后期的工作規劃。
【最近在給你談一個仙俠劇的本子,古裝天花板更高更抬人,沒問題吧?】
發了個點頭的表包:【知道啦,你安排吧。】
對面正在輸了一會兒,發來一句:【你跟謝行川最近怎麼樣了?】
有點奇怪,但沒當回事兒。
藝人的狀態嘛,經紀人是需要時刻關心的。
撿個桃子:【什麼怎麼樣,就那樣唄。】
夢姐:【你們結婚多久了?】
側過頭,看了一眼正在旁邊敲電腦的謝行川,想了想:【兩年半了吧。】
【那久了。】
是久了。簡桃心想。
一句“怎麼突然問這個”還沒發出去,夢姐的消息又跟進來:【你們當時約好是結幾年?】
曲著,將腳尖輕微勾起:【沒說幾年,反正起碼得持續到他正事辦完。】
打完這句,突然想起什麼似的,轉頭問謝行川:“對了,你后媽那事兒進行得怎麼樣了?”
謝行川按了行回車鍵,道:“差不多了。”
“媽媽留下的公司已經差不多回到你手上了?”
“嗯。”
噢了聲。
謝行川母親離世那年,他還沒年,母親留下的公司由父親轉給后母,而這些年間,他一直在用自己的方式,將本該屬于自己的公司拿回來。
謝行川頓了下,如同緩慢回憶起什麼,側頭問:“怎麼突然問這個。”
而簡桃已經將頭重新偏了回去,在看夢姐發來的ppt,沒聽到他的聲音。
謝行川:“簡桃?”
愣了下,這才回過神來,如夢初醒般看向他。
好像很見他催促過自己,如同想證實什麼東西一般。
輕咳了聲,這才道:“沒什麼啊,當時結婚不就是為了應付嘛,我順便想到了,就問問。”
房間安靜了會兒,只有加和空調的聲音,聊了會兒工作也困了,放下手機,撈了個眼罩,囑托他早點關燈睡覺,就平躺著,呼吸漸漸均勻。
不知過了多久,謝行川關掉自己那側的臺燈,太久未有指令的電腦也隨之熄屏,只有藍環形的電源燈,在黑暗中散著淡淡的。
謝行川手指搭在電腦邊沿,很輕地抬了下。
回憶許久未開封,他做人極回看,但其實每一幕都無比清晰。
他向來比任何人記憶力都要好。
風投圈,無人不知謝家獨占鰲頭已久,他父親謝益一共有過三任妻子,他母親凌珊,是第二任。
謝益與第一任妻子離婚后五年才再婚,因母親是位出塵絕世的人。他出生那年,是母親嫁謝家的第三年,他上頭還有個第一任所出的哥哥,不過那兄長對商界來往毫無興趣,早已在國外結婚生子,鮮聯絡。
年乏善可陳,沒什麼好講的,既沒有風云纏斗,也沒有糖般的溫馨歡愉,生活于他是杯溫水,能及的紙醉金迷愈多,反而愈加覺得沒什麼意思,母親子向溫,他便互補地多了些玩世不恭與氣,用以應對一些不安好意的人,或是輕飄飄地拒絕些不喜歡的提議。
別人總覺得他是擁有得太多了,才會沒什麼想要的。
其實他也沒有過什麼,至那時,收到與付出的都很淡,淡到偶爾午睡大夢覺醒,會覺得以往十來年會不會也就是場夢而已。
母親素來溫解語,見朋友工作氣,主引薦來謝家管事,然就在母親去世那年,這位“管事朋友”一鳴驚人,領出個與他同父異母的親弟弟,只比他小上三歲。
原來背叛在十三年前就發生。
其中如何勾纏他不得而知,只覺反胃,謝益朝秦暮楚、離心背德,薛蘭恩將仇報,滿腹算計,只為家產。
母親因意外去世,所有人都沉浸在突如其來的悲傷里,只有薛蘭,這由母親引薦而來的“朋友”,他平素都要喊一聲阿姨的人,忙著要來母親本留給他的那間公司,假意說是代為保管。
保管是假,握住他唯一想要的東西,用以制衡他,是真。
制衡他不可有狼子野心,制衡他不可威脅到兒子的地位,制衡他絕不可太過優異,為謝家的下一個繼承人。
倘若他選擇謝氏,就要失去母親留下的,唯一的心。
他那時只覺得荒謬。
謝家的公司,不要說當時僅高一的他,就連現在他都沒有毫興趣。
然那時到底是沒有選擇,于是薛蘭需要他不學無,他便不學無;
需要他荒誕不經,他便荒誕不經;
需要他一無所長,他也可以一無所長。
他倒也不覺得這一生都要這麼過下去,但往后如何確實也未曾想好,那年夏天,薛蘭找了個冠冕堂皇的托詞,說是為他學業好,將他從國際學校送出,送進了寧城一中。
那一年,他遇到簡桃。
他知自己是被放逐于此,也深知要當個紈绔的使命——或者說,無論他本是何種樣子,在別人眼里,他得是紈绔。
與薛蘭推拉不過月余,他仿佛已無師自通地學會飾與扮演,總而言之,得先騙過薛蘭,才能為爭取到更多的自由。
于是扮演得愈加自然,甚至能得心應手地演出自己需要展現的緒,往后想來,或許正是如此,才讓他在演戲上總比旁人天賦異稟許多。
好在他格本就隨意,不過是要演墮落而已。
分班考試幾個大題,試卷做,上課休息,沒人知道轉來之前,他是整個國際學校的年級第一。
薛蘭對他的一蹶不振十分滿意,連他自己都騙過自己,抬頭時世界布滿云,他也分不清,究竟是不是會下雨。
一中的軍訓比別的學校更晚一些,每個年級都必須有,開學三個月過后,他們被打包送去軍訓營地,那日是難得的惡劣天氣,狂風夾雜陣雨。
最后一個訓練項目,他無意間被人撞下高臺,大家都在笑,他抄手靠著墻沿也在笑,別人羨慕他不用過索道,打趣聲沒一會兒便停。
他們在上面熱熱鬧鬧,他獨自站在臺下,覺得這些熱鬧似乎從來都和自己沒有關系。
這些年來不也一直是這樣嗎,所有人羨慕他那一刻擁有的,卻沒人關心那擁有的,他是不是真的想要。
沒一會兒,簡桃從上方探出來,似乎是唯一一個記得他還在底下的人。
陣雨前奏,細的雨滴落在鼻尖和額發,一手撐著欄桿,另一只手朝他遞來,掌心攤開:“上來麼?”
他垂眼。
視線所及,胳膊纖細而白皙,朝他遞來時翻轉過側,更是細膩如瓷。
讓人不由得懷疑,要真能把他拉上去,是不是起碼也得骨個折什麼的。
這麼想著,他順著手腕朝上看去,打趣般地道:“我還得上去?”
……
頭頂雷聲轟隆作響,看向他時視線清明,茶棕的瞳仁不染雜質,澄明而鎮定。
仿佛是在說此刻,又仿佛不是在說此刻。
“謝行川,”這麼他的名字,問他,“下陷可以,你甘心嗎。”
暴雨陡然而至,卻很奇跡地、命運般地只落在后側,分界線從某清晰地劃開,而沒有被淋。
很奇怪。
所有人都以為他是玩世不恭的公子哥,以為他本如此,偏知道,他是在墮落。
又或者,其實并沒猜出,只是就事論事著隨口一說,只有他以為是話里有話。
是啊,他甘心嗎。
怎麼可能甘心。
驟雨初歇時,他低眼開了口。
“歇著吧。”
他說,“不用你拉,我自己上去。”
……
于他而言,回憶是很玄妙的東西,偶爾想起也只是盡可能快地掠過,高中三年并不是什麼快樂的記憶,然而又總有割舍不下的緒摻雜其中,如同苦藥里的甜味劑,困苦越深,那甜味就更像是救贖。
對別人脾氣總是很好,卻不被他惹得跳腳,不讓他,手不讓他,不得給他畫出一個限定的區域,一刻也不要惹到才好。
那時候他已經松懈了很久,雖然母親離世已過去快一年,再怎麼接和釋懷,多也會被影響,但那日雷聲和的眼睛仿佛是警鐘,于不斷下墜之中告訴他,停止放逐,才是唯一的解藥。
他將的卷子全數找出,許久未翻開的書頁也重新劃上筆記,幾個月的課程而已,對基礎很好的他,要趕上并非難事。
他還是眾人眼里散漫的小爺,上課只支著腦袋轉筆,考試提前卷去打臺球,作業偶爾缺席也沒人管,不想背包就提著漫畫書去上課,因為謝家為學校翻新了圖書館和教學樓,只要他不犯事,老師和校長也不會對他有任何不滿。
猜你喜歡
-
完結367 章

前妻,敢嫁別人試試
三年前,她在眾人艷羨的目光里,成為他的太太。婚后三年,她是他身邊不受待見的下堂妻,人前光鮮亮麗,人后百般折磨。三年后,他出軌的消息,將她推上風口浪尖。盛婉婉從一開始就知道,路晟不會給她愛,可是當她打算離去的時候,他卻又一次抱住她,“別走,給…
95.4萬字8 74666 -
完結115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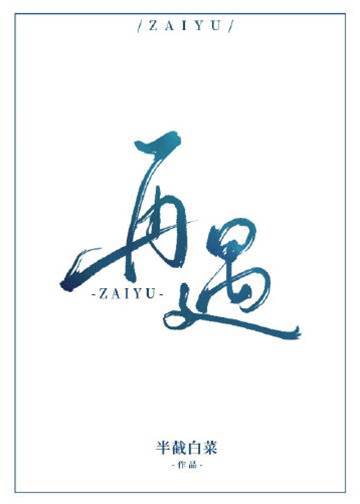
再遇
孟淺淺決定復讀,究竟是為了自己還是為了應浩。她也不知道。但是她成功考上了應浩所在的大學。一入學便得知,金融系應浩正跟金融系的系花談戀愛。-周喬曾說應浩不是良人,他花心,不會給她承諾以及未來。孟淺淺其實明白的,只是不愿意承認,如今親眼所見,所…
38.8萬字8 18890 -
完結641 章
重返七零之空間小辣妻
末世大佬唐霜穿到年代成了被壓榨的小可憐,看著自己帶過來的空間,她不由勾唇笑了,這極品家人不要也罷; 幫助母親與出軌父親離婚,帶著母親和妹妹離開吸血的極品一家人,自此開啟美好新生活。 母親刺繡,妹妹讀書,至于她……自然是將事業做的風生水起, 不過這高嶺之花的美少年怎麼總是圍著她轉, 還有那麼多優秀男人想要給她當爹,更有家世顯赫的老爺子找上門來,成了她的親外公; 且看唐霜在年代從無到有的精彩人生。
121.5萬字8 68733 -
完結2314 章

第一名媛:奈何嬌妻太會撩(盛莞莞凌霄)
“我愛的人一直都是白雪。”一句話,一場逃婚,讓海城第一名媛盛莞莞淪為笑話,六年的付出最終只換來一句“對不起”。盛莞莞淺笑,“我知道他一定會回來的,但是這一次,我不想再等了。”父親車禍昏迷不醒,奸人為上位種種逼迫,為保住父親辛苦創立的公司,盛莞莞將自己嫁給了海城人人“談虎色變”的男人。世人都說他六親不認、冷血無情,誰料這猛虎不但粘人,還是個護犢子,鑒婊能力一流。“世界上最幸福的事是什麼?”“哪怕全世界的人都說你不好,那個人依然把你當成心頭寶。”
426.6萬字8 39770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