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見春天》 第31章 第30章
魏清越只覺得心里大慟, 就是做文言文閱讀理解會遇到的“大慟”,洇在心口, 瞬間泛濫將人淹沒。他一直都不知道一個人遇到什麼,那顆心,才會“大慟”。
青春參差不齊,各人有各人的苦樂,但大部分人吃飽穿暖,家長的唯一要求就是你好好念書,就這,就這樣一大群人依舊過的不高興。
魏清越把書念好了,卻仍然只能這樣,他從不知道有人還會這麼想著他,孩子臉跟豬頭一樣可笑,他看看,又慢慢站了起來。
一句話都沒跟江渡說,魏清越跟張曉薔回到學校。
學校報了警,鬧到派出所,男人嚷著要做親子鑒定,說什麼打孩子天經地義, 打自己孩子不犯法。
這麼囂張的一個男人有著一個再普通不過的名字, 王勇。
王勇有前科,當年因為強干獄, 十年, 后來又因為盜竊獄,這次剛出來沒多久。
主任告訴警察,江渡的檔案資料里并沒有填父母的信息,只有兩個老人的。
“警察同志, 現在你知道我為什麼打孩子了吧,不認……”王勇很猾,滿歪理,民警呵了他一聲,嚴厲說:“再是你的孩子,你這麼打也是犯法的,我知道什麼,你知道什麼?!嗯?”
最終王勇被拘留。
江渡請了整整一周的假,住院兩天,剩下幾天回了家。
學校里到拉滿了橫幅,紅紅的,那麼長,從頂樓一直飄到一樓,上面寫著振人心的話,好像一手,就真的到明的未來。
倒計時很快就會從兩位數變個位數,城市卻像進梅雨季,說是中雨,可下起來,激流從公車玻璃上傾瀉,打碎霓虹,一灘淌的杏子紅煙霧藍,街邊傳來蔥羊的焦香。
Advertisement
江渡的傷開始結痂,外婆不讓摳,怕留疤,但疤這種東西,并不是只留皮的。
沒人提那天的事,聽見外婆在屋里抑地哭,一地煙頭,是外公的,他說了句“造孽”,然后就是一聲長長的嘆息。
吃飯的時候,外婆幾次想張口,都吞咽下去了,外頭雨聲越來越
急,洗著新綠的桂花樹。
“寶寶,有件事想跟你商量,”外婆雖然端著碗,但里頭的米,幾乎沒,手里筷子張著,像各自為政的兩個破折號,“我跟你外公想把房子賣了,換個地方住,梅中那邊我們也問過了,可以轉學,保留學籍,你到時高考可以回梅中考,不耽誤事。”
飯桌上,外公今天不在,外婆說他去見一個老朋友去了。江渡猜,外公不知道在為什麼事奔波。
雨好大啊。
“我們又沒做錯事,為什麼要搬家?我為什麼要轉學?”江渡眼睛里涌出淚水,不懂,不懂的事太多了,世界變了嗎?也許,這個世界本來就是這個樣子,只不過,以前不知道而已。
外婆不作聲了,手微微著。
有些事,江渡一個字都沒問,沒問就可以裝作是假的,沒發生過。
飯桌上,沒說笑聲了,吃的很苦。
外面忽然傳來敲門聲,祖孫倆,都是渾一,對視一眼,還是外婆先站了起來,走到門前,在貓眼那觀察一番,轉頭對江渡說:
“是同學,就是那個送你回家的同學。”
雨這麼大,魏清越來找了。
一瞬間,心無從名之,魏清越永遠跟其他人不一樣,他考第一,是世俗的好孩子,但他煙打架,總是沒被馴服的樣子。開學典禮是所有學生的偶像,可以送回家,還能狂揍變態。他的背面,卻站著不能逾越的父權,他一兩面,江渡想,自己對他也許未必有什麼重大意義,只不過,自己恰巧為他行為中的一部分,格使然。
生走過來,把門打開,看到的,是男生那一瞬間抬起的臉,眼睛清澈,頭發被淋得霧霧的,球鞋是黑的,已經。
他穿了件條紋長袖,休閑牛仔也是黑的,不知道了沒。
“給,你們班這段時間發的講義還有試卷。”魏清越把一個包裝嚴實的塑料袋遞過來,“你同桌給你復印的各科筆記,說可能你們沒怎麼說過話,希你早日康復。”
江渡臉白得詭異,薄薄的,明的,好像紙片都能劃出殷紅的來
。接過塑料袋,抱在懷里,抵在下頜,眼睛閃爍不定有些陌生地看著他,沒說話。
“孩子,要不進來坐坐?”外婆站在江渡后,對魏清越出一略顯局促又莫名張的笑容,老人像變了個人,失去了往日那自然而然的熱洋溢。
魏清越微微一笑,很淡,他那雙眼睛黑黝黝的,無話時,漉漉的頭發遮的眉眼卻像有話要講。
“別站外頭,進家喝杯茶再走,你看,下這麼大雨還給江渡送資料來了。”外婆努力找著話,讓魏清越進來。
江渡往后退退,彎腰給他找了雙拖鞋,然后,看他把傘放在了玄關那,雨珠滴下,很像眼淚。
兩人坐的客廳沙發,外婆找出茶葉,用一次紙杯接了熱水。
“你們聊,我去收拾收拾廚房,對了,孩子,你吃飯了嗎?”外婆一邊掛圍,一邊問他,魏清越連忙說自己已經吃過了。
外婆就賠笑般“哦哦”了兩聲,去了廚房。
一時間,只能聽到臺的雨聲,幕天席地,讓人產生河水要漫過河床的錯覺。
“你要是有什麼不會的題目,可以問我。”魏清越握著紙杯,抿滾燙的水。
江渡笑了下,很短暫,眼睛看著他的長袖,猜的卻是魏清越一定挨打了,他手臂上一定都是傷痕,很丑,所以才不給人看見,就像,躲在家里,還不知道怎麼積攢勇氣再回學校。
忽然站起來,把外公搞到的治疤痕特效藥膏拿給魏清越,魏清越果然愣了下,他竟然笑了,接到手里,看了兩眼,表還是那樣無所謂:
“謝了。”
“軍訓那會兒,你怎麼天天坐場邊?”他好像是隨便找了個話題,就開聊了,沒問你好些了嗎,也沒說什麼開導的話。
江渡臉上又是那種靦腆的樣子,說:“我從小心臟不好,上面有,不能劇烈運。”
說到這,看向魏清越的臉,忽然就知道在哪兒了,約約疼著,但奇怪的是,他就坐在眼前,同時變得溫而鮮明,有呼呼的春風,往里面灌,又繾綣又纏綿,直到把全部灌滿,再生長出青青的
草,的花,上頭是很亮的天。
魏清越沒接話,只是又抿了口熱茶。茶幾上,放著兩本科普讀,他隨手一翻,問:“喜歡看科普?”
“我喜歡無用又有趣的知識。”江渡的聲音終于活潑一點。
魏清越笑笑:“什麼無用又有趣的知識?”
“我小學的時候喜歡反復含草,看它合上,那時我就想知道為什麼這麼神奇。知道含草閉合的原理,沒什麼用,但很有趣,大概就是這樣。”江渡娓娓道來,其實有點累,那種小心翼翼想要維持和尋常朋友說話狀態的累,但今天很高興。
魏清越手底迅速翻著書,像洗撲克牌那樣:“那巧了,我一肚子這樣無用又有趣的知識,你有什麼想知道的,都可以問我。”男生對笑時,眼神里閃著些戲謔,還有些別的東西。
江渡抿了抿,也淺淺笑了,兩手搭在沙發布上,輕輕挲兩下,說:“我都沒好好跟你說謝謝。”
說著往廚房方向看了一眼,外婆走過去,悄悄進了和外公的房間,把門掩了。
“我其實沒你想的那麼高尚,”魏清越說,“那天,我那麼做不純粹是因為你,我很討厭暴力,但我發現,我跟魏振東還真是有的一像,你不知道我有多討厭他,我像誰不好?非得像魏振東。”
江渡都聽老師說了,魏清越想把人勒死,沒勒,有十分的話,一般只能跟他說到一分,可這一刻,必須把話都說出來。
“魏清越,你以后別這樣了。”江渡說,“我以前看書上寫,人心里有頭猛虎,你得學會控制他,不能被他吞噬了。我在想,人做事得有個邊界,一旦超過那個邊界就不好了,這個不好,主要是對自己。你如果把那個……”忽然強烈地抖了一下,“把人打死了,可能我們現在年紀還不夠坐牢,我不太懂法律,可是如果我們滿十八歲了,是要負法律責任的,無論如何,不值得,我的意思是,你這麼好,不該為這種事糟蹋自己的前程。”
“看不出,你跟老師一樣,這麼說教,我哪兒好了?怎麼我自
己不知道。”魏清越半真半假地說,他笑的。
江渡的眼神黯下去,勉強笑笑:“我真是這麼想的。”
他就繼續低頭喝茶,好像茶里不知有什麼了不得的滋味一樣,熱氣撲到臉上,眉眼都要被潤化了。
“好,那我聽你的。”魏清越非常干脆,他又沖笑,看見出的胳膊,細細的,白白的,手臂上有兩個紅點,紅點旁,是結的紫黑痂。
他指了下,說的紅點:“蚊子咬的啊?”
江渡“嗯”一聲,也低頭看看,問他:“為什麼蚊子咬人之后會有包呢?”
“因為蚊子在咬你的時候,會朝你皮里注一種抗凝質,這種東西,被人免疫系統識別,簡單說,就是雙方打起來了,從而導致過敏反應。”魏清越的眼睛像被風吹過的稻浪,一片凸明,一片凹暗,外頭亮起一道閃電,極快的,碾著桂花樹葉子過去了。
江渡點點頭,好像很欣:“無用有趣的知識又增加了。”
雨可真大,風也跟著大起來,的枝葉被吹開,出一方烏暗,黑云洶涌。客廳線越來越,人坐在那兒,只有個大致的廓。
“好像夏天啊。”江渡輕聲自語,魏清越說,“立夏早過了,確實是夏天。”
“我每次都覺得春天沒過完,好像暑假才是夏天,吃雪糕,吹空調,還能睡長長的午覺。否則,不夏天。”江渡正經八面地說。
魏清越出了汗,被茶頂的,他笑,覺得江渡特別有意思,人就得這麼過每一天,跟有意思的人呆一塊兒。
他問:“想過以后做什麼沒?”
“我想當記者,或者雜志編輯,你呢?”江渡的心和外面天氣逐漸背道而馳,輕快地問起他。
“我啊,我就做你的采訪對象。”魏清越接的特別順其自然,“你問我什麼,我都會回答你,不會難為你。”
江渡手背掩,笑了。
笑著笑著,察覺到自己緒太外了,慢慢收起笑容,一時沒話說,空氣緩慢而沉默地尷尬著。
魏清越是真的怕熱,他不覺挽起了袖口,猙獰傷痕了一鱗半爪,江渡的目,便
自偏移過去。
“我爸跟我媽關系很差,天天吵,我習慣了。”魏清越順著的目落到自己小臂上,說起自己的事,“他們吵他們的,我該吃飯吃飯,該寫作業寫作業。后來,兩人離婚,我跟了魏振東。他自卑,你可能不懂一個男人的自卑,我媽是高材生,家庭條件優越,他念書腦子不好使智商欠費,但會做生意,我媽覺得他這個人鄙沒文化,很看不起他。他就一直找人,換人,證明人都喜歡他。家里買一堆古董,名人字畫,西裝革履地去看展,我懷疑他什麼都看不懂。除了掙錢找人,他最大喜好就是打我,他越是手舞足蹈地在那咆哮,我越是無于衷,這對我沒用,魏振東總想著讓我認錯,他瘋魔了,好像把我制住了,就等于間接制住了他搞不定的原配,我也是花很長時間才弄明白魏振東為什麼瘋狂打我。”
話很長,但語氣很輕飄。
魏清越說完,笑著問:“是不是很可笑?”
江渡靜靜說:“忘掉這些不好的事吧,你很快就能擺你爸爸了,你會過上好日子的。”
魏清越先是被這麼樸素的話逗樂一瞬,猶豫了片刻,著紙杯:“是,大概暑假結束我就要去國了,我等這天很久。”說到這,那種明明該欣喜若狂夢想真的覺,反而像被稀釋的空氣,幾乎尋覓不到。好像“我等這天很久”只是覺得該表達一下說出來而已,緒并沒有變得濃烈。
這麼快……江渡低著頭,好大一會兒都好像是在聽雨聲。
終于抬起頭:“那真好,你會念特別厲害的大學,對吧?”
“你也會的。”魏清越避開的目,往臺方向看了看,“雨好像小了點。”
“嗯,好像小了點。”江渡也往外看看。
“你什麼時候回學校?”魏清越清清嗓音。
江渡卻搖搖頭:“我不知道,外公外婆想搬家,讓我轉學,我也不知道我還去不去梅中。”
魏清越手中的紙杯慢慢變形。
他說:“你要轉學了?是因為……這個事嗎?”
江渡眼睛紅了,扭過頭,
慶幸這是個雨天線不好。不想讓人覺得自己看起來文弱,格也跟著弱。
“是吧,我不想離開梅中,但如果外公外婆堅持,我會聽他們的。”
魏清越半天不吭聲,忽然站起來:“我該走了,你不用轉學,再等等。”
江渡有點慌地跟著起,外面雨沒停,魏清越匆匆換了鞋,拿起傘,轉看看,說:“別送了。”
“今天謝謝你給我送資料。”江渡小聲說。
魏清越笑笑:“你好好用功,功課別落下了。”
他撐起傘,邁出那道防盜門,江渡穿著拖鞋,站在門口寫著“出平安”的紅墊子上,看魏清越往單元門走去。
他出單元門時,回頭又看了一眼,沒招手,也沒說話,轉走進了風雨中。
猜你喜歡
-
完結70 章

我愛你,我裝的
寧思音的未婚夫是蔣家最有希望繼承家產的曾孫,無奈被一個小嫩模迷了魂,寧死也要取消婚約,讓寧思音成了名媛圈的笑柄。 蔣家老爺子為了彌補,將家里一眾適齡未婚男青年召集起來,供她任意挑選。 寧思音像皇上選妃一樣閱覽一圈,指著老爺子身邊長得最好看最妖孽的那個:“我要他。” 前未婚夫一臉便秘:“……那是我三爺爺。” - 蔣老爺子去世,最玩世不恭的小三爺繼承家業,未婚妻寧思音一躍成為整個蔣家地位最高的女人。 嫁進蔣家后,寧思音的小日子過得很滋潤。住宮殿,坐林肯,每個月的零花錢九位數,還不用伺候塑料假老公,她的生活除了購物就是追星,每天被晚輩們尊稱奶奶。 唯一的不便是,作為蔣家女主人,在外要端莊優雅,時時注意儀態。 忍了幾個月,趁蔣措出差,寧思音戴上口罩帽子偷偷去看墻頭的演唱會。 坐在下面喊得聲嘶力竭:“寶貝我愛你!” 后領子被揪住,本該在外地的蔣措將她拎上車,笑容涼薄:“再說一遍,你愛誰。” *白切黑狡詐小公主VS美強慘陰險大BOSS *我以為我老公歲月靜好沒想到心狠手辣,呵,陰險/我老婆表面上單純無邪背地里鬼計多端,嘖,可愛 *本文又名:《震驚!妙齡少女嫁給前男友的爺爺》《前男友成了我孫子》《豪門奶奶的幸福生活》 【排雷】 *黑心夫妻二人組 *非典型瑪麗蘇,一切設定為劇情服務 *人多記不住的,蔣家家譜見@碳烤八字眉
26.2萬字8 14514 -
完結115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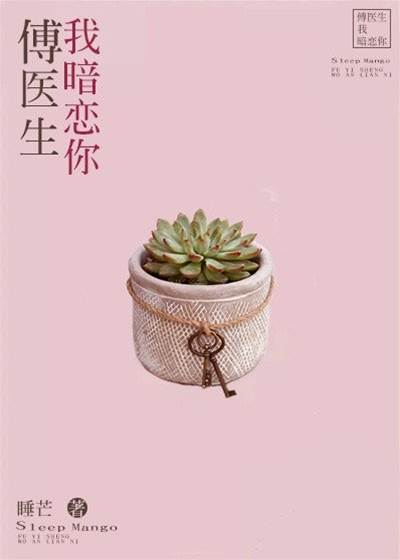
傅醫生我暗戀你
暗戀傅醫生的第十年,林天得知男神是彎的! 彎的!!!! 暗戀成真小甜餅,攻受都是男神,甜度max!!!! 高冷會撩醫生攻x軟萌富三代受 總結來說就是暗戀被發現後攻瘋狂撩受,而受很挫地撩攻還自以為很成功的故事……
44.4萬字8 7391 -
完結561 章
快穿:白月光渣過的男主全瘋了
(已完結)【1v1雙潔+甜寵+女主白月光】【病嬌瘋批+修羅場+全HE】作為世界管理局的優秀員工沐恬恬,本該退休享受時,突然被警告過往的任務世界全部即將崩壞?!那些被她傷過的男主們充滿恨意哀怨的看著她…冷情江少眸色晦暗,“恬恬,既然回來就別再想離開,不然我不知道我會做出什麼…”頂流偶像低聲誘哄,“跟我回家,我照顧你…”這次他絕不能再讓她離開…瘋批竹馬展露手腕劃痕,“如果你再拋下我,下次,我一定死給你看…”精分暴君看到她頸肩紅痕,眼尾殷紅,“你怎麼能讓別人碰你?”沐恬恬,“我沒…唔~”天地良心,她從始至終只有他一個人啊!沐恬恬本以為自己死定了,結果腰廢了。已完成:①冷情江少燥郁難安②頂流偶像醋意大發③邪佞國師權傾朝野④病嬌始祖上癮難戒⑤黑化魔尊囚她入懷⑥天才竹馬學神校霸⑦精分暴君三重囚愛末日尸皇、忠犬影帝、偏執總裁、妖僧狐貍、病態人魚、黑化徒弟、虛擬游戲、腹黑攝政王、殘疾總裁、無上邪尊。有婚后甜蜜番外,有娃,喜歡所有世界he的小伙伴不要錯過~
98.4萬字8 5079 -
完結337 章

南小姐別虐了,沈總已被虐死
沈希衍很早以前,警告過南淺,騙他的下場,就是碎屍萬段。偏偏南淺騙了他,對他好,是裝出來的,說愛他,也是假的。從一開始,南淺的掏心掏肺,不過是一場蓄謀已久的陰謀。她裹著蜜糖的愛,看似情真意切的喜歡,隻是為了毀掉他。當所有真相擺在沈希衍麵前,他是想將她碎屍萬段,可他……無法自拔愛上了她。愛到發瘋,愛到一無所有,他也無怨無悔的,守在她的房門前,求她愛他一次,她卻始終不為所動。直到他家破人亡,直到她要和別人結婚,沈希衍才幡然醒悟,原來不愛他的人,是怎麼都會不愛的。沈希衍收起一切卑微姿態,在南淺結婚當天,淋著大雨,攔下婚車。他像地獄裏爬出來的惡鬼,猩紅著眼睛,死死凝著坐在車裏的南淺。“兩年,我一定會讓你付出代價!”他說到做到,僅僅兩年時間,沈希衍就帶著華爾街新貴的名頭,席卷而來。但,他的歸來,意味著——南淺,死期將至。
69.2萬字8.46 11142 -
完結445 章

離婚後,千億前妻驚豔全球
她把所有的愛情都給了傅西城,可是三年,她也沒能融化了男人的心。“我們離婚吧。”江暮軟一紙離婚證書,消失在了男人的世界。離婚之後,她消失的幹幹淨淨,可是傅西城慌了。追妻漫漫……傅西城發現,原來自己曾經拋棄的女人不僅僅是財閥大佬這麽簡單……
77.6萬字8 25215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