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染》 第74章 把他送進了局子
明佑強撐起,手掌輕拍幾下。
眼裡陌生的疏離令傅染驚怔,他陡然大笑出口,線條僵的側臉落傅染眼中,竟是無限惆悵。
「為什麼我就是不死心?」
他沒頭沒腦的一句話。
傅染喟然低嘆,「我打電話讓王叔送你回去。」
「你要回去嗎?來,我送你。」明佑上前扣住傅染的手腕。
緒激地甩開,「瘋子,我自己會回去。」
「還是我送你吧!」明佑再度去抓傅染的手,驚退開,上次的事仍記憶猶新,「別我。」
才退兩步,明佑已大步來到跟前。
傅染想回到車,但男人卻擋著不肯讓道。
彷徨恐懼,揚起手機嚇他,「你再這樣我報警了!」
「你報啊,」明佑兩眼赤紅,「看看小爺怕不怕你!」
話語方落定,人便撲了出去。
傅染拔往後跑,卻被明佑一把按住在了橋墩上。
腹部抵住堅的石塊,疼得後背冒出冷汗,「放開我。」
明佑的臉埋在傅染背後,他冷不丁張開重重咬口。
傅染倒吸口冷氣,兩人間合幾乎不見隙。
無力從四肢襲來,傅染臉微微側去,「我哪怕撞到了你,我都不該停車的。」
他呼吸縈繞在傅染頸間,忽然出手去奪的手機。
「你不是要報警嗎,我看你怎麼報!」
傅染下被得死死的,手臂出去才不至於被明佑搶掉電話。
Advertisement
他出的手裹住前,越收越,傅染趕忙按鍵,「快鬆手,不然我真的報警。」
明佑兩手改摟住傅染的腰,臉埋頸間,突如其來的涼意順領口灌。
手機另一頭接通,「喂,您好,這裡是……」
傅染用力推了下,見他仍然不鬆手,且作越來越不規矩。
「您好,我要報警,」找個理由,「這兒有人酒後駕駛。」
後難得有行人經過,只當小兩口浪漫才會在這大冬天的抱著在橋邊吹冷風。
直到警車的鳴笛聲由遠及近,傅染才驚覺,玩大了。
明佑維持先前的姿勢不,呼吸沉穩,倒像是睡的樣子。
一名年輕的警察了眼,這兒彷彿只有他們二人,他神疑慮,「請問……」
傅染後的明佑,「他,他酒駕。」
另一名警察見況不對,「居然醉酒,深夜耍流氓?」
「不是不是……」傅染擺手,「沒有耍流氓。」
「你們什麼關係?」警察上前扳住明佑的肩膀,將他從傅染上拉開,年輕男子顯然沒認出他來。
傅染急忙解釋,「我們是朋友。」
「男朋友?」
「不是,普通……」
「是我老婆。」明佑道。
「我不是!」
警拿眼斜向傅染,「報警電話是你打的吧?」
傅染老實點頭,「是。」
另一名警拿來測試酒駕的儀放到明佑邊,「含住,用力吹氣。」
他抿不配合,傅染有些懵,看這架勢像是來真的。
但明佑不是狂妄地說警察局是他家開的嗎?儘管落魄但也不至於真的被查吧?
「含住,用力吹氣。」警不耐重複。
明佑十分不願地指了指旁邊的傅染,說話刻意表現出大舌頭,「這活……這活都我老婆晚上做,你讓吹。」
傅染瞠目結舌,兩個年輕的警面面相覷,臉部泛出可疑的紅。
其中一人把儀收回去,「這酒味聞都聞得出來,肯定是醉酒駕駛,走,帶回去理。」
傅染見真鬧出事,忙攔在跟前,「不好意思,我是開玩笑的,我不報警了。」
「你當警察局是你家開的?他這樣肯定有問題,待會我們回去還要調取路面監控,看是不是真的在醉酒狀態下駕駛,走吧。」
兩人拉著明佑上警車。
傅染急的跟去,「那你們會怎樣理?」
「一旦屬實,吊銷駕駛證,還要拘留和罰款。」
拘留?
明佑倒也乖,可能真的是酒喝多了,竟然跟著上了車。
傅染不假思索拉開車門進去,就這樣作繭自縛跟去了警大隊。
兩人耷拉腦袋出來,時針已掃向凌晨。
傅染在前面焦急地走,明佑經過方才一鬧也徹底醒酒,慢慢在後面跟著。
全翻遍除了手機沒找到一錢,傅染杵在路口,待明佑走近后沒好氣開口,「有錢嗎?」
他翻翻口袋,無分文。
這麼晚也拉不下臉喊誰過來接。
「不說你都能搞定嗎?我只不過打個電話嚇唬你,你還差點真的被扔進局子。」
繼續往前走,卻遲遲沒等到跟來的腳步聲。
傅染驚疑地向後,只見明佑站在十步之外,落寞寂寥的夜,染得男子雙肩微微抖。
他目鎖定傅染,一道長長的影子直拉到腳邊,「傅染,我說的是之前的明三。」
只一句話,便泄了氣。
「走吧,我們停車的地方離這有幾公里。」傅染到底心有不忍,途徑一個賣烤紅薯的小攤,明佑站定后不肯走。
「要來一個嗎?賣完我就收攤了。」
傅染走回明佑旁,「你有錢嗎?」
他搖頭。
傅染再掏一遍口袋,「我也沒有。」
攤主眼見這兩人都沒錢,僅有的興緻也全無了。
明佑卻依舊杵著不走,「還記得你送我的第一份禮嗎?」
他喊小氣鬼,因為在他權利登天的時候,送他的禮是半個烤紅薯。
傅染拉起明佑的手往前走,他回握住,直到把的手出紅痕。
「明佑,」傅染嗓音微,無以名狀的悲傷沁心間,「為什麼你有時候會像個孩子呢?」
後的男人沒有答話,一前一後兩道影子親昵地偎在一起。
但影子終只是影子而已,就不了現實的。
午夜過後,清冷的街頭,連車駛過的聲音都不再聽到,皮鞋踩著冷地面發出錯而有序的咯噔聲,遠遠能看到車頭相對的兩輛車。
「我讓王叔過來接你吧。」
「用不著。」
「可你的駕照……」
傅染走到明佑車旁,吃驚地見到他的車門沒鎖,拉開門探進去。
只見裡頭被翻得凌無比,別說是錢包,就連紙巾盒,乃至能拆的東西都拆沒了,真皮坐椅被利劃得無完,遭賊了。
「你怎麼不知道鎖?」
明佑無所謂地攤開手掌,「你報警報那麼急,我好像看到你也沒鎖。」
「是麼?」傅染完全記不清有沒有按那一下。
著急跑到自己的車前,可不是嗎,車門還敞著條,毋庸置疑,遭到了跟明佑相同的待遇。
氣得差點口。
猜你喜歡
-
連載0 章
嬌寵甜妻鬨翻天
前生,她心瞎眼盲,錯信狗男女,踏上作死征程。 沒想到老天開眼,給了她重活的機會。不好意思,本小姐智商上線了!抱緊霸道老公的大腿,揚起小臉討好的笑,“老公,有人欺負我!” 男人輕撫她絕美的小臉,迷人的雙眸泛著危險,“有事叫老公,沒事叫狗賊?” 寧萌萌頭搖的如同撥浪鼓,並且霸道的宣告,“不不不,我是狗賊!” 男人心情瞬間轉晴,“嗯,我的狗我護著,誰虐你,虐回去!” 從此,寧萌萌橫著走!想欺負她?看她怎麼施展三十六計玩轉一群渣渣!
246.6萬字8 59408 -
完結518 章

團寵女鵝是偏執大佬的白月光
錦城豪門姜家收養了一對姐妹花,妹妹姜凡月懂事大方,才貌雙全,姐姐姜折不學無術,一事無成。窮困潦倒的親生家庭找上門來,姜家迫不及待的將姜折打包送走,留下姜凡月;家產、名聲、千金大小姐的身份、未婚夫,從此以后盡數跟姜折毫無關系。.姜折踏入自己家…
95.4萬字5 132471 -
完結1752 章

腹黑萌寶,總裁爹地寵入骨
溫酒酒愛了傅司忱十年,結婚后傅司忱卻因為誤會選擇了其他女人。當他帶著帶著大肚子的林柔柔回來之后,溫酒酒失望至極,決心離婚。挺著一個大肚子,溫酒酒一尸三命。五年后,溫酒酒以大佬身份帶著兩只小萌寶回歸。瘋了五年的傅司忱將她抓回家中:“我們還沒離婚,你生也是我的人,死也是我的人!”當看到兩只翻版小萌寶時,傅司忱急了,“你們是誰?別搶我老婆!”
162.3萬字8 399611 -
完結1685 章
愛上你劫數難逃
一場代嫁,她嫁給了患有腿疾卻權勢滔天的男人。“我夜莫深不會要一個帶著野種的女人。”本以為是一場交易婚姻,誰知她竟丟了心,兜兜轉轉,她傷心離開。多年後,跟他長得一模一樣的小正太一巴掌拍在夜莫深的腦袋上。“混蛋爹地,你說誰是野種?”
303.9萬字8 22992 -
完結199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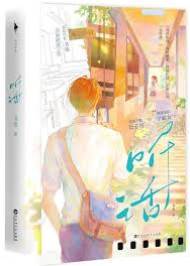
聽話
那不是程歲寧第一次見周溫宴。 她見過他意氣風發,見過他浪蕩不羈,見過他懷裏女孩換了一個又一個。 只是那次,她心動最難捱。 那天室友生日她走錯包間,偶然窺見他懶懶陷在沙發裏,百無聊賴撥弄打火機。 火苗忽明忽暗身旁女生和他說話,他勾着笑半天敷衍回個一字半句。 她回到包廂裏第一次鬼迷心竅主動給他發了信息,【今天聚會好玩嗎?】 下一秒,他回:【你不在沒意思。】 後來他們分手,多年後在風雨裏重逢,她被男友差遣輕視狼狽不堪。 他跨過一衆圍着他殷勤討好的人羣,不顧目光,拉住她的手,塞進一把傘。 冬夜昏天暗地光線裏,他垂眼看她,聲音淡淡:“撐傘,別淋雨。” 那一刻她這才知道,除了他以外都是將就。 朋友問那再後來呢?她淺笑着沒說話。 只是每年西園寺,雲蒸霞蔚煙火繚繞的銀杏樹下多了個虔誠的少女。 那天年初一,青衣僧人說有緣人贈了她一張紙條。 展開一看,字體熟悉,上面寫着‘一歲一禮,得償所願。’ 她下意識回頭,人海茫茫裏,一眼只看見他溫柔背影。
34.2萬字8.18 6017 -
完結94 章

他的鳶尾
【先婚后愛】【蓄謀已久】【暗戀】【甜文】【雙潔】裴琛是京城有名的紈绔子弟,情場浪蕩子,突然一反常態的答應貴圈子弟最不屑的聯姻。結婚后,他每天晚出早歸,活脫脫被婚姻束縛了自由。貴圈子弟嘩然,阮鳶竟然是只母老虎。原本以為只是短暫的商業聯姻,阮鳶對裴琛三不管,不管他吃,不管他睡,不管他外面鶯鶯燕燕。后來某一天,裴琛喝醉了酒,將她堵在墻角,面紅耳赤怒道:我喜歡你十六年了,你是不是眼瞎看不見?阮鳶:……你是不是認錯人了?我是阮鳶。裴琛:我眼睛沒瞎,裴太太。
31.8萬字8.18 7381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