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姐》 第二百三十二章 催漕和紛爭
又是忙忙的一天,天黑了,李月姐和鄭典才回到衙門後堂。
隻是兩人才剛坐下,還沒來得及休息,就有衙差急匆匆的來報,朝廷特使來了。
“快,月姐兒,幫我換上服。”鄭典一聽朝廷特使,哪裏敢耽擱,連忙起,換了服,李月姐在一邊幫他整理著領,卻是一額臉忐忑的道:“朝廷特使這時候來幹什麽?”
“我也不曉得,看看再說吧。”鄭典道,然後急匆匆的到前衙去了。
“好,你慢點兒。”李月姐看著他急急的腳步,不由的了聲。隻是鄭典一拐彎已經看不見人影了。
李月姐才回屋,焦灼的走來走去,不知這時候朝廷特使來幹什麽?
“夫人,熱水我準備好了,洗漱一下吧,你累了一天了。”這時,青蟬上前道。
“嗯。”李月姐應了聲,等到一切收拾好,鄭典還沒有回來,李月姐有些坐不住了:“走,青蟬,我們去前麵瞧瞧,怎麽老爺這麽久還不回來。”
“嗯,我掌燈。”青蟬應著,點了一盞氣死風燈,兩人正準備出屋,迎頭就看到鄭典回來了,那臉卻是很不好看。
“怎麽啦?”李月姐連忙掇著腳步問。
鄭典回頭,在燈下細細的看著李月姐。
“怎麽回事啊?越來越神叨了你。”李月姐急的沒好氣的跺腳。
“是三貴,他帶來了聖旨和朝廷文書,讓我馬上放下衙裏的事,南下催漕。”鄭典歎著氣道。所謂催漕,在因天災人禍,使得運河上漕糧運輸遇阻時,朝廷派員下去,督促漕糧及時運達。催漕這不是一個常設的職,但一遇天災人禍就有。
李月姐一聽,臉大變,隻覺得兩有些發,然後一臉蒼白咬著牙道:“這怎麽行,南邊淮安一團,聽說連臨清那邊也都開始了,你這一去豈不是往虎口裏投。”
Advertisement
“聖命難違,再說了,我也想去淮安一趟,我大伯和三哥不能這麽白死。”鄭典兩眼亮的道。
一聽鄭典這麽說,李月姐便知道此行定局了。
“決定了?”李月姐咬著問。
“決定了。”鄭典重重的點頭。
“什麽時候?”李月姐又問。
“明日一早。”鄭典道。
李月姐不啃聲了,坐在一邊生著悶氣,心裏恨不得咬那刻薄的皇帝一口,這也太不近人了。鄭家剛在淮安那邊剛死了兩人呢,這又上桿子送過去一個。
“月姐兒,別擔心,我會照顧好自己的,三貴還給了我一塊皇上賜的玉佩,能調運河沿岸各衛所衛軍的,還有便宜行事之權,我這下去,雖隻是個催漕,卻有著欽差大臣之權呢,多人都羨慕不來,再說了, 這回我又升一品,如今是六品了,要是差事完的好,說不定還能再升一級,到那時你可真正是太太了。”鄭典討好的道。
“呸,誰稀罕太太來著,我隻要你平安。”李月姐沒好氣的道。
“我知道,我知道,你放心,我絕對會全須全尾的回來。”鄭典科打諢。
事已是這樣,李月姐再急再不甘願也是白搭,想著鄭典明日一早就要走,便忙活著幫他打點行裝。
鄭典又連夜去了大宅那邊,他這一去,怕是來不及參加大伯的下葬禮了,得跟家裏人打個招呼,另外,還要跟那兄弟幾個再細細問問江淮那邊的事,好心裏有數。
接下來一夜纏綿,自不必說,鄭典似乎要把接來幾個月的分兒做足似的,貪的讓人咋舌。
第二天鄭典便,李月姐送他到碼頭,又拉著他的長隨石三到一邊道:“石三,老爺我可就給你了,一應事,你都要仔細著,要是回來的時候一油皮,我就唯你是問。”
“夫人放心,石三把腦袋撂這裏了。”石三拍著脯保證。
“行了,說沒用,看表現,看結果。”李月姐道。
“嗯,夫人瞧著吧。”石三再次保證。
得了他的保證,李月姐才稍稍放心些,又細細叮囑鄭典一番。
“其實比起我南下,我倒更擔心家裏,月姐兒,我這一走,家裏的事可就給你了,大伯娘和三嫂子偏,是不住家裏其他幾房的,你得給們撐腰,你別怕輩份低,到底是朝廷六品孺人,你做什麽都不出格的。”鄭典低著聲衝著李月姐道。
“放心,我怕過什麽來著,定給你看好家。”李月姐瞪眼道。
鄭典瞧著李月姐瞪眼那悍樣,哈哈一笑,然後帶著石三上了船。
看著船揚帆遠去,李月姐才依依不舍的回衙門後堂。換了裳,還要去大宅那邊支應著。
晌午時候,李月姐剛送走了一些吊唁的客人眷,了個空,回屋裏休息一會兒,隻是一杯茶水還沒喝完,二房家的老小鐵水就顛顛的跑來,裏嚷嚷著:“六嫂,快去,打架了。”
“誰打架了?”。李月姐疑的問。
“我二哥和四哥。”鄭鐵水道
“為什麽打?”李月姐又問。
“我也不曉得,好象是漕上的事。”鐵水道。
一聽鐵水這話,李月姐臉就不太好看了,這些日子日日在大宅忙活著,鄭家二房和四房的幾個兄弟別的那點苗頭看的出來,這幾天,趁著接待吊唁客人的事,暗地裏卻是在拉攏人,為的還不就是那幫主大當家的位置。
李月姐還道他們也就暗地裏使使手段呢,沒想這會兒就明麵上打起來了,那隔天要不要帶著兄弟去壇口那邊打啊?那鄭家的臉皮還要不要了,真是越來越過份了。
“走,去看看。”李月姐讓鐵水帶路,朝著正屋那邊裏。一路走,卻一路在琢磨著,心裏有一種覺,鄭家這次怕是有**煩了。
鄭大伯一死,通州漕幫群龍無首,偏鄭家二房和四房的幾個兄弟都不是省油的燈,而尤其鄭四嬸子又是個見就鑽的主,幫裏這麽大的利益,為了幫主之位,為了漕中的利益份額,不得要爭奪一翻,而這還不是最壞的,反正鄭家兄弟不管如何爭,那壇口總是在鄭家手裏,最壞的是幫裏還有一個鐵九郎虎視眈眈,那更不是省油的燈,怕他到時來個漁翁得利,而最讓李月姐心驚跳的卻是柳銀翠。
柳銀翠腹中的孩子若是個兒還罷,但若是個男兒,再加上當日大伯當著全屯的人親口承認,那等於如今鄭家大房就這麽一個繼承人,這裏麵可作的東西就多了,那柳銀翠決不是一個安份的主兒,若是以這孩子宮的話,那鄭家這邊就被了,當然,反正大伯已死,當日柳銀翠也否認了的,鄭家人完全可以不認,可話又說回來,若是鐵梨鐵漢和鄭圭鄭癸鬧起紛爭,自顧不暇,漕上人心複雜的很,那柳銀翠這孩子就了一個最大的變數了,一個能讓外人手鄭家漕幫事的借口。
不行,這事,先得備上一手。
說起來,以前大伯在世的時候,李月姐雖然為大伯娘不平,但這畢竟是長輩們的事,不到心,自然是事不關已,高高掛起,從來沒把柳銀翠這事兒當事,可如今不一樣了,這個變數關係著鄭家在漕上的利益, 就不得不防。
嗯,看來,這段時間柳銀翠那裏得尤其注意點,讓月幫忙盯著,那丫頭機靈著呢。
須臾,李月姐同鐵水便到得正屋,就看到鄭鐵漢同鄭圭兩個俱是鼻青眼腫的,一邊鄭屠娘子還罵罵咧咧的,鄭屠則悶聲著旱煙,另一邊鄭四娘子正拉著鄭四兩個嘀嘀咕咕的,不知道在商量著什麽。
而前麵主位上,鄭大娘子臉也不太好看。
“這是怎麽了?”李月姐一進門就沉著臉問,然後走到大伯娘邊。
“六郎媳婦兒來了正好,你給做個主,大家一樣跑漕,憑什麽二房那邊多得兩船的夾帶。”那鄭四娘子見到李月姐進來,便嚷嚷的道。
“我那是為了安置壇口裏傷的兄弟,這回民,好些個壇口兄弟都傷了。”鄭鐵梨在一邊冷冷的道。
“呸,你要安置兄弟,我家鄭圭難道就不安置了?他手下兄弟也有不傷的呢。”鄭四娘子理直氣壯的道。
“那怎麽一樣,我這是要代表壇口安置他們。”鄭鐵梨臉鐵青。
“呸,你憑什麽代表壇口?”鄭四娘子不服氣的道。
“憑什麽?就憑鐵梨是鄭家第三代的老大,他不代表壇口誰代表。”一邊鄭屠娘子氣衝衝的道。
“嗬,這又不是鄭家立家主,這是壇口的事,若論資曆的話,我家鄭圭跟著他大伯跑漕的時候,你家鐵梨鐵漢還在柳窪修河渠呢……”鄭四嬸子一步不讓的道。
“咣當”一聲,一隻茶杯砸在了地上,碎片片。
所以的人都不由的看著李月姐,那茶杯之前正在李月姐的手上。
“啊,不好意識,手了,沒拿住,我讓青蟬收拾,你們繼續,這若是吵了還不夠,不如各自帶著兄弟去壇口那邊打,誰贏了誰就是幫主大當家的,多利索呀。”李月姐一臉淡淡的道。
……………………
謝zlx-清,塞德蘭的紅票。謝謝支持!!!!!!rs
猜你喜歡
-
完結188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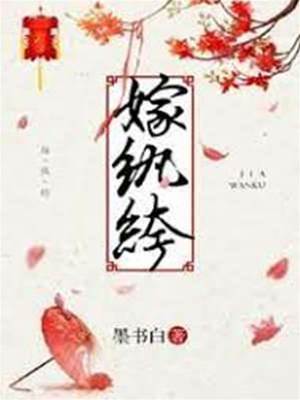
嫁紈绔
柳玉茹為了嫁給一個好夫婿,當了十五年的模范閨秀,卻在訂婚前夕,被逼嫁給了名滿揚州的紈绔顧九思。 嫁了這麼一人,算是毀了這輩子, 尤其是嫁過去之后才知道,這人也是被逼娶的她。 柳玉茹心死如灰,把自己關在房間里三天后,她悟了。 嫁了這樣的紈绔,還當什麼閨秀。 于是成婚第三天,這位出了名溫婉的閨秀抖著手、提著刀、用盡畢生勇氣上了青樓, 同爛醉如泥的顧九思說了一句—— 起來。 之后顧九思一生大起大落, 從落魄紈绔到官居一品,都是這女人站在他身邊, 用嬌弱又單薄的身子扶著他,同他說:“起來。” 于是哪怕他被人碎骨削肉,也要從泥濘中掙扎而起,咬牙背起她,走過這一生。 而對于柳玉茹而言,前十五年,她以為活著是為了找個好男人。 直到遇見顧九思,她才明白,一個好的男人會讓你知道,你活著,你只是為了你自己。 ——愿以此身血肉遮風擋雨,護她衣裙無塵,鬢角無霜。
81.5萬字8.46 50163 -
完結94 章

驚雀
虞錦乃靈州節度使虞家嫡女,身份尊貴,父兄疼愛,養成了個事事都要求精緻的嬌氣性子。 然而,家中一時生變,父兄征戰未歸生死未卜,繼母一改往日溫婉姿態,虞錦被逼上送往上京的聯姻花轎。 逃親途中,虞錦失足昏迷,清醒之後面對傳言中性情寡淡到女子都不敢輕易靠近的救命恩人南祁王,她思來想去,鼓起勇氣喊:「阿兄」 對上那雙寒眸,虞錦屏住呼吸,言辭懇切地胡諏道:「我頭好疼,記不得別的,只記得阿兄」 自此後,南祁王府多了個小小姐。 人在屋檐下,虞錦不得不收起往日的嬌貴做派,每日如履薄冰地單方面上演著兄妹情深。 只是演著演著,她發現沈卻好像演得比她還真。 久而久之,王府眾人驚覺,府中不像是多了個小小姐,倒像是多了個女主子。 後來,虞家父子凱旋。 虞錦聽到消息,收拾包袱欲悄聲離開。 就見候在牆側的男人淡淡道:「你想去哪兒」 虞錦嚇得崴了腳:「噢,看、看風景……」 沈卻將人抱進屋裡,俯身握住她的腳踝欲查看傷勢,虞錦連忙拒絕。 沈卻一本正經地輕飄飄說:「躲什麼,我不是你哥哥嗎」 虞錦:……TvT小劇場——節度使大人心痛不已,本以為自己那嬌滴滴的女兒必定過得凄慘無比,於是連夜快馬加鞭趕到南祁王府,卻見虞錦言行舉止間的那股子貴女做派,比之以往還要矯情。 面對節度使大人的滿臉驚疑,沈卻淡定道:「無妨,姑娘家,沒那麼多規矩」 虞父:?自幼被立了無數規矩的小外甥女:???人間不值得。 -前世今生-我一定很愛她,在那些我忘記的歲月里。 閱讀指南:*前世今生,非重生。 *人設不完美,介意慎入。 立意:初心不改,黎明總在黑夜后。
21.3萬字7.83 21942 -
完結866 章

神醫魔后
21世紀玄脈傳人,一朝穿越,成了北齊國一品將軍府四小姐夜溫言。 父親枉死,母親下堂,老夫人翻臉無情落井下石,二叔二嬸手段用盡殺人滅口。 三姐搶她夫君,辱她爲妾。堂堂夜家的魔女,北齊第一美人,生生把自己活成了一個笑話。 她穿越而來,重活一世,笑話也要變成神話。飛花爲引,美強慘颯呼風喚雨! 魔醫現世,白骨生肉起死回生!終於,人人皆知夜家四小姐踏骨歸來,容貌傾國,卻也心狠手辣,世人避之不及。 卻偏有一人毫無畏懼逆流而上!夜溫言:你到底是個什麼性格?爲何人人都怕我,你卻非要纏着我? 師離淵:本尊心性天下皆知,沒人招惹我,怎麼都行,即便殺人放火也與我無關。 可誰若招惹了我,那我必須刨他家祖墳!
228.2萬字8 39455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