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蜜愛婚約:總裁離婚請簽字》 第582章 男人女人,厚此薄彼
紀母的臉冷了下來:「傅太太,你這是什麼意思,且不說紀家和傅家一直好,就連時年和我家紀南風也是過命的,我敬你是傅時年的太太才跟你好好說話,你可別給臉不要臉。」
「我的臉要不要不是由你說了算的。」蘇木冷冷的看著:「像你這樣的人,給我的臉面我也不敢要,怕走出去別人說我人面心,白白壞了我的招牌。」
「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我的意思你要是有一點點的良心就應該明白,你對江北做了什麼事,不用我一件件的告訴你,我就是念在你是紀南風的母親才沒有把話說的更難聽,在我還能忍得住之前,我勸你還是離開的好,否則大家的臉上都不會太好看。」
「我做什麼事了?」紀母並不認賬,但似乎有些心虛,所以嗓門倒是提高了不:「是不是江北那個賤人在你面前嚼舌了,傅太太,你不能聽一個人說啊,嫁給紀南風之前,跟別的男人可是同居了兩年的時間呢,這樣的人能夠進我們紀家的大門已經是給足了面子,還想怎麼樣?」
蘇木做了一個深呼吸,但是腔里的憤怒卻還是沒有緩解半分,笑了笑,開口道:
「同居兩年?這件事你們在結婚之前不知道嗎?江北有任何的瞞嗎?既然你們什麼都知道,當時也妥協和接了,那麼現在又有什麼資格在這裡說嫁給紀南風是你們施捨的結果?你們把自家當寶,可江北未必看在眼裡,兩年的時間都沒有讓你真正的了解江北,這是江北的悲哀,不該當時盲目的選擇紀家,從而悲慘了的婚姻。」
Advertisement
「傅太太,話可不是這麼說的。」
「那該怎麼說?你為長輩卻沒有一點長輩的樣子,張口閉口的說自己的兒媳婦是賤人,那麼你兒子呢?你說江北在外面和別的男人同居兩年,那麼你又計算過自己的兒子在外面糟蹋了多姑娘嗎?。」
紀母不是很贊的看了一眼蘇木:「男人和人怎麼能一樣?」
「呵。」蘇木冷笑出聲:「做人不能厚此薄彼,也不能太絕了,你在江北尚且不好的況下給的飯菜里下藥,強行要給做羊水穿刺,你有沒有想過的,你有沒有為肚子里的孩子想過?若是真有了什麼閃失,你打算怎麼辦?這個責任你負的起嗎?」
「那萬一懷的本不是南風的還自己呢?」紀母看著蘇木:「傅太太,你現在年紀太小,很多事都不懂,等你到了我這個年紀,你就會明白我為什麼要這麼做了。」
「我永遠不會為你這樣的人,因為你讓我看到了人最涼薄的一面,我現在終於明白為什麼江北那麼活潑開朗的一個人會變了如今這個模樣,你們紀家真是功不可沒。」
「你……」
「不過現在還不算太晚,你不是一直想要江北和紀南風離婚嗎?不是一直千方百計的想要拆散他們嗎?你不用再在這件事上費心思,江北會離婚的,希在正式和紀南風提出離婚之後,紀南風能同意,也不要再糾纏,僅此而已。」
紀母的眼亮了亮:
「你說真的?」
「當然是真的,紀家這個火坑還是越早逃出來越好,齊家的千金既然那麼想跳進去,我們也攔不住不是嗎?」
蘇木的話雖不好聽,但至紀母聽到了自己想要聽的,所以也沒有太過計較,微微笑了笑:
「既然傅太太都這麼說了,那我也就不打擾了,江北既然想在這裡住著就住著好了,等孩子生下來做了親子鑒定再說。」
紀母說完這句話就想離開,卻被蘇木手攔下:
「把話說清楚的好,你剛才說什麼?做親子鑒定?做完之後確定是紀南風的之後呢?你打算怎麼做?難不還想要回去由你們養不?」
「這是理所當然的啊。」紀母並不覺得自己的說辭有任何的問題:「如果真的是紀家的孩子,當然是由我們紀家養,江北有什麼能耐,再說了,自己待的孩子,我還不放心被帶什麼樣呢。」
蘇木心中的火氣抑了一次又一次,卻終究還是到了忍無可忍的地步,笑了笑,再開口卻是完全沒有留:
「我第一次見你這麼不要臉的人,你有什麼資格站在這裡,跟我理直氣壯的說出這樣的話,你們紀家養?江北期間你們紀家但凡有一個人盡到對一個孕婦該有的關心和護,江北現在也不至於是這個模樣,等辛辛苦苦十月懷胎生下孩子,你們不但不相信要去做親子鑒定,還想要孩子要回去?敢這個世界上所有的好事都讓你們紀家佔了是嗎?」
「我告訴你們,死了這條心,這個婚是離定了,這個孩子跟你們半錢關係沒有,等日後相見,我們彼此都要裝作不認識,畢竟跟你們做家人的這兩年會是江北這輩子都想抹去的污點。」
「傅太太!」紀母似乎也忍到了極限,還從未見過有人這麼猖狂的跟說過話:「我是看在傅家的面子上才跟你好聲好氣的說話,你以為你是誰?雖然說曾經和傅家有關係,但說到底現在還沒有復婚,說好聽了是傅太太,說難聽了不過是傅時年還沒玩夠,養在邊逗趣兒罷了,我勸你別太把自己當回事,否則等有一天被踢出傅家,日子怕是不會太好過。」
因為紀母的人品剛才蘇木也算是有了見識,所以此時說什麼話都不能引起蘇木的波瀾,也沒想過要為自己扳回什麼,畢竟此刻最在乎的是江北,只要江北沒有收到傷害,其他的都可以看在傅時年和紀南風的面子上既往不咎。
但蘇木不追究,不代表傅時年也不追究,轉想要回到車上的時候,聽到後傳來一聲不太友善的聲音:
「我傅時年這輩子只娶一個人,這個人只能是蘇木。」
猜你喜歡
-
完結1099 章

寵妻NO.1:霍少,親夠沒!
霍景琛是個掌控欲極強的病態偏執狂,而趙思卿是他的心理醫生。霍景琛忍了六年,沒敢靠近她半步。 他以為他已經能很好的控製住自己那病態的佔有慾。可才一個照麵,霍景琛的臉就被自己打腫了。 「趙思卿是我的,她的眼睛是我的,身體是我的,從頭到腳、從裡到外、她的頭髮絲兒都是老子的!」人世間有百媚千紅,唯有你是我情之所鍾。 男主有病,女主有葯。雙處寵文,歡迎跳坑。
90.7萬字8.18 32039 -
完結476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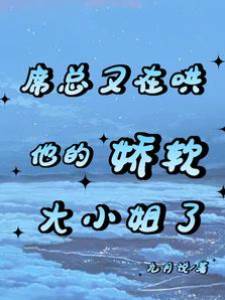
席總又在哄他的嬌軟大小姐了
矜貴腹黑高門總裁×嬌俏毒舌大小姐【甜寵 雙潔 互撩 雙向奔赴 都長嘴】溫舒出生時就是溫家的大小姐,眾人皆知她從小嬌寵著長大,且人如其名,溫柔舒雅,脾氣好的不得了。隻有席凜知道,她毒舌愛記仇,吵架時還愛動手,跟名字簡直是兩個極端。席凜從出生就被當成接班人培養,從小性子冷冽,生人勿近,長大後更是手段狠厲,眾人皆以為人如其名,凜然不已,難以接近。隻有溫舒知道,他私下裏哪裏生人勿近,哄人時溫柔又磨人,還經常不講武德偷偷用美人計。兩人傳出聯姻消息時,眾人覺得一硬一柔還挺般配。溫舒第一次聽時,隻想說大家都被迷了眼,哪裏般配。經年之後隻想感歎一句,確實般配。初遇時,兩人連正臉都沒看見,卻都已經記住對方。再見時兩人便已換了身份,成了未婚夫妻。“席太太,很高興遇見你。”“席先生,我也是。”是初遇時的悸動,也是一次又一次的心動。
89.3萬字8.18 19853 -
完結170 章

金魚入沼
偶有幾次,江稚茵聽朋友談起:“你沒發現嗎?你男朋友眼睛像蛇,看上去滿腹心機的,但是你一盯着他,他就乖得不得了,好奇怪。” 後來江稚茵注意了一下,發現的卻是別的奇怪的東西。 比如聞祈總是挑她最忙的時候,穿着鬆垮垮的衣服半倚在床頭,漆發半溼,瘦白指尖捻弄着摘下來的助聽器,嗓音含糊微啞: “與其做那個,不如做——” 他的嘴型由大到小,像嘆氣。 江稚茵打字的手一頓,猜到他將說沒說的那個字,及時制止:“現在不行。” “啊。”他耍渾,笑,“聽不到,你過來說。” “……” 在汗溼的時候,她故意盯着聞祈的眼睛,那人卻用手蓋住她的眼,用輕佻的語氣叫她不要多心。 後來江稚茵才知道,朋友說的都是對的。 這個人的心腹剖開後,都黑透了。 原來他從在孤兒院第一眼見到她,就算計到自己頭上來了。
27.4萬字8.18 1886 -
完結201 章

噓!你逃不出我的手掌心
“唔唔……”“疼……”“求求你放了我吧……”“沈佑寧你做夢,你這輩子死都是我孟宴辭的鬼。”寂靜的夜里一片漆黑,房間里光線昏暗。一個嬌美的女人被禁錮在床榻,她衣服有些凌亂,臉色慘白,手被皮帶綁著高舉過頭頂。而,男人則是一臉泰然自若地看著女人掙扎。看著她因為掙扎過度,被磨紅的雙手,臉上的情緒愈發冷然,鏡片下的鳳眼里只有滿滿的冰冷。“寧寧你又不乖了。”“是不是想讓我把你的腿給折斷……”“這樣就不會跑了… ...
32.7萬字8 4213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