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偏執太子是我前夫/歲時有昭(重生)》 第44章 第四十四章
顧長晉盯著屏風,手悄悄向腰間的短匕。
然看清來人后,他瞳孔微,心重重跳了下。
“顧大人醒了?”容舒將張媽媽送進來的藥放在幾案上,慢聲細語地解釋道:“常吉把你送來我這,想借著沈家的船將大人送到揚州去。”
見到容舒的那一剎那,顧長晉便已經想通了個中的前因后果。
“常吉與橫平改走陸路了?”
容舒頷首,“常吉說如此方能將那些人引走。大人放心,常吉與橫平武功高強,定能平安到揚州。你昏睡了十數日,還有約莫半月船便能到揚州了。大人可要我扶你坐起?”
指了指小幾上的藥碗,“大夫說你這傷,一日三劑藥,斷不能。”
也不知為何,顧長晉忽地便想起方才那個夢。
不喝藥,會難過。
遂強撐著坐起,這一番舉牽扯到上的傷,疼得他額間滲出了冷汗。
Advertisement
他二話不說便接過藥,一口飲盡。
這藥苦中帶了點辛辣,方才醒來時,他舌間便是這樣一子苦辣的味道。
他昏迷時,是喂的藥。
驀地又想起了夢中他對自己說的——
“以后你喂的藥,我都會喝。”
思緒一時繁復起來。
那個夢,或者說那些與相關的夢,不像是夢。
不是頭一回有這樣的覺了。
三年前的宮宴,他曾見過安世子一面。
那時的安世子只有八歲,可夢里的安世子已經十一歲了,一個只有一面之緣的孩子,怎可能會在夢里將他三年后的模樣都夢得那般清楚?
還有他給雕的冰貓兒,那覺太過悉,悉到給他一個石片和冰塊,他立時便能雕出一個一模一樣的貓兒來。
甚至于常吉說的那個“娘子”,也不知為何,一聽到這個名字,下意識便會將同潘學諒聯系在一起。
可他從不曾聽說過這個“娘子”,不管是潘學諒還是老尚書都不曾提過這人。
若這世間當真有一個“娘子”,那是不是,他做的夢也不僅僅夢?
“容姑娘曾在揚州住過九年,可曾聽說過一個名喚‘娘子’的人?”
容舒對這名字沒有印象,但還是認真思索了片刻,搖頭道:“不曾。”
看著顧長晉,“這人可是與大人要查的案子有關?”
顧長晉“唔”了聲:“若真有這樣一個人,與潘學諒的案子應當有關。”
容舒想了想便道:“我離開揚州好些年了,等回到揚州府,我便替大人問問,興許我在揚州的故人會聽說過這人。”
總歸去了揚州也要打聽沈家和舅舅的事,多打聽一個“娘子”也不費什麼功夫。若是能對潘學諒這案子有所幫助,此趟的揚州之行也算是不虛此行了。
“張媽媽讓人熬了粥,我現下就讓人送進來,顧大人用完膳便好生休息,盡早把傷養好罷。您到了揚州府,不得又要忙得昏天黑地的。”
顧長晉的確是覺得腸轆轆了。
可他舍不得走,還想再多聽說話,只容舒說完那話便頭也不回地出了客艙。
張媽媽很快便將熬好的粥送了進來。
顧長晉用完膳,吃下的湯藥漸漸起了效,闔目睡去的剎那,他昏昏沉沉地想:他還會做夢嗎?方才那夢……可會繼續?
給雕的那貓兒……可喜歡?
猜你喜歡
-
完結696 章

首輔大人的仵作小娘子
現代女法醫,胎穿到了一個臉上有胎記,被人嫌棄的棺材子魏真身上,繼承了老仵作的衣缽。一樁浮屍案把小仵作魏真跟首輔大人溫止陌捆綁在一起,魏真跟著溫止陌進京成了大理寺的仵作。“魏真,一起去喝點酒解解乏?”“魏真,一起去聽個曲逗逗樂?”“不行,不可以,不能去,魏真你這案子還要不要去查了?”溫止陌明明吃醋了,卻死活不承認喜歡魏真,總打著查案的由頭想公費戀愛……
126萬字8 9570 -
完結1881 章

鬼帝毒妃:逆天廢材大姐大
她被夫君與徒弟所害,一朝穿越重生,醜女變天仙! 她有逆天金手指,皇族宗門齊討好,各路天才成小弟! 戲渣父鬥姨娘虐庶妹,玩殘人渣未婚夫!他明明是妖豔絕代、玄術強悍的鬼帝,卻視她如命,“丫頭,不許再勾引其他男人!”
339.8萬字8 166366 -
連載1216 章

神醫廢材妃:皇叔寵如命!
蘇映雪被父親和庶妹害死了,一朝重生,她勢必要報仇雪恨。 靈藥空間,她信手拈來,醫學手術,她出神入化,一手絕世醫術,震驚九州大陸。 但報仇路上,總有那麼些人要來保護她。 冷血殺手:主人,紫尾誓死服從你的命令。
112.3萬字8.18 47704 -
完結81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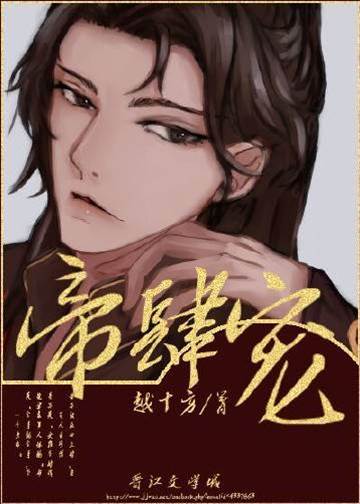
帝肆寵(臣妻)
從軍六年渺無音訊的夫君霍岐突然回來了,還從無名小卒一躍成為戰功赫赫的開國將軍。姜肆以為自己終于苦盡甘來,帶著孩子隨他入京。到了京城才知道,將軍府上已有一位將軍夫人。將軍夫人溫良淑婉,戰場上救了霍岐一命,還是當今尚書府的千金,與現在的霍岐正當…
28.8萬字8 27151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