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銷魂》 第 139 章 第 139 章
139
棺木是寧時亭盯著做的。
他盯著工匠,計算著選材,秦燈則監視著他。靈均王下葬,用的也該是王侯的陣仗,七天,木靈的匠人足以趕制完。
秦燈慢慢發現,寧時亭倒是真的在認真替顧聽霜做棺材,不像是有什麼打算的樣子——他甚至詳盡到棺材地步要鋪什麼材料。
按照王侯品級,棺木中陪葬本來應該有金玉三千,法寶無數。對于晴王府來說,辦一場風大葬,實在算不上什麼事。
人都是要死的了,這些陪葬的東西,無非是個寄托哀思的手段。
秦燈把開出來的陪葬清單拿去給寧時亭過目:“寧公子,您看這樣可以麼?”
清單里開出的東西極盡奢華,寧時亭掃了一眼,淡淡地說:“不用這些俗。殿下從自然中來,也要放歸群山去。”
秦燈這兩天被這小鮫人懟習慣了,他倒是耐著子,問:“那麼,隨葬一些什麼呢?”
“自然花草,天然珍寶靈藥。”寧時亭靜靜地說,“這孩子病痛沉疴,靈藥伴他下葬,希他來世有一副好,不求靈出塵,但求平安健康。”
秦燈頓了頓,在心里微不可查地嘆了一口氣。
寧時亭像是知道自己已經瞞不過去了,所以也不再瞞自己對顧聽霜的偏心——或者,那種他們都能看出來的愫。
連秦燈都忍不住想說一聲:何必呢。
晴王能忍寧時亭到現在,甚至為他殺了白塵,已經非常不同尋常了。寧時亭現在,只要回頭,就能將一切全數掌握在手中。
七日當天,棺木落,寧時亭也為顧聽霜選好了墓地——此棺將深埋在冬洲的峽谷前,正是步蒼穹舊日的山谷。
此谷此山,是他這一生中,僅存的回憶之地。
Advertisement
凌晨剛過,寧時亭便已經起。
帳外有人馬走過的聲音,聽這麼大的靜,應該是顧斐音回來了,不知道是剛好手頭的事結束,還是特意為了監視他殺顧聽霜這件事,特意趕回來。
冬洲冷,外邊天還很暗,寧時亭提著燈出去,秦燈已經讓人給他備好了馬。
那馬和普通的馬不一樣,雙眼暗紅,神極通人,寧時亭意識到,這是上古傳聞中的靈馬,擁有極高的靈和意識,而且隨時可以為主人赴湯蹈火。
秦燈說:“是靈馬,雖然事已至此,我相信公子您沒什麼別的心思了,但我需要提醒您,一旦您二位的行程與我們原先商議的有任何不同,靈馬都會將你們帶回原,且靈馬一死,我們這邊也將立刻接到消息。您是鮫人,世子殿下殘疾,未必能抗衡得了這靈馬。”
寧時亭垂下眼,淡淡地說:“知道了。你們實在多慮。”
秦燈干笑一聲:“王爺的子您是知道的,他萬事都求一個穩妥。”
人聲漸去。
寧時亭牽著靈馬,來到顧聽霜帳前,輕輕說:“殿下。”
過了一會兒,里邊傳來顧聽霜的聲音:“你真的來了?快回去,這里很危險。”
“不礙事。你聽。”寧時亭說,“今日全軍演武,他們跟著晴王的人馬,全部都到西邊去了。你聽我的話,不要消耗神,就當是為我好。”
“不要消耗神。”
顧聽霜正想放出靈識探查周圍的向,在這剎那間生生止住。
他知道寧時亭的意思,他在他不要用靈識。
寧時亭說話,他一直聽話,但如今的況,他只能信一半——他不知道寧時亭正于什麼樣的況中。
晴王多疑,名不續傳。
他們并不知道他有靈識,只聽說了上古白狼極聰明,喜群聚,于是將他幽閉在這個小院落中,任何人不得接近,四周都是銅墻鐵壁,他無法讀取任何人的靈識,也無法知道外界的全貌。
再加上嚴刑拷打,他的也撐不住長時間的靈識消耗了。
“聽話。”寧時亭輕輕說,“小狼在哪里?殿下等等我,我去接小狼來。”
“你上次來過之后,小狼被他們鎖在了后院。”
“好。”
寧時亭將靈馬拴在院門口,去后院,看見了在籠子里一團的小狼。
小狼的皮已經沾發灰,聽見有人來,甚至不愿抬起眼睛。
寧時亭笑了笑,輕輕說:“小狼來。”
銀白的小狼忽而睜開眼睛,黑暗中綻開一雙金的眼睛。
小狼嗚嗚著,似乎是想念,似乎是委屈,寧時亭對它出手,以為小狼會和從前一樣,隔著籠子來蹭他,但此時此刻,小狼反而豎起了尾,低沉地對他嘶吼起來。
它在他快點離開。
連它也知道此地危險,魚一個人過來,兇險萬分。
“沒關系,沒關系。”寧時亭安著它,暗青的眼眸展開笑意,“我來接你們了,不要怕。”
這一剎那,他如同回到數年以前,他從上輩子的死亡中回過神,決心照顧好那個庭院中寂寞寥落的孩子。小狼被關在后院的鐵籠里,瘦得皮包骨,一雙黃澄澄的眼睛無知無畏地看著他,湊上來嗅他的手指。而他后,坐在椅上的年第一次放松戒備,認真注視他。
顧聽霜出來了,他搖著椅,著他庭院門口的靈馬,問道:“你我二人,同乘一匹馬?不如……”
“小狼載我們”這句話他沒有說出口,寧時亭即對他比了一個噤聲的手勢,搖了搖頭。
顧聽霜皺起眉:“你說今日我們周圍沒有人了。”
寧時亭為什麼還這麼防備?甚至不允許他和小狼使用靈力。
“以殿下的聰明,過后就會知道了。”寧時亭說,“不要著急,您會知道的。”
“好。”顧聽霜也不再糾結。
這時候,再糾結下去,也沒有用。
他一向相信寧時亭的能力,每次他從來都不用擔心事件的結果,每次唯一要擔心的,是寧時亭自己。
寧時亭扶著顧聽霜上馬,隨后把小狼抱在懷里。小狼的四爪上都被上了捆靈的鐐銬,抹在手里一片冰涼,帶著濃重的腥味。
冬洲冷風拂過,他們頭頂還有稀稀落落的群星,和暗藍的天幕一起在他們頭頂。
空氣清爽,他們的呼吸散在空中,升騰一片白霧。
他們離晴王營地越來越遠,一路上沒有遇到任何阻礙,直到他們拐山道小路后,顧聽霜才略微放下心來。
他坐在寧時亭前,想回頭找寧時亭說話,寧時亭卻打斷了他:“什麼都不要說,什麼都不要問,殿下。”
他輕輕俯,往前在他背上,雙手環住他的腰。
這是一個溫順服的姿態,人的姿態。
顧聽霜啞聲笑:“要不是時機不對……我以為我夢想真了。”
寧時亭輕輕問:“什麼夢想?”
“山林野地,你我相伴,不再孤獨。”
他到底是想歸的,但這條路已經走到了這里,無法回頭。
顧聽霜怕他聽了難過,很快又說:“我們像是在私奔。今日你帶著我來了這麼一出,日后恐怕私通名號逃不了了。兒子竟然覬覦小娘……”
他以為寧時亭會笑,但寧時亭沒有,他只是仍然從背后抱著他,伏在他肩頭。
顧聽霜于是也安靜下來。
片刻后,他輕輕說:“沒事了,你看我現在不還是好好的?不要難過。”
“嗯。”寧時亭說。
小狼了,尾甩了甩。
靈馬一路狂奔,顧聽霜沒有問過方向,直到靈馬奔到一個開闊悉的地方時停下,他才察覺出眼前的景象有幾分悉。
“步蒼穹山下?”顧聽霜問寧時亭,“這個地方很危險,他們知道我們來過這里。”
“沒關系。”寧時亭縱馬停下,自己下了馬,隨后手接顧聽霜下馬——他在此還備下了一個椅。
顧聽霜放眼去,第一眼是,這里的雪已經被清掃干凈。
第二眼是,山谷門口,擺著一副琥珀的棺木——他看一眼就知道,是最上等的神木。
“那是什麼?”
“不重要。”寧時亭的語速加快,他手扶住顧聽霜的肩膀,認真地凝著他的眼睛,“殿下,我下面所說的一切,你都要記好。”
“我是您的臣子,也不止臣子。從前我為人臣,從不生私心,一心為君主,無怨無悔,而今我生出私心,我希殿下我,記得我,我當你的臣子,從未想過背叛,也絕不背叛。”
顧聽霜著他的眼睛。
寧時亭的眼神格外認真,著一種他看不的緒——那是他看不的,一個比他更多的靈魂。
這種眼神讓顧聽霜心里疼痛起來。
“我知道。”顧聽霜說,“我一直都知道。”
“我從前或許有拿自己的命,為殿下鋪路的想法,而今也不會了,因為我此生的愿,只剩下與殿下和睦相守,殿下心想事,一世平安。所以殿下也要信我。”
寧時亭說,“我知道殿下一直信我。”
顧聽霜沒有說話,他看向他的神中,漸漸帶上了一些疑。
這不是正常的囑咐。
這簡直像是……言。
顧聽霜正想問他的時候,寧時亭忽而一笑,湊上前來。打斷了他的話。
用。
他輕輕地俯過來,手扣住他的手腕,另一手攀上他的下頜,用力掐著他的下,死死地吻了上來。
顧聽霜這一剎那什麼都看不見了,他只看見寧時亭暗青的眼睛,妖異麗,是他沉淪多年的。
他毫無防備,劇烈的鮫毒在這一剎那侵他全,將他拉徹底的冰涼中。
寧時亭一直沒放開他,沒松開他,直到眼前人失去呼吸時,他才輕輕放手,像是站不住似的,跪倒在雪地里。
他后,山谷四周涌上一支威武雄壯的大軍。
顧斐音站在最前,出微笑:“好,他還是做到了。”
秦燈站在他邊,不忍地嘆了口氣:“那王爺,我們現在是接寧公子回去?”
“再等等。”顧斐音似笑非笑,“阿寧小心思多,這人死了,怎麼也要停尸七日吧。七日之后,他還死著,那麼才是真死了。”
猜你喜歡
-
完結1082 章
爆笑王妃:邪魅王爺澀澀愛
太師府剋夫三小姐,平生有三大愛好:食、色、性。 腹黑男八王爺,行走江湖有三大武器:高、富、帥。 當有一天,兩人狹路相逢,三小姐把八王爺全身摸了個遍,包括某些不該摸的地方,卻拒絕負責。
213.7萬字8.18 88415 -
完結861 章
龍鳳雙寶神醫娘親藥翻天
天才藥劑師一朝穿越成兩個孩子的娘,還是未婚先孕的那種,駱小冰無語凝噎。無油無鹽無糧可以忍,三姑六婆上門找茬可以忍,但,誰敢欺負她孩子,那就忍無可忍。看她左手醫術,右手經商,還有天老爺開大掛。什麼?無恥大伯娘想攀關系?打了再說。奶奶要贍養?行…
156.3萬字8.18 81645 -
完結1025 章

農家小福妻有法術
【無所不能滿級大佬vs寵妻無度鎮國將軍】 現代修真者楚清芷下凡經歷情劫,被迫俯身到了一個古代農家小姑娘身上。 小姑娘家八個孩子,加上她一共九個,她不得不挑大樑背負起養家重任。 施展禦獸術,收服了老虎為坐騎,黑熊為主力,狼為幫手,猴子做探路官兒,一起去打獵。 布冰凍陣法,做冰糕,賣遍大街小巷。 用藥道種草藥,問診治病,搓藥丸子,引來王公貴族紛紛爭搶,就連皇帝都要稱呼她為一句女先生。 為了成仙,她一邊養家,一邊開啟尋夫之路。 …… 全村最窮人家,自從接回了女兒,大家都以為日子會越來越艱難,沒想到一段時間後,又是建房又是買地…… 這哪是接回的女兒,這是財神爺啊! …… 連公主都拒娶的鎮國大將軍回家鄉休養了一段時間,忽然成親了,娶的是一位小小農女。 就在大家等著看笑話的時候,一個個權貴人物紛紛上門拜見。 太后拉著楚清芷的手,“清芷,我認你做妹妹怎麼樣?” 皇帝滿意地打量著楚清芷,“女先生可願意入朝為官?” 小太子拽住楚清芷的衣擺,“清芷姐姐,我想吃冰糕。”
177.3萬字8.46 176072 -
完結60 章

春閨嬌
一上一世,沈寧被死了十年的父親威逼利誘嫁給喜愛男色的東宮太子秦庭。 身為太子妃,她公正廉明,人型擋箭牌,獨守空房五年,膝下無子無女,最終熬壞了身子,被趕出東宮死在初雪。 重回始點,她褪去柔弱,步步為營,誓要為自己謀取安穩幸福,提起小包袱就往自己心心念念的秦王秦昱身邊衝去。 這一世,就算是“紅顏禍水”也無妨,一定要將他緊緊握在手裏。 二 某日。 沈將軍府,文院。 陽光明媚,鳥語花香,突傳來秦昱低沉清冷如玉般的聲音:“阿寧,你年紀小,身子弱,莫要總往我府上跑了。” 正抱著茶盞喝的開心的沈寧暴跳如雷——她跑啥了跑?倒是您一個王爺,沒事少來行嗎? 三 問:該怎麼尷尬又不失禮貌的嫁入秦·王·府? 天鴻清貴的秦昱勾了勾薄唇:王妃,床已鋪好,何時就寢? ps:男女主雙潔 ps:關於文中的錯別字,過完年我會抽時間整改一次,另外是第一次寫文,許多細節可能沒有完善好,但我日後會更加努力,謝謝觀看。 內容標簽: 情有獨鍾 宅鬥 重生 甜文 主角:沈寧
18.5萬字8 21891 -
完結1055 章

最小反派:團寵魔女三歲半
魔女變成三歲半小團子被迫找爹,可是沒想到便宜老爹一家都是寵女狂魔。從此,小團子開始放飛自我,徹底把改造系統逼成了享樂系統,鬧得整個江湖雞飛狗跳。小團子名言:哥哥在手,天下我有。什麼?有人找上門算帳?關門,放爹!
192.7萬字8 28556 -
完結438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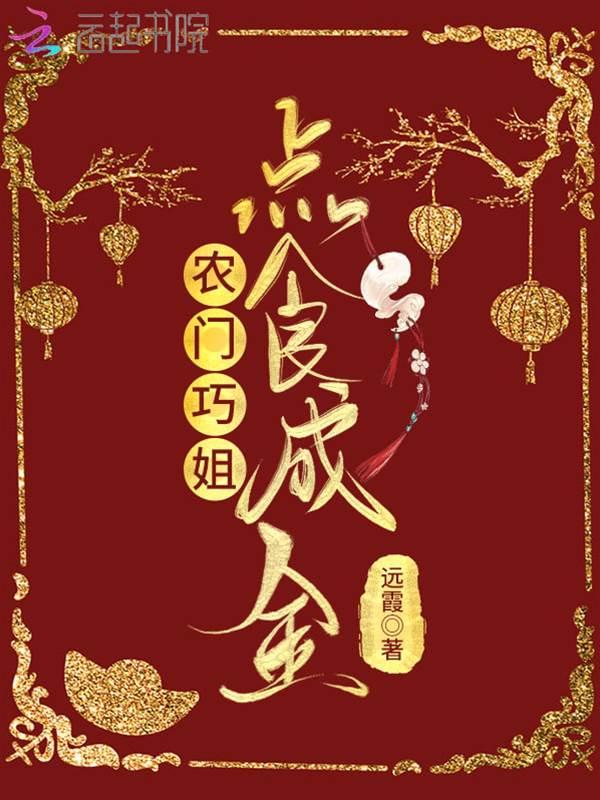
農門巧姐點食成金
高級點心師意外穿成13歲彪悍小農女-包蓉。後奶惡毒,親爺成了後爺。,爹娘軟弱可欺,弟弟幼小,包蓉擼起袖子,極品欺上門,一個字:虐!家裏窮,一個字:幹!爹娘軟弱慢慢調教,終有一天會變肉餡大包,弟弟聰明,那就好好讀書考科舉,以後給姐當靠山,至於經常帶著禮物上門的貴公子,嗯,這條粗大腿當然得抱緊了,她想要把事業做強做大,沒有靠山可不行,沒有銀子,她有做點心的手藝,無論是粗糧、雜糧、還是精糧,隻要經過她的手,那就都是寶。從此,包蓉銀子、鋪子全都有,外加一個自己送上門的親王夫君,氣得後奶一概極品直跳腳,卻拿她無可奈何。
77.6萬字8 37904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