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靈帝國》 第1345章 先祖歸來
“先祖靈魂完全消散大概是多長時間?”看到復活流程即將開始,我問出了這個關鍵問題。
“不確定,”塔維爾坦然答道,“因爲至今沒有檢測到靈魂反應,所以先祖之魂即使還在,也位於不可測量的狀態——屬下沒辦法對一個測不到的東西做任何推斷。不過假如按照最理想況,先祖之魂位於不可測的臨界點上的話,我們最多有二十四小時的時間。”
二十四小時……在這短短的一天之就要把所有可行的復活方法都嘗試一遍,如果不能功,那即便之後復活了先祖的軀也會毫無意義:這可真是一件迫的事。
珊多拉和塔維爾已經把復活計劃中已經遇上和可能遇上的問題都跟我講了一遍,我看們已經準備開始了,忍不住問道:“那什麼,我能幫上啥忙?”
我覺得珊多拉這麼急匆匆把自己過來肯定是有意義的,結果珊多拉想了想:“沒有——我就是想讓你過來看著。不管第一次試驗功與否,這都是歷史的一幕,你要做個見證人……”
我:“……”
“當然還有一點,如果你在旁邊,我會安心一點。”
我這才呼了口氣。
第一次試驗當然不可能把所有先祖骸都拿出來,用於復活的只是其中之一,這樣即便失敗,我們也有下次嘗試的機會。當然假如可能的話,誰都希第一次就功,畢竟在知道復活過程可能遇上的種種麻煩之後,我覺得假如第一次嘗試失敗,之後不管多次也沒多大機會找到別的可行方案了。
“設備組就緒。各小組順次檢查各自負責的項目段,”塔維爾飛快地在試驗檯旁的晶狀面板上作著,一邊對的外圍助手們作出指示,與此同時,的一大羣質量投影也開始按順序啓實驗室中那一大堆我看不出用的設備。“我們時間迫,我要求每一個步驟都無銜接。”
Advertisement
珊多拉拽著我後退了幾步:現在這裡已經是專家的領域了,外行不能干擾行工作。
在這個位置我也正好能看到整個實驗室的況,可以看到附近的大量記錄和分析設備已經上線,複雜的全息畫面閃爍著微,逐一出現在那些設備上空。分別顯示覆活所用裝置的狀態以及對先祖骸的監控況。停放著先祖骸的平臺上方也出現了懸浮在半空的影像,是先祖骸的掃描圖像,以及組織活躍度和對靈魂的監控:後者現在是一條直線,毫無起伏。
塔維爾冷靜到近乎機械的聲音是在張忙碌的實驗室中唯一的人聲:“質重組設備上線,災難事故置小組待命,軀重構準備就緒……實驗室主機。能源系統怎麼樣?”
“主機彙報……能源系統檢測完畢,十二組備用能源可用,所有冗餘系統無切換模擬功,本實驗室可保證在任何況下對核心設備提供能源或切換到備用系統。”
我覺珊多拉了自己的手,隨後聽到神連接中傳來的輕聲低語:“正常的復活流程都是先定位目標的靈魂,隨後在開始重構,必要的況下甚至是可以丟棄換新的東西。但這次,我們卻只能按照相反的流程來:先復活,然後這軀是否有靈魂就只能聽天由命了……”
我也珊多拉的手,讓安心:“這些事我不太懂,不過我覺得會功的。”
這時塔維爾已經完所有前置工作,最後檢查了試驗平臺的工作況,隨後下令啓房間上方那個環形燈管……好吧,學名是“信息演化重啓裝置”,這個裝置將通過將範圍的所有信息重啓來打破故鄉質上的凝滯狀態——我們現在還不知道這個凝滯狀態是怎麼來的,但塔維爾已經知道它是怎麼沒的。這就足夠了。
那個裝置啓的時候我沒任何覺,只是聽到實驗室中迴響起一陣十分低沉的嗡鳴聲,或許有一點覺?彷彿自己經歷的時間出現了某種斷面或者丟失了一秒鐘?反正只是一瞬間的事,隨後復活流程就開始了,實驗室的所有人彷彿從一個靜止畫面啓。瞬間飛快運轉起來。
一道垂直的幕從試驗平臺下面升起,從頭到腳緩慢地掃過先祖骸,隨後又反向掃過,平臺上方的監控圖像上顯示著損況。先祖骸的完整無缺,並沒有致命傷害,導致他死亡的是休眠艙故障所帶來的超低溫和巨量輻,因此這骸的大部分細胞都有著“傷”。那些細胞和地球上的任何一種生都不一樣,它們看上去有點像結晶,其部的傳質是一道縱貫結晶的亮線:正常細胞是這樣,而被超低溫和巨量輻殺死的細胞則有破裂或變質跡象。百分之八十的細胞同時死亡,導致這位先祖瞬間逝世,而卻保存的栩栩如生。
塔維爾開始著手修復那些破損的生組織,從微觀層面,一個分子一個分子地重新搭建起這,完全用這原本的質來完修復過程,以防止任何外來質對這個過程產生不穩定影響。同時,一道環形芒出現在平臺上方,我覺某種能量場將先祖骸籠罩了起來。
“那是防止靈魂逸散的東西,”珊多拉解釋著,“儘管檢測不到先祖的靈魂,這個裝置也仍然能生效,如果先祖之魂真的還在,這個裝置就能在目標軀達到可以‘運行’靈魂的時候,將靈魂重新編碼並制到目標上。你知道,對軀而言,靈魂是類似可執行代碼一樣的東西,件不能離件而存在,這道環的作用就是僞裝軀,讓靈魂無法離它的作用範圍。”
“但它不能阻止靈魂衰弱下去,是吧?”我好奇地問道。
珊多拉表有些憾地點點頭:“確實是這樣。你能用籬笆阻止羊羣跑出羊圈,但你不能阻止它們在籬笆裡慢慢老死……”
珊多拉已經會用這麼生的比喻了。
實驗室中瀰漫著張的氣氛,對先祖進行修復其實是技含量最低的環節,以希靈科技,在質層面上修復任何東西的難度都近乎可忽略不計。真正困難的地方,是讓這軀重新“活過來”。生命是一種奇妙的東西,地球上的科學家在“何爲生命”這個話題上已經爭爭吵吵許多年了,至今尚未定論。在單純的“科學”眼看來,所謂生命不過是一堆有機的轉化過程,不帶地拆分之後。生命最終歸於理和化學,並可以視作一堆不斷轉化的大分子——這個概念推而廣之,將生命的範疇推廣到無機和靈能生上,也不過是更復雜的化學或者理變化而已。
如果僅僅按照這個標準,那麼我們讓先祖的軀重新開始那一系列理化反應就可以算作後者“活過來”了,然而珊多拉想要的並不是這麼簡單的結果。
要讓先祖復活。我們要的不僅僅是讓那開始一系列有序的質變化,不僅僅是讓它在激素和生電流的刺激下張開眼睛那麼簡單——那與弗蘭肯斯坦別無二致。
在先祖的骸被修復之後,項目進了下一環節,塔維爾開始嘗試讓這恢復“活力”。
在各種監控畫面上,我能看到那已經運轉起來:他有了呼吸,開始流,一分鐘前剛修復完的臟正在有力地搏著。那不同於人類,結構多有些怪異的軀在我看來已經“生機”,我甚至在幾米外看到試驗檯上那“骸”的手指微微了一下。
然而他始終沒有睜開眼睛,對塔維爾施加的各種外界刺激毫無反應,甚至對神上的直接刺激都沒有反應,就好像一臺空白的機一樣,轟鳴作響,卻死氣沉沉。
“哪個步驟出了問題?”珊多拉上前兩步低聲問道,塔維爾皺著眉:“質層面上的修復已經完了,但先祖的拒絕‘活過來’。我檢測不到任何生命力。也沒有神波。理論上是這樣。”
我看著水晶棺槨中的先祖,這正在平穩地呼吸,它的每一個細胞都在工作,但它沒有生命力——這與植人都不一樣,植人仍然有神力量。而這……
非要說的話,它現在就是一團數十公斤重、正在發生著有序化學反應的硅硫化合(先祖的主要組部分),與任何一個化工罐裡的反應沒什麼本質差別。
就好像連os系統都沒有裝的計算機一樣,盤嗡鳴作響,理冒著熱氣,機箱中一片繁忙,屏幕上卻只有漆黑一片,連標都沒有。
珊多拉將手放在水晶棺槨上,的力量小心翼翼地瀰漫開來,我知道正在用奪靈者的強大力量呼喚先祖的靈魂,片刻之後,珊多拉表微微有了變化,似乎帶著一點喜悅,但更多的是困:“我能覺到類似靈魂的東西正在慢慢復甦,先祖之魂好像就在這上,隨著凝滯態一起被保存了下來,但這個靈魂無法‘啓’,一定是缺了什麼……”
“缺了生命力量,啓,耦合靈魂,並將生和化工罐裡的反應區別開來的關鍵要素,叮噹它生命力量——雖然除了叮噹,誰也沒實際到過那種力量,”我覺自己的腦袋前所未有地靈了一下,當然這跟自己平常天和叮噹玩鬧也有一定關係,“塔維爾你覺得呢?”
“不應該啊,”塔維爾困地搖搖頭,“正常況下,修復之後就會自然而然地產生生命力……”的話說到一半就被珊多拉打斷了:“現在不是正常況,組先祖骸的遠古質已經被凝滯數萬億年了,這些質可能還產生了我們不知道的變化。阿俊,叮噹在你兜裡麼?”
我手口袋,結果想起來今天出門的時候小東西正忙著看電視,就沒帶上。這時候應該在家跟淺淺玩或者被淺淺玩呢。
“把來,我真是糊塗了,這種項目一定能用上的力量的。”珊多拉拍著腦門說道,其實不怪之前沒想起來,主要是叮噹在家裡當米蟲的時間太久。已經沒多人記著小東西的本事……
“哦,這就……誒等等,塔維爾你先試試這個。”我剛要擡回去,突然想起上還帶著些“奇奇怪怪”的東西,於是趕在上掏起來,珊多拉疑地看著我。直到我從的口袋裡出一個扁扁的金屬盒來,金屬盒有煙盒那麼大,打開之後裡面是四分之三的綠末,末發著淡淡的熒,質彷彿介於虛實之間一般,並且微微變幻著迷人的澤。
“這是……”珊多拉小心翼翼地接過金屬盒。用手指沾起一點綠的熒末放在裡嚐了嚐——遇見稀罕玩意兒肯定是要嚐嚐的,“有一點清甜味,但不像我見過的任何質,這是什麼?”
“叮噹飛來飛去的時候翅膀上不是偶爾會灑下一些綠的小粒麼,”我指著那一小盒末,“這就是叮噹上掉下來的,我它叮噹渣……”
珊多拉霎時間整個人都傻那了。良久之後默默地看著那幾乎盛滿了盒子的綠,又擡頭看看我:“阿俊,你平常到底是要有多閒?”
我:“……一開始就是好奇,想看看叮噹上灑下來的那到底是什麼東西,最初的時候那些保持不了多久就會消失,但後來我發現用星金石做的容可以把它們保存長時間,就收集……”
猜你喜歡
-
連載1180 章
爆裂天神
迷霧籠罩地球,行星生物於深處涌現。孱弱的地球文明終於暴露於億萬種族目光之下。未來一百年,原本是一部血與火的人類抗爭史……然而故事線卻隨著那個男人回到原點的一刻,徹底改變。……“物競天擇,適者生存,你們來到這裡沒錯。”“但是,我作爲地球人類的一員,作爲這顆星球的執火者,我同樣有權拒絕。”“所以,今日我殺你,無關
247.4萬字8 16728 -
連載633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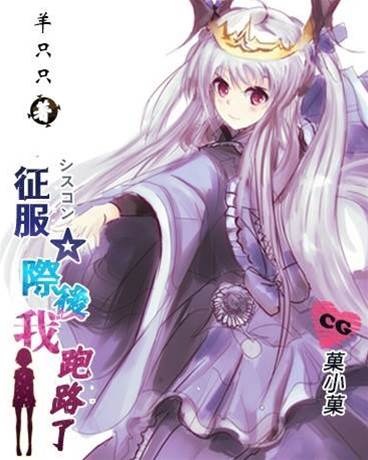
征服星際后我跑路了
明明只想做個大頭兵,卻偏要我到軍事學院混日子; 明明已經放棄復仇,仇家卻非要貼臉來找虐; 明明普通到不能再普通,最后竟然要拱我做統帥; 生活不如意,愛情不美麗,還要天天看人生贏家開后宮,這到底是什麼世道? 行吧,既然我過不好,那大家都別想好好過了!
123萬字8 6834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