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肆》 第57章 夏夜長┃高考時間
余和平背著包站在長明縣通往長海市的路邊, 等來往於兩地的第一班車。
夏天的時候,第一班車是早上六點,他五點半就站在了那裡。街道上一個人都沒有, 只有偶爾路過的汽車。九點開始的高考對他來說本是人生最珍貴的機遇, 他卻兒戲一樣當了賭注。
太將升未升的時候,梁東起來晨跑, 剛打開房門,就看見門口蜷著一個影。那人聽見開門聲就抬起頭來, 竟然是余和平。
梁東大吃一驚, 問:“你怎麼在這?”
余和平上裹著氣, 站起來說:“我來找你。”
“你找我做什麼,今天不是要高考麼?”
“我跟你說了,你不陪考, 我就不考了。”余和平看著梁東,說:“你果然不會去陪我,我都沒猜錯。”
“你腦子是不是被驢踢了?”梁東有些生氣,“高考你也敢這麼來麼?”
“那你今天有空麼?”
梁東看著余和平的眼睛, 薄抿著,半天才說:“你不要胡鬧!”
“你不是說高考是人生最重要的時刻麼,這麼重要的時刻, 我想你陪著我。他們都有人陪,就我沒有!”
“你家裡人呢?他們知道你這麼胡來麼?”梁東越說越生氣,“你回家去,趕!”
“我不走……”
梁東就手去拽他, 把他往樓梯口推,余和平抓住欄桿,就是不松手。樓上有戶人家估計是聽到了靜,打開一點門朝他們看。梁東松開了余和平,說:“你要胡鬧是吧?”
余和平雙眼都是眼淚,抓著欄桿就是不松開。
梁東索不再管他,直接朝樓下走。余和平就跟著他,他出來跑步的時候余和平還是跟著他,太從東方升起來,金的不冷不熱,風也開始暖了起來。梁東心裡有氣,就故意跑的很快,跑的也比平時要遠,余和平背著書包氣籲籲地跟在後頭。他顯然平時就缺乏鍛煉,個頭又沒梁東高,也沒有梁東長,很快就被甩到了後頭。
Advertisement
余和平大概已經魔怔了,他覺得他現在和梁東的狀態就像是他以後的人生,梁東跑的太快,他追不上,無論如何他都追不上。他又覺得自己很無恥,恥,竟這樣死皮賴臉地纏著一個好人。
他這麼做是對是錯,他也不想知道,反正他一直都是這樣可鄙的人生,或許從頭到尾都不會改變。
最後他實在追不上了,就癱坐在路邊,抱著他的書包氣。
但他竟不再悲傷,只是覺得很累,汗水順著他的下滴下來,太高高地升起來,這又是炎熱的一天。
如果一開始余和平就是這樣闖梁東的生活裡,梁東大概會把他當神經病,變態,別說不會理他,甚至還可能會報警。
但問題就在於他認識余和平已經很久了,余和平在他心裡已經留下了固有印象,那就是很溫順,甚至有些可憐和翳的一個孩子,他甚至都不覺得余和平真的有十九歲。已經有了這樣的印象,在面對如今余和平的行為舉止的時候,心就變得異常複雜。
他是老師,因此更知道教育對於余和平這樣的孩子的重要。可他也知道余和平這是纏上自己了,他不能管,管了可能就甩不掉了。
但是他和余歡已經結束,和余和平往來,別說余歡和陳平會不高興,他自己其實也不願意。他不想和那個家庭再有任何尷尬的往來,何況他約悉了余和平對他不可言說的。
他才想到余和平已經十九歲了,他是人是鬼,大概早已經定,不能更改。他注定是一個扭曲的人。
梁東就往回走,卻再也沒有看到余和平的影。
梁東有些心慌,將附近都找了一遍,還嘗試著了幾聲:“和平?余和平!”
但是他沒有找到余和平。他想余和平可能心灰意冷地走了,也可能幡然醒悟,趕回去參加高考了。但也只是猜想,不知道實際是怎麼樣。他想依照余和平弱的子,大概會是哭著走的。他還是有些不忍心的,但也只是不忍心,知道自己不能手。
太越升越高,天氣漸漸熱了起來。大清早的陶建國就打電話過來了,再次代了一下陶然要注意的事項,最後說:“昨天你媽還去廟裡給你許了願呢,你這一回是天時地利人和,放心考。”
陶然洗漱完畢,最後檢查了一遍考試要帶的東西。神清氣爽地準備出門。
走到客廳裡發現盛昱龍也穿好了服:“我送你。”
“不用,我跟同學說好了一起坐公車去,我們都算好時間了。”
“你同學是誰,一塊坐車去吧,反正我今天也沒什麼事。”
陶然笑著說:“你要陪考麼?”
盛昱龍說:“廢話。”
他當然要陪考,陶然人生中那麼重大的事,他不能不參與。
陶然就讓他去送,一起去的是他班裡兩個男生,跟他前後桌的,盛昱龍並不認識。那倆男生都是頭一次坐車,表現的十分拘謹。盛昱龍問陶然:“你那個同桌呢?”
“你說柳依依麼,跟爸媽一塊去。”
生大部分還是都有父母陪著的。
盛昱龍把他們送到韓福小學門口的時候是八點十分,但是他們來的已經算晚的了。那時候還沒有為了考生街道行這些規定,韓福小學外頭那條街好多車,但也都很有秩序地停在馬路兩邊。盛昱龍對陶然說:“你們十一點半下考場是吧,我到時候在門口等你,一起吃飯。”
陶然點點頭,和同學朝學校裡走,進大門之後回頭看,看到盛昱龍站在熙熙攘攘的人群裡,因為個頭高,很顯眼,一眼就能看見。
七月七號那一天特別熱,韓福小學屬於比較老的小學,教室裡連個風扇都沒有。最張的是發卷前的那幾分鍾,心都要從嗓子眼裡跳出來了,可是等做了幾分鍾的卷子,就一心撲在試卷上了。
第一科目考的是數學,陶然相對來說最薄弱的科目,但是他考的還算不錯,最後的一道大題,竟然和他們最後模擬考試的一道大題非常類似。這科目他做的有些,要卷的前兩分鍾才做完,花了最後兩分鍾檢查了一下選擇題。鈴聲響起的時候教室裡出現了輕微的,陶然坐直了,他手掌的汗水都沾了考卷。
監考老師收完卷子他們才被準許離開教室,外頭熙熙攘攘的都是考生,上一刻還寂靜無聲的校園這一刻人頭攢,但是走到大門口的時候才發現學校的大門還沒有開,站了好多保安。日頭毒,大家都站在門等待,已經有考生迫不及待地在大門口和自己的爸爸媽媽說自己考試的況,陶然站在人群裡,看到盛昱龍也在家長堆裡,正四尋他。
陶然擺了一下手,但是盛昱龍沒有看見。他們在人群裡等了大概十幾分鍾,學校的大門才開了,陶然穿過人群喊道:“六叔,我在這!”
盛昱龍看見他就笑了,說:“我還怕找不到你呢。”
他也沒問陶然考的怎麼樣,直接帶他去吃飯,附近的飯館都坐滿了人,好在他們有車,就走的遠一點。陶然告訴盛昱龍他覺得他考的還可以:“題都做完了。”
盛昱龍點點頭,說:“下午幾點考?”
“三點。”
中間休息的時間其實非常久,而且考場除了考試時間是不準任何人進的,回家一趟來回又太耽誤時間,也趕,所以大部分考生吃完飯都去東河公園裡乘涼休息。盛昱龍問他要不要去旅館睡個午覺,陶然雖然累,但也睡不著,於是倆人就去了東河公園散步,最後在河邊坐著,看波粼粼的東河水,吹著河面上的帶著點熱氣的風。
大概對於陶然這樣人生四平八穩的人來說,生活太過波瀾不驚,所以高考對他來說印象就格外深刻,以至於他很多年後想起高考,記憶最深刻的就是他和盛昱龍在午休時間在東河邊上呆的那兩天。七號中午,和八號中午。考試的心,考卷的容很快就忘記了,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那兩個午後看著東河水的心,雖然他也不記得都和盛昱龍說過什麼,他們兩個好像也沒有說什麼,大部分時間都靜靜地看著河面,看人釣魚,或者看河面上的遊船,綠洲上的白鷺。盛昱龍問他要不要睡一會,他睡不著,但也很累,就枕在盛昱龍的上小憩,朦朦朧朧的時候睜開眼,看到盛昱龍低著頭看他,眼神無限溫。
十八歲以前,陶然只有逢年過節才見盛昱龍一次,人生大事從來和他無關。十八歲以後,人生的每個重要時刻,都有盛昱龍在他邊。
因為記掛著陶然的高考,劉娟和陶建國這一天都心神不寧的,比他還張。晚上回來之後,就立馬給陶然打了個電話。陶然說考得還行,還告訴了陶建國夫婦盛昱龍有在陪考,他們不要擔心。
“我們等你考完了再去看你。”陶建國說。
劉娟很高興,晚上又拖著陶建國去步行街的廟裡拜。
這一回人要比昨天很多,陶建國也進去拜了一下。陶然最薄弱的一科就是數學,如今考的還算順利,功就有大半的希了,他也激。
回來卻見余家門口聚集了幾個鄰居,說是余家出事了,孩子找不著了。
“會不會是孩子沒考好,心裡害怕,所以躲起來了?”
“也可能是考完跟同學玩去了,天剛黑,這時間還早呢。”
鄰居七八舌地說。
陳平去找了還沒回來,余歡一個人在家門口等。有人問余歡:“你們家那條小白狗呢,這幾天怎麼都沒見。咱們附近多了好多狗的,你可看了,別小給弄走了。”
余歡說:“我們家的狗前幾天就賣了。”
那條狗有點上年紀了,老狗就有個病,咬,對陳平一直兇的,又,賣了省心。他們大院養狗就是養狗,還沒人把狗當孩子養的,何況那個年代,狗老了大家都會賣,能掙倆錢,還有的人家自己宰了吃的,因此大家聽了也都沒什麼反應。倒是劉娟覺得有些可惜,本來想要那條狗的。
“我看那狗以前天跟在和平屁後頭,有時候還跟著他上下學,會不會你把狗賣了,他心裡難,所以鬧脾氣跑出去了?”張婆婆說,語氣明顯帶了點敵意,因為一向看不慣余歡對待余和平的態度。
余歡聽了尷尬地笑了笑,說:“不會,賣狗之前問了他的,他要不同意哪會賣。”
是真的問過余和平,當時余和平蹲在地上正在喂小白吃的,聞言抬頭看了一眼,但並不吃驚,好像早知道要賣狗似的。也的確經常嚷著要把這條狗賣了。
“這狗白天咬了你爸一口,而且誰從家門口過它都追著,”余歡說,“賣了省心了。”
“誰家買啊?”余和平問。
余歡說:“它都這麼老了,誰還買來養,當然是賣給賣狗的。”
余和平頓了一下,低著頭沒有說話,繼續把手裡的饅頭一塊一塊掰碎了遞到小白的裡。余歡說:“你要不想賣不賣也行,就是以後看了,我想著拿條繩子拴起來,省的它咬人,你知道你爸打那個預防針花了多錢麼?要是咬了別人更不得了了。”
余和平要高考,余歡上沒好話,心裡其實還是關心的,余和平如果不答應,也不會要賣。不曾想余和平沉默了一會,說:“賣吧。”
後來家裡事多,這事就耽擱了下來,好在前幾天有空,就把那狗給賣了。那買狗的是老手了,把小白網走的時候小白都沒怎麼就被卡住了脖子。余和平一直在房間裡呆著,等到那買狗的走了之後才跑了出來,余歡正在數錢,看見他跑出來還嚇了一跳,朝他喊道:“賣都賣了,可要不回來了!”
猜你喜歡
-
完結949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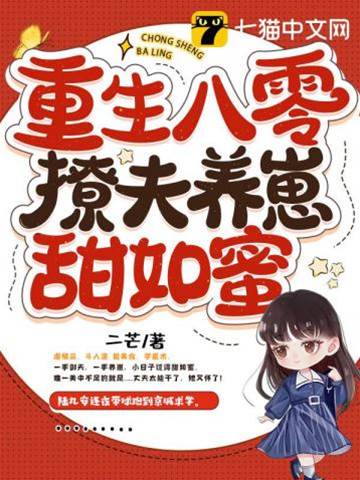
重生八零撩夫養崽甜如蜜
一場綁架,陸九安重回八零年的新婚夜,她果斷選擇收拾包袱跟著新婚丈夫謝蘊寧到林場。虐極品、斗人渣。做美食、學醫術。一手御夫,一手養崽,小日子過得甜如蜜。唯一美中不足的就是……丈夫太能干了,她又懷了!怕了怕了!陸九安連夜帶球跑到京城求學。卻發現自己的丈夫站在三尺講臺上,成了她的老師!救命!她真的不想再生崽了!!
174.3萬字8.18 74899 -
完結146 章

占欲
[現代情感] 《占欲》作者:三奈果子【完結】 文案 【欲撩➕年下➕白切黑弟弟➕極限拉扯➕追妻火葬場➕偏執瘋批➕雙潔1V1➕4歲年齡差】 【身軟腰細美艷大明星姐姐VS偏執瘋批白切黑弟弟】四年前寧喻因一雙漂亮的眼睛資助了一位少年,不料事後發現,對方竟是一個時刻覬覦她的瘋批偏執狂。寧喻以爲他是人畜無害的小弟弟,不想從資助他開始,她就落入了他蓄謀已久的圈套中。她踏進他精心佈下的局,成了他唯一的軟肋。寧喻抵開他的胸膛,極力找回自己的理智:“佔行之,我是你姐姐!”“姐姐?”佔行之溫柔的輕撫她的臉,笑意諷刺,“你覺得弟弟會對姐姐做這種事嗎?”佔行之見到寧喻那天,是在福利院裏。她一身紅長裙,飄零白雪落於肩,手上提着他不願穿的鞋,笑眼看他:“穿嗎?”那一刻,佔行之決定跟她走。遇到寧喻之前,佔行之的生活殘忍黑暗,沒有留戀。他能在面對瀕死父親時見死不救,也能機關算盡,只爲了徹底佔有寧喻,佔行之:“知道爲什麼不叫你姐嗎?”寧喻:“爲什麼?”“因爲叫你姐是想釣你,不叫姐是想上……”男人捏住她的下頜,強勢的吻隨之落下——“你。”佔喻,是隻對你寧喻的佔有慾。
20.3萬字8 8969 -
完結241 章

弄嬌
雪嫣與鎮北侯府的大公子定下親事, 沒有人知道,她曾與大公子的孿生弟弟有過一段不堪回首的過往。 雪嫣抱着僥倖待嫁, 然而婚儀前的一場大火,喜事變喪事。 謝策走進靈堂,寬慰痛不欲生的兄長,“人死不能復生。” 就在顧家爲顧雪嫣操辦喪事的時候,城郊的一座別院裏,已經“死去”的雪嫣淚落如珠,絕望哀求謝策:“求求你,求你放了我。” 謝策縛着雪嫣的雙手,輾轉吻去她的淚珠,“我是不是告訴過你,不能嫁給他。”他用極致溫柔的聲音,娓娓低語,“放了你?做夢。” 謝策覬覦兄長心上之人多時,圖謀不得,那便唯有硬奪。
38萬字8 7865 -
完結150 章

意亂情迷
路遙第一次見到霍遠周時,她十歲。 她只知道霍遠周是爸爸資助多年的山區的窮孩子。 那年霍遠周畢業工作,看在他帥的份上,她喊了他一聲叔叔。 路遙第二次見到霍遠周時,她二十五歲。 那年霍遠周已是坐擁兩地上市公司的商界傳奇人物。 只是那聲叔叔她怎麼都喊不出口。 路遙:“那什麼…我可以喊你霍大哥嗎?” 霍遠周似笑非笑:“我喊你爸大哥,你再喊我大哥?” 路遙:“……”
22.5萬字8.18 3968 -
完結130 章

霧港纏綿
【先婚後愛?港圈豪門?性張力拉滿?撩欲雙潔】【病嬌暴徒權貴社長??嬌媚尤物名媛總裁】港城世家千金宋輕韻,乖乖女的偽裝下嬌野難馴。聯姻三個月,將形婚老公連人帶名忘得一幹二淨,轉而在國外酒吧泡了個帶勁的男人。‘婚內出軌\’當天,宋輕韻就接到神秘老公梁宥津的電話。男人勾玩著指間的黑蛇,低沉蠱惑的嗓音說著動人的粵語關心她“bb,多喝點溫水,你的嗓子聽著好啞。”宋輕韻勾唇,笑他懂事回國後才知道,那是個不折不扣的斯文敗類。-港城梁老家主遭人投毒病重,億萬家產的爭奪暗潮洶湧宋輕韻被迫和極具野心的梁宥津捆綁,各取所需。他們身心默契,白天利益至上,晚上聽從感覺。說著半真不假的情話,抵死廝纏。“宋輕韻,我無條件服從你。”-突發的關係變故讓這段婚姻岌岌可危,宋輕韻丟下離婚協議消失不見。鋪天蓋地的報道震驚全國,梁宥津飛越9000公裏將人找到。蓄謀已久的七年暗戀難藏,他把人抵在門後發狠的親咬著懷中的女人。“宋輕韻,你好狠心。”沒等宋輕韻解釋,男人死死纏住她,埋在她頸窩說粵語的嗓音低啞。“bb,別丟下我。”-“商人逐利。”“梁宥津逐愛。”-24.1.1妘子衿
34.3萬字8 9645 -
完結309 章

叔叔,別撩我
唐墨何許人也?軍政界的扛把子,花癡界的全民老公,基佬界的小白菊,也是她顏若韻麵前的蘿莉控,更是她的三叔。情難自控,做了不該做的事,理應被甩?ok,她的錯,三叔您走好。再次相見,他相親,目睹她遭人劈腿。唯有歎逢年不吉,遇人不淑,一場誤會。“你男朋友就是酒吧那個?”舊情人戳中傷口,顏若歆氣定神閑,“不過是君子之交而已,三叔,這也當真?”“你什麽時候變成這樣?”“不知檢點?”某女微笑,“天生的!
55.6萬字8 5399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