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肆》 第50章 夏夜長┃六月九日,周二,炎熱
陶然不知道盛昱龍在發什麼瘋, 因為不知道,所以其實是有點怕的。
但是第二天下了晚自習回來,到家到盛昱龍, 盛昱龍跟沒事人一樣, 問:“不,吃夜宵?”
陶然淡淡地說:“不。”
他說罷就走, 盛昱龍卻抓住了他的手。他要出來,盛昱龍卻抓的更, 臉上也是笑著, 說:“別氣了, 昨天六叔喝了點酒,唬你玩呢。”
“你看我東西,還撕爛了, 也是唬我玩麼?”
盛昱龍說:“你這馬上就高考了,我也張,所以看到那書就有點反應過度,是怕你貪玩耽誤了學習。”
他語氣和緩, 求和的態度非常明顯。陶然反問:“我高考,你張什麼。”
“你說我張什麼,你疼你, 才替你張……”盛昱龍說,“你爸媽不也替你張麼?”
盛昱龍趁熱打鐵,低聲說:“別氣了。我都是出於好心,屬於好心辦壞事。”
陶然抿著不置可否, 說:“以後不經我允許,你不準進我房間,更不準私自翻我的東西,我也有私的。”
盛昱龍點點頭:“那書我也是無意間看到的,不是一開始就存心翻你東西。”
他見陶然態度和緩了一點,就拉著他出去吃宵夜,一邊走一邊問:“你那書,誰給你寫的?”
“不知道!”
盛昱龍關上門,笑著說:“剛說了不生氣,怎麼還生氣呢?”
“我沒生氣,我真不知道。你不是看了麼,上頭又沒寫名,又不是本人到我手裡的,我一去學校,就看到夾在我的課本裡。”
盛昱龍拔了鑰匙,說:“之心人皆有之啊。”
陶然扭頭看盛昱龍,盛昱龍說:“你還歡迎的。”
Advertisement
其實盛昱龍今天一整天都在後悔。
他是很後悔的人,但對於陶然,常常會後悔。一個人,最明顯的緒變化就是不確定,比如患得患失,比如總是覺得自己可以做的更好,或者不至於做的那麼差。“我當時其實可以怎麼怎麼樣”,“我要是不怎麼樣怎麼樣就好了”,這些緒總是充斥著他的心。
其實他在喝酒的那一會,還決定放下這不該有的念,做一個合格的六叔。
但是陶然總在他眼前晃悠,尤其是看到書這種對他來說有些刺激的東西,他總是會忘了自己的決定。就好像一頭的獅子,眼前擺著一塊鮮的,他能不吃已經屬於極度忍耐,難道還要眼看著別人吃?
做不到,不可能。那他還是個男人麼?!
陶然是真的很用功,吃宵夜的時候還在拿著一個小卡片時不時地看一眼。盛昱龍問:“什麼東西,吃飯也看。”
“英語單詞。”陶然給盛昱龍看了一眼,盛昱龍一個都不認識。
陶然高三,學歷已經比他高了。盛昱龍自認為自己是個人,心裡也敬仰有文化的人,心想陶然真好,以後就是大學生了,文化人。
他就無法忍住自己齷齪的覬覦的,眼睛在陶然上上下打量。
他一直都在想,上天造人真是不公平,陶然上真的找不到什麼明顯的短板,樣樣出類拔萃,以前不覺得,後來這種覺就越來越強烈,明顯。而不得會在男人心裡形白月似的偏執的,堆積,漸漸充滿心房。
天氣預報說明天是大晴天,陶然讓盛昱龍把被子抱到臺上去曬一曬。
“八九點的時候再曬,不然有水。”他五點多就要去上學了,那時候天都還沒完全亮,不然可以自己曬,
“知道了。”盛昱龍說。
第二天盛昱龍起來就把倆人的被子都曬上了。果然是很晴朗的一天,大清早的就覺得有些熱。
六月份,自從雨停了之後氣溫就一天比一天熱起來了,晚上睡覺都要開風扇。他把被子曬上之後,趁著有時間,就開車去了一趟長明縣。
他去看看陶建國夫婦的況。
這才多久沒去他們那,一進大院就發現了那片小區跟以前不一樣了,街道髒了不,牆上還掛著很多標語,他把車子停在大院門口,拎著東西下了車。雖然是午飯時間,大院裡卻沒什麼人,不像以前每次來都見有人在院子裡打牌逗鳥的。院子裡有些積水還沒有退,他踩著木板到了一樓的走廊下頭,發現有戶人家開著門窗,在做大掃除。
一個姿婀娜的人穿著碎花,手裡拿著一個拖把在拖地,有個男的手說:“給我給我,不是說了,你坐著,家裡的活都給我來乾。”
那人笑著推了他一把,臉上的笑容很是。察覺門口有人看,便扭頭看了一眼。
盛昱龍從門口走過,突然一隻灰白的小狗躥出來對著他,倒把他嚇了一跳。那狗不大,的卻很兇,呲牙咧的。那人從屋裡走出來,訓了那狗兩句,一腳踢過去,那小狗便嗚地一聲躥開了。
笑著對盛昱龍說:“不好意思,家裡的狗這兩天有點瘋。”
盛昱龍說了句“沒事”,上樓的時候聽見那人對屋裡頭的男人說:“這狗越來越煩人了,見人就咬,剛要不是我看見,恐怕又要咬著人了。你去打聽打聽哪有買狗的,賣了算了。”
盛昱龍上了樓,卻發現陶家沒人,只看到了陶然他三在二樓上曬蘿卜乾。
“昱龍來啦?”
“三嬸。我大哥他們家裡沒人?”
“陶然他媽去郊區挖野菜去了,建國在外頭乾活呢,中午不回來。”
“他在哪兒乾活呢?”
“樓板廠給人和混凝土呢,剛開始乾沒兩天。”
盛昱龍把東西都放在了那兒,又問了陶建國乾活的地址,立即就過去了。樓板廠他倒是見過,就是不知道都是幹什麼。那樓板廠離家遠的,在城郊了,日頭正烈,樓板廠裡也沒見乾活的人,他下了車,踩著碎石子往裡走,路面坑坑窪窪的,有些地方還很泥濘,他見一個中年婦戴著草帽子出來,便問了一下。
“這時候他們估計都在棚底下吃飯呢。”
盛昱龍按指的方向又往前走了一段,繞過一個土丘,果然就看見陶建國和一幫老爺們蹲在地上吃飯呢。
陶建國也看見了他,立即放下手裡的碗筷走了過來,頂著日頭問:“老六,你怎麼跑這來了?”
“我來看看你跟嫂子,結果家裡沒人,三嬸說你在這乾活呢,我就過來了。”盛昱龍說著就打量了一下那大棚底下的況,問:“你怎麼乾起這個來了?”
陶建國臉上略有些不自然,說:“我怎麼就不能乾這個了,昨天才來。”
他說著便拍了拍上的土,但那些都是混凝土,沾在服上,幹了就拍不掉了。盛昱龍說:“這活怎麼樣,累麼?”
“不累。”陶建國說罷又看向盛昱龍,見盛昱龍撇撇,便笑著說:“哪有不累的活,我也是閑的沒事,湊合乾乾,不然老在家裡呆著,你嫂子心裡也不踏實。你還沒說你來這有什麼事呢?”
“沒什麼事,就是看你工作找的怎麼樣了。”
盛昱龍說著就掏了煙出來,了一支給陶建國。陶建國接過來,盛昱龍又給他點上,他吸了一口問:“你吃了麼?”
“沒呢,這不是來你們家蹭飯來了。”
“那你等會,咱們出去吃。”
陶建國說罷就回去跟樓板廠的老板說了一聲,和盛昱龍一塊出來了。盛昱龍今天穿的是皮鞋,那一路都是泥路,沾了他一鞋,陶建國看見了,就說:“你不用擔心我,我做什麼不做什麼,心裡都有數。沒事也別往這邊跑,好好做你的生意。”
盛昱龍說:“咱們什麼分,你跟我說這個。”
陶建國笑了笑,被太曬紅的臉上胡子拉渣,盛昱龍見他後背都了,心下有些不是滋味。
“大哥,你要不想去我那乾,我也認識不人,可以讓他們幫著找找其他工作,說不定比你在軋鋼廠的活還輕松點,起碼會是個正經工作。”
“怎麼,瞧不起打樓板的?”陶建國笑著問。
“不是。”
“這活我肯定也不會常乾,這不是這樓板廠的老板是我朋友,天熱,願意來乾的人不多,我過來幫幫他的忙。”陶建國說著指了指前頭:“咱們在那吃吧,那家的菜還行。”
這頓飯陶建國執意要掏錢,盛昱龍也隨他去了。他想要是陶然,他想給錢直接就給了,陶建國卻不行,給了傷面子。吃完飯倆人又說了一會話,還是工作上的事,盛昱龍問:“我怎麼聽三嬸說,嫂子去城郊挖野菜了?”
陶建國一聽他那語氣就知道他想差了:“不是挖了自己吃,是我們大院一哥們在城郊包了十幾畝地,專門種野菜的,這幾天到了收割的時候,人手不夠,所以大院裡沒事的人都去幫忙了,管飯,一天還給二十塊錢。你嫂子就去了,這都是第二天了。”
“嫂子工作也不好找吧?”
“打算做點小買賣呢,張姐如今在賣菜,聽說還賺錢的。”陶建國說:“我們的事你就別問了,幫我照顧好陶然就行。不跟你說了,我得回去幹活了,下次咱們再好好喝。”
天熱,這頓飯就喝了兩瓶啤酒,陶建國不喝啤酒,盛昱龍也不喝。
盛昱龍回到市裡以後,便打電話找朋友打聽了一下,但合適的工作真不好找,如今下崗那麼泛濫,長海市這種老工業城市下崗的更多,待遇差強人意的都爭著有人乾,那更不用說差不多的職位了。尤其是給陶建國找,好的恐怕陶建國乾不了,差的他也不好意思介紹,沒找到合適的。
晚上的時候陶然回來了,他看到陶然,想起白天裡看到的陶建國的工作環境,心裡發沉,連帶著覺得陶然也很可憐,陶然越是不知,他心裡越是覺得憐之心泛濫,看著陶然那白淨俊秀的模樣,想讓他過食無憂的好日子。
陶然問:“你白天去哪了?”
盛昱龍一愣,心想這小子火眼金睛啊,突然問這個,好像知道他白天去了長明縣一樣。
“去了你家一趟,你怎麼知道了?”
“看你皮鞋上都是泥。”
盛昱龍的鞋一般都很乾淨,今天穿的皮鞋都是泥,他進門就看見了。不過還真沒想到盛昱龍就去他家了,心裡微微一,問:“我家裡怎麼樣?”
盛昱龍說:“老樣,我就是沒事去看看。”
陶然竟然沒有再多問,隻拿起他的皮鞋,去洗手間幫他刷鞋去了。
盛昱龍走到門口,依著門框說:“今天回來這麼早?”
“嗯,今天有點累,想早點睡覺。”
皮鞋好刷,刷乾淨之後他就拿到臺上去了,結果剛拉開臺的門就吃驚地喊道:“六叔,被子你怎麼沒收啊?”
盛昱龍這才想起來他今天曬了被子,把這事給忘了。
被子已經有些了,陶然把被子抱回來,一邊走一邊說:“你曬個被子,你也能忘了收。”
又好氣又好笑。
“天這麼熱了,被子早該收起來了。”其實現在他睡覺都沒蓋被子了,最多蓋個毯就夠了。就是陶然依舊蓋被子,蓋著被子吹風扇,說那麼睡舒服。
今天的天氣似乎特別熱,風扇也不管用。陶然洗了澡去睡覺,沒多大會就又是一汗,怎麼都睡不著,眼看著都快十二點了,心裡就有些急,想著去浴室再衝一下,結果出門卻發現洗手間裡亮著燈。他走到門口一看,就看見盛昱龍洗了澡,正溜溜地站在鏡子前頭髮,全上下一覽無余,端的是高大健壯。
還是老樣子,洗澡都不關門。
盛昱龍也看見了他,竟然了一下,好像有些嚇到了,然後了浴巾過來,系在腰間。
這下倒讓陶然吃驚不小,以前盛昱龍都是當著他的面直接赤條條啊,他都習慣盛昱龍的大喇喇了,如今看見他竟然還知道拿浴巾遮住,實在他意外。
“你也洗澡呢、”他說,“真熱。”
“嗯。出汗了,衝衝。”盛昱龍說著便走了出來,上還掛著水珠子,順著他理分明的膛往下流,上全是的水汽。
盛昱龍說:“你衝吧。”
陶然了眼睛就進去了,順便關上了門。盛昱龍回頭看了一眼,輕輕咳了一聲,撓了撓頭。
陶然隻穿了個三角,條看著更順更了。尤其是剛才看到的那一瞬,因為陶然站在影,他還以為陶然溜溜的沒穿服,嚇得一抖,刺激得近乎他害怕。
猜你喜歡
-
完結718 章

嬌妃火辣辣
某夜,某人爬牆被逮個正著。 「王妃欲往何處去?」 「那個……南楚世子東陵太子和西炎王又不老實了,我削他們去」 「那個不急,下來,本王急了……」
136.3萬字8 27080 -
完結156 章

穿成侯門寡婦後,誤惹奸臣逃不掉
【雙c 傳統古言】沈窈穿越了,穿成了丈夫剛去世的侯門新鮮小寡婦。丈夫是侯府二郎,身體不好,卻又花心好女色,家裏養著妾侍通房,外麵養著外室花娘。縱欲過度,死在了女人身上……了解了前因後果的沈窈,隻想著等孝期過了後,她求得一紙放妻書,離開侯府。男人都死了,她可不會愚蠢的帶著豐厚的嫁妝,替別人養娃。 ***謝臨淵剛回侯府,便瞧見那身穿孝服擋不住渾身俏麗的小娘子,麵上不熟。但他知道,那是他二弟剛娶過門的妻子。“弟妹,節哀……。”瞧見謝臨淵來,沈窈拿著帕子哭的越發傷心。午夜時分,倩影恍惚,讓人差點失了分寸。 ***一年後,沈窈想著終於可以解放了,她正要去找大伯哥替弟給她放妻書。沒想到的是,她那常年臥病在床的大嫂又去世了。沈窈帶著二房的人去吊唁,看著那身穿孝服的大伯哥。“大伯哥,節哀……。”謝臨淵抬眸看向沈窈,啞聲說道:“放你離開之事,往後延延……。”“不著急。”沈窈沒想到,她一句不著急, 非但沒走成,還被安排管起侯府內務來。後來更是直接將自己也管到了謝老大的房內。大伯哥跟弟妹,這關係不太正經。她想跑。謝臨淵看著沈窈,嗓音沙啞:這輩子別想逃,你肚子裏出的孩子,隻能是我的。
31.5萬字8.18 9189 -
完結121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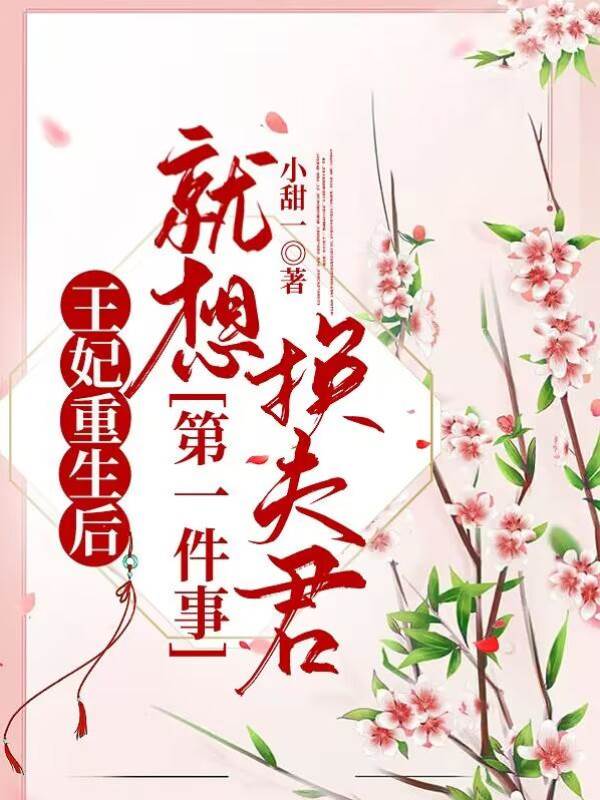
王妃重生後,第一件事就想換夫君
上輩子盛年死於肺癆的昭王妃蘇妧重生了。回想自己前一世,溫婉賢惠,端方持家,一心想把那個冰塊一樣的夫君的心捂熱,結果可想而知;非但沒把冰塊捂化了,反而累的自己年紀輕輕一身毛病,最後還英年早逝;重生一世,蘇妧仔細謹慎的考慮了很久,覺得前世的自己有點矯情,明明有錢有權有娃,還要什麼男人?她剛動了那麼一丟丟想換人的心思,沒成想前世的那個冤家居然也重生了!PS:①日常種田文,②寫男女主,也有男女主的兄弟姐妹③微宅鬥,不虐,就是讓兩個前世沒長嘴的家夥這輩子好好談戀愛好好在一起!(雷者慎入)④雙方都沒有原則性問題!
34.3萬字8 20883 -
完結279 章

嫁給兄長的竹馬
寧姒10歲時遇見了16歲的姜煜,少年眉目如畫,溫柔清雅,生有一雙愛笑桃花眼,和她逗比親哥形成了慘烈的對比。 那少年郎待她溫柔親暱,閒來逗耍,一口一個“妹妹”。 寧姒既享受又酸澀,同時小心藏好不合時宜的心思。 待她出落成少女之姿,打算永遠敬他如兄長,姜煜卻勾起脣角笑得風流,“姒兒妹妹,怎麼不叫阿煜哥哥了?” 【小劇場】 寧姒十歲時—— 寧澈對姜煜說,“別教她喝酒,喝醉了你照顧,別賴我。”嫌棄得恨不得寧姒是姜煜的妹妹。 姜煜微醺,“我照顧。” 寧姒十六歲—— 寧澈親眼看到寧姒勾着姜煜的脖子,兩人姿態親密。 姜煜低頭在寧姒臉頰上親了一口,然後對寧澈笑,“阿澈,要揍便揍,別打臉。”
42.9萬字8.18 11084 -
完結309 章

釣餌
周宴京電話打來時,陳桑剛把他白月光的弟弟釣到手。周宴京:“陳桑,離了我,你對別的男人有感覺?”弟弟雙手掐著陳桑的腰,視線往下滑:“好像……感覺還不少。”……“在我貧瘠的土地上,你是最後的玫瑰。”【飲食男女 男二上位 人間清醒釣係美人VS偏執腹黑瘋批大佬】
53.4萬字8.18 6024 -
完結123 章

傻妃配殘王
最近京城可出了個人人皆知的大笑話,將軍府中的傻公子被太子殿下退貨轉手給了殘王,傻子配殘王,天生一對。 世人卻不知這被人人嘲笑的某人和某王正各自私地下打著小算盤呢。 “報,王爺,外面有人欺負王妃殿下。” 某人聞言,眉頭一挑:“將本王四十米的刀拿來,分分鐘砍死他,活得不耐煩了!!” “報,王爺………………,”某士兵支支吾吾的看著心情不錯的某人。 “怎麼了,誰又欺負王妃殿下了?” “王爺,這次并不是,王妃殿下他去了春香閣……………………” 砰的一聲,某人身下的輪椅碎成了幾塊:“給本王帶兵將春香閣拆了!” 歡脫1V1有副cp
15.5萬字8 55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