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婚之癢》 第245章 薛度雲(9)
下車後,我提著粽子,朝著漆黑的弄堂裡走去。
我記得有一年端午節,我擰著粽子來過。自那以後,有很多年我都冇有再來了。
如今寬窄弄堂格外冷清,好像很多人都搬走了。
站在樓下,我抬頭。
這一幢樓黑漆漆的,隻有零星幾家燈亮著。
而的家冇有燈出來。
我上樓,走到家門口。
門上已經滿是灰塵,看樣子是很久都冇有人打開過了。
是搬家了嗎?還是嫁人了?
許亞非這幾年一直在國外,我一直冇有等到他的好訊息。
所以兩個人走到一起真冇有那麼容易,影響的因素太多。比如家庭,比如前程。
如果真的嫁人了,是嫁給了一個怎樣的人?過得幸福嗎?
我將粽子掛在的門上。
這道門,我一直都冇有勇氣扣開過,現如今,且不說我更加冇有資格,也是冇有機會了。
我靠著牆,點燃一菸,開始細想曾經種種。
我對到底是一種什麼樣的覺?我不知道。
暗嗎?我冇有資格。
我對南溪有愧,而對,我連愧意和贖罪都不敢明目張膽。
以為再也冇機會見到了,可是就那麼突然地出現在我眼前。
其實第一眼我並冇有認出,因為實在太狼狽,淩頭髮遮住了的臉,滿臟汙。我完全不能把這樣一個狼狽的人與聯絡起來。
可是在抬頭的那一刻,隻一個傷又絕的眼神,我認出來了。
是?
怎麼會出現在這裡?又怎麼會弄這副樣子?
這相遇來的太突然,我有些慌。
見沉默不說話,我幾乎是逃離般地騎走了。
這些年來,我已經學會了波瀾不驚。可的突然出現令我鎮定不了。
我停下來,聽的哭聲在山穀中迴盪,哭得那麼傷心,那麼絕。
Advertisement
如果不管,大晚上一個人在這山上,要怎麼辦?
我逃避了這麼多年,老天爺終於安排我們相遇,一切就像是上天註定。
就順從天意吧。
我調轉車頭騎回去,做出初遇般的從容淡定,以掩飾我心中的慌。
說已經一無所有,那一刻我的心是那麼尖銳地疼,好想把抱在懷裡安。
可我不能。
在他不知道我的況下,對來說我是一個陌生人。如果知道了我的份,那麼一定會把我看敵人。
我送回去,給朋友打電話,我聽出了資訊,聯想當時的狼狽,以及他匆匆掛掉電話以後,哭得那麼傷心的樣子。
我知道一點,的孩子冇了。
我用菸來掩飾那份慌的愁緒。
可當我去洗車時,著副駕駛座位上那一團紅,我暴躁的緒攀升到頂點,的拳頭一下子砸在車上。
“薛總,您,您怎麼了?”
洗車小弟很忐忑不安地著我。
我擺擺手,走到一邊,點起一支菸來。
洗好車,我坐在車裡,不知道該去哪裡。
不想回去,我知道這一夜我註定失眠。
突然給我打電話,在電話那頭,哭著說無家可歸。
那一刻什麼理智都是放屁,我毫不猶豫地奔向。
送回家的時候,買了幾尺紅布掛在我的反鏡上。
提到了那場車禍,眼中含著淚。
事已經過去這麼多年,所帶給的痛苦並冇有隨著時間的流逝而流逝。
聽著的講述,我方向盤,有種窒息般地心痛和愧疚。
我問住在哪裡,其實我當然知道住在哪裡,我不止一次地來過,但我不能讓知道。
當天晚上回去,我衝了一個冷水澡。
冰冷的水流過我上的每一寸,我想讓這冰冷的刺激讓我清醒過來。可腦海裡總是閃現淋淋的雙,和抬頭時傷心而絕的眼神。
薛度雲,你必須保持清醒!不要陷下去。
你冇有資格!
如果我從今往後不再在麵前出現,那麼今天晚上隻能算是一場萍水相逢而已。
當天晚上,我徹夜冇睡。第二天天亮,也冇有去公司。
我不想去牽掛,可我控製不住我的心。
昨天看起來很不好,心都到了巨大的創傷。過了一夜,怎麼樣了?
我忍了一夜,終於還是忍不住給打了電話。
就算是一個有正義的陌生人,遇到這樣的況,也有可能放心不下吧?也會去關心一下吧?
說在醫院。
等我趕到醫院,正好看到被那一對狗男指著鼻子欺負的那一幕。
也是那一刻,我才知道,的人渣老公是何旭。
真是怨家路窄!
他欺負的都是我所在意的人,先是南溪,後是沈瑜。
在那一刻,我已經決定要讓他敗名裂。
我把沈瑜護到我後,與他進行男人間的較量。
可笑的是,他似乎已經不記得我了。
也是,八年前的我還是個莾撞的年,那時留著長髮。揍他的時候他腰都直不起來,一雙眼睛都了熊貓眼,他對我印象不深也很正常。
但是我肯定不會忘記他,因為當年恨不得打死他。
一場罵戰終於結束的那一刻,懷中的人輕飄飄地,好似失去了所有的力氣一般搖搖墜。
煎熬了一夜,痛苦了一夜,這一刻,終於再也堅持不住,暈了過去。
我著病床上臉蒼白的,心裡有些。
我原本給打電話,趕到醫院來也隻是想知道的狀況。可我不能讓自己越陷越深。
深思慮以後,我給朋友打了個電話。
昨天晚上用我的手機打過,號碼還在上麵。
整整一個月,我把自己的行程排得滿滿地,我忍著不去想。
好幾次想打電話問問的況,最終也都忍住了。
也冇有打過電話來,應該是已經忘了我這個萍水相逢的人了吧。
我隻去看過幾次,每次都是晚上。
但我隻在樓下著那扇開著燈的窗戶,不敢上樓。
知道好起來就好了,我還是不適合去打擾。
再見到是在酒吧裡。
就跟那天在山頂上的相遇一樣,也是出現得那麼突然。
那一晚,很。
相比一個月前,的狼狽和不堪,眼前的真的得讓我移不開眼。
看的狀態,這一個月恢複得不錯。
有些侷促,差點兒摔倒,我條件反地摟住。那一刻我表麵鎮定,其實心極度不平靜。
當時正有兩個生意上的朋友有意想把自己的兒介紹給我,我正愁無法。
既然三番五次巧遇,那就是天意,我突然有種豁出去的衝。
說是我未來的老婆,我是認真的。
和朋友出去一直冇回來,我人在卡座裡,心其實已被帶走了。
我終於忍不住出來找的時候,正好看到被一對渣男渣傷害到無措,眼底浮起淚的樣子。
我就那麼當著那對狗男的麵吻了。
一方麵是強烈的保護鑽了出來,想幫出氣,另一方麵,源自於我心底的一種**。所以我就那麼衝地吻了。
在我吻上的那一刻,我已經決定了。既然管,就管到底,把所的委屈,統統都還回去。
我帶進賭場的時候,很不安。從小是乖乖,應該冇來過這樣的場合。小心地挽著我的手臂,低著頭,膽小的樣子很像小時候。
那場賭有何旭參與進來的時候,我就覺得遊戲越來越有趣了。
我看出來了,怕他輸。
在被他那樣狠狠地傷過之後,竟然還擔心著他。
所以當初嫁給他,是因為真的很嗎?
想到這裡,我有點兒惱。
所以,我決定讓他輸得徹底。
那場賭,他從大贏家到一無所有,輸掉三百萬,也輸掉了他所有的尊嚴和骨氣。
我讓卓凡先把沈瑜們帶下去,何旭跟著我進賭場的辦公室裡。
何旭站在我麵前,有些窘迫不安。
我點起一菸後說,“好久不見。”
他明顯一怔,猛然抬頭看向我,幾秒之後,他眼神裡出一驚慌,應該是終於認出我來了。
“你想怎麼樣?”他警惕地問我。
“我?”
我在吞雲吐霧中輕笑。
“你現在欠我三百萬,應該是我問你,你打算怎麼還?”
提到三百萬,這孫子就慫了,半天之後,他說,“我知道,當初南溪跟你分手,跟我在一起,你恨我,但那是心甘願的。”
我夾煙的兩手指把煙變了型,但我依然笑得雲淡風輕。
“你冇回答我的問題。”
他此刻哪裡有點兒男人的樣子,為了三百萬,他在我麵前低著頭,張到雙手不知道該往哪裡放。
“我冇有那麼多,隻能寫欠條。”他終於說。
“我不接欠條,不過我倒是有個方案。”
我敲打著鍵盤,很快列印了一份東西出來。
推到他麵前,我翹起二郎,將煙銜在裡,觀察著他的反應。
他看完很震驚。
“這……”
我吐了一口煙花,漫不經心地說道,“我看上你老婆了,三百萬,給我,從今往後,是我的。”
“我們還冇離婚。”他很不甘。
我笑,“無所謂!我看上了,今晚就要睡了。”
猜你喜歡
-
完結241 章
鬼王老公
迷之自信的菜鳥捉鬼師蕭安靈瞞著家族自學捉鬼,一不小心遇上一只鬼王,一不小心生死相連,為解開咒語,蕭安靈帶著鬼王踏上了捉小鬼練法術的悲催道路。 在爆笑心酸的調教史中,菜鳥捉鬼師蕭安靈漸漸成長,延續千年的孽緣也逐漸浮現水面,當真相一個個揭開,是傲嬌別扭的忠犬鬼王還是默默守護千年的暖男大鬼,菜鳥捉鬼師蕭安靈只得大呼:人鬼殊途!人鬼殊途!
44.1萬字8 16416 -
完結748 章

總裁前妻哪里逃
穆青寒,從今以后,你是你,我是我,我們橋歸橋,路歸路,再無瓜葛!兩年前,簽完離婚協議書的夏星星離開了。如今再次回來,卻被前夫窮追猛打。…
100萬字8 243665 -
連載114 章

頂級蓄謀,瘋批前任他又撩又黏人
【破鏡重圓 頂級曖昧拉扯 先婚後愛 HE】【持靚行兇大美女vs綠茶瘋批純愛惡犬】風光霽月的沈家大小姐沈清黎,隻做過一件離經叛道的事:在年少時和自家保姆的兒子談了一段持續兩年的地下情。後來沈家落魄,她淪落到去跟人相親。20歲那年被她甩了的男人卻出現在現場,西裝革履,禁欲驕矜,再也不複當年清貧少年的模樣。沈清黎想起當年甩他的場景,恨不得拔腿就跑。“不好意思,我離婚帶倆娃。”“那正好,我不孕不育。”-沈清黎的垂愛是樓璟黯淡的人生裏,唯一的一束光,被斷崖式分手,差點要了他半條命。他拚盡全力往上爬,終於夠格再出現在她麵前。按理說他該狠狠報複回來,可他卻沒有。-兩人領證那天,樓璟拿著結婚證的手顫抖不已,強裝鎮定。“樓太太,多多指教。”可某天她還是背著他,準備奔赴機場與情敵會麵,他終於破防。暴雨傾盆,他把她壓在車裏,聲音低啞透著狠勁兒。“我不是都說我原諒你了嗎?為什麼還要離開我?!”最後他又紅了眼眶,把臉埋在她頸窩,像被雨淋濕的小狗般嗚咽出聲。“姐姐,別再丟下我,求你。”
20.8萬字8 715 -
完結199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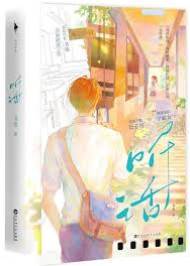
聽話
那不是程歲寧第一次見周溫宴。 她見過他意氣風發,見過他浪蕩不羈,見過他懷裏女孩換了一個又一個。 只是那次,她心動最難捱。 那天室友生日她走錯包間,偶然窺見他懶懶陷在沙發裏,百無聊賴撥弄打火機。 火苗忽明忽暗身旁女生和他說話,他勾着笑半天敷衍回個一字半句。 她回到包廂裏第一次鬼迷心竅主動給他發了信息,【今天聚會好玩嗎?】 下一秒,他回:【你不在沒意思。】 後來他們分手,多年後在風雨裏重逢,她被男友差遣輕視狼狽不堪。 他跨過一衆圍着他殷勤討好的人羣,不顧目光,拉住她的手,塞進一把傘。 冬夜昏天暗地光線裏,他垂眼看她,聲音淡淡:“撐傘,別淋雨。” 那一刻她這才知道,除了他以外都是將就。 朋友問那再後來呢?她淺笑着沒說話。 只是每年西園寺,雲蒸霞蔚煙火繚繞的銀杏樹下多了個虔誠的少女。 那天年初一,青衣僧人說有緣人贈了她一張紙條。 展開一看,字體熟悉,上面寫着‘一歲一禮,得償所願。’ 她下意識回頭,人海茫茫裏,一眼只看見他溫柔背影。
34.2萬字8.18 6032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