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嫡女策:殿下,藥不能停》 第062章 他和美人在一起
焦元祿唯恐他們選了不該選的,忙拿著拂塵過來,看著那綃紗,臉驟變。
“李公公,這……這匹可不妥呀!萬萬使不得!”
妙音一門心思都在研看這蛟綃紗,沒有察覺李正中給焦元祿遞眼,疑地問道,“李公公,這不就是尋常的綃紗嗎。”
“此言差矣,郡主請隨奴才過來看!”
李正中忙帶著,抱著綃紗走到滴水的更前,用手了一點水花在綃紗上,水珠似落在荷葉上,一滾,就落在地上,綃紗上竟是干干凈凈,半點水痕都沒有。
“哇!”妙音歡喜地忙著綃紗不釋手,“我爹給我買的好幾件袍服,也都是這般材質,據說一尺千金,我爹自己卻從來舍不得穿。這百福綃紗倒是能給我爹裁,金紗罩在黑袍外,高端大氣上檔次!”
“郡主慧眼!”李正中當即就拿了一塊黑布,將蛟綃紗仔細包纏起來,“郡主收下吧,這庫房里,這種東西多著呢,也不知是哪年進貢的。”
妙音沒客氣,當即就抱著出了尚宮局。
焦元祿氣急地拉住李正中,“李公公,您糊涂了?您剛才說了,德馨郡主是皇上眼里的紅人,萬萬得罪不得,您為何如此明目張膽地加害?!”
李正中笑瞇著
眼睛,向門外的妙音,“寧和王是皇上的表弟,又是太后的親侄子,誰能得了他?到時候皇上問起,你我都不承認,這里也無第三個人知曉,咱們死咬著是蘇妙音自己拿的,此事只置蘇妙音一人!”
Advertisement
焦元祿恐慌地抓住他的手臂,“李公公,盜宮中財,可是斷手斷腳的,且那東西又是進貢給太后的,且三年才得這麼一匹,這可是重罪死罪!”
“死的又不是你,你怕什麼?!”李正中這就疾步出去庫房。
焦元祿忙又追上他,拉著他躲到墻邊,避開往來的太監宮。
“你……你與這德馨郡主有何仇怨?你若不說清楚,我現在就去皇上面前告你!”
“拿人錢財與人消災罷了。”李正中說著,就從腰間扯下玉佩給他塞進手里,“你我共事多年,你可別去做蠢事,回頭我拿到好,不了分你一份。”
焦元祿無奈,死前向后,勉為其難,左右看了看,便將玉佩兜袖中。
兩人卻都沒發現,有個人正鬼魅般無聲立在后的墻頭上。
墻那邊,焦元祿和李正中剛走。
墻這邊,皇長赫連霓正帶著幾位小公主自繡坊出來。
見拓跋玹柱子似地立在墻頭上,著自己三個月孕的肚皮
笑了笑,終是忍不住喚道:“玹兒,你跑墻上去做什麼?”
拓跋玹脊背一凜,轉頭就見孩們依著由矮到高的順序整齊排著隊,一個個花枝招展氣韻不俗,仙娥一般賞心悅目。
赫連霓正是皇后段實蓮嫡,丞相段實意的親外甥。
后面的一眾小公主忙都朝拓跋玹行禮喚表哥。
他忙飛而下,上前俯首行禮,“給大表姐請安,讓各位表姐表妹們見笑了。”
拓跋玹忙示意們免禮,就近看向素來行事乖巧且與他十分親厚的十八公主赫連珺。
“珺兒,我離京之前代你寫的字,你可寫好了?”
眾公主都疑地看赫連珺。
赫連珺只七歲,正是瑞王赫連遙同母親妹。
小丫頭被問得一頭霧水,白地小手抬起,抹了抹腦門,卻沒想起他代過什麼,小小的蘋果臉兒頓時就漲紅了,“表哥你……你好像沒有讓珺兒寫字呀!”
大公主赫連霓看著萌態無辜,不莞爾。“玹兒,素來貪玩,你讓寫什麼怕是轉眼就忘了,回頭多寫兩張補上。”
赫連珺小臉兒頓時慘兮兮的,懇求地看拓跋玹。
拓跋玹上前就拉過赫連珺斜夸的緞小布袋,從里面拿了一張紙和筆,又在口中點了口水
,在紙上寫道,“皇外婆,李正中已被太子收買,意圖利用百福綃紗栽贓謀害妙音,懇請皇外婆秉公置,并及時趕往蘇家取回蛟綃紗,玹兒叩拜皇祖母圣恩!”
寫完,他對赫連珺眨了下眼睛,便疊好了紙,給赫連珺放在布袋里,“回去之后,好好練習,明日我檢查,不得有誤!”
赫連珺眨著大眼睛,忽閃忽閃地看他,又看布袋,“哦!”
一眾公主都告退,拓跋玹知道赫連霓要返回公主府,這便扶著的手肘一起往外走,心里估著妙音與那馬車前行的速度……
“大表姐這是帶著表妹們來做什麼?”
“還能來做什麼,們與我一樣,都是要嫁人的,為了不讓婆家嫌棄,繡工總要過得去才,今日的課業這是剛結束。”赫連霓嗔怒地瞥他一眼,“你和遙兒出征幾個月,回來也不到公主府看我和你姐夫,今晚你喚遙兒過來,咱們一起吃頓飯。”
“是。”
赫連霓拉著他一起坐上肩輦。
肩輦起行,才問道,“你剛才在那墻頭上做什麼?”
“沒什麼,玹兒剛在藥房服了湯藥,閑來無聊,便找了一高賞景,剛才發現,自那片墻頭賞朝,格外!”
赫連霓卻不信他這滿謊
言,“罷了,你不想說,表姐也不你說,不過,聽說明霜那丫頭很可憐,如今被囚在冷宮隔壁的破屋里。對你癡心一片,你不去探?”
拓跋玹道:“玹兒消不起的癡心,還是不去打擾的好。”
赫連霓悲憫地嘆了口氣,“明霜爹謀反,罪證確鑿,如今已經被死,趙家人和蘭妃也都疏遠了明霜……也是可憐!”
“大表姐,可憐之人必有可恨之,趙明霜的事您還是管為好,免得惹火燒。”拓跋玹言盡于此,再不想多言,便閉目養神。
赫連霓啞了一下,看著他俊的側,再不知該說什麼好。
肩輦行到皇宮大門,正應了拓跋玹掐算的時辰,與妙音出宮的馬車不期而遇。
李應坐在車轅上,見是大公主肩輦,忙示意車夫停下,迅速俯首跪地。
妙音在車廂里察覺馬車停下來,掀開車窗垂簾正要問李應什麼事,卻不經意間正注意到,行經一旁的肩輦上,正坐著一對兒璧人。
那肩輦上尾花的垂紗奢華富麗,子頭戴冠,細眉若遠山,杏眼如水,妝容致,姿態貴雅地目不斜視,一華貴艷麗的石榴紅袍,越襯得那圓潤的臉格外艷白膩。
那男子卻是——拓跋玹。
(本章完)
猜你喜歡
-
完結1409 章
農門小醫妃
再次醒來,曾經的醫學天驕竟然變成了遭人嫌棄的小寡婦?顧晚舟表示不能忍受!直到……因緣巧合下,她救下生命垂危的燕王。他步步試探,她步步為營。亂世沉浮中,兩人攜手走上人生巔峰。
253.1萬字8.18 62446 -
完結609 章
神醫毒妃權傾天下
“本王救了你,你以身相許如何?”初見,權傾朝野的冰山皇叔嗓音低沉,充滿魅惑。夜摘星,二十一世紀古靈世家傳人,她是枯骨生肉的最強神醫,亦是令人聞風喪膽的全能傭兵女王。素手攬月摘星辰,殺遍世間作惡人。一朝穿越,竟成了將軍府變人人可欺的草包四小姐,從小靈根被挖,一臉胎記醜得深入人心。沒關係,她妙手去胎記續靈根,打臉渣男白蓮花,煉丹馭獸,陣法煉器,符籙傀儡,無所不能,驚艷天下。他是權勢滔天的異姓王,身份成謎,強大逆天,生人勿近,唯獨對她,寵之入骨,愛之如命。 “娘子,本王想同你生一窩娃娃,我們什麼時候開始實施?”某人極具誘惑的貼在她耳後。生一窩?惹不起,溜了溜了。
110.5萬字8 65819 -
完結585 章
小公主又幫母妃爭寵了
穿書成了宮鬥劇本里的砲灰小公主,娘親是個痴傻美人,快被打入冷宮。無妨!她一身出神入化的醫術,還精通音律編曲,有的是法子幫她爭寵,助她晉升妃嬪。能嚇哭家中庶妹的李臨淮,第一次送小公主回宮,覺得自己長得太嚇人嚇壞了小公主。後來才知道看著人畜無害的小公主,擅長下毒挖坑玩蠱,還能迷惑人心。待嫁及笄之時,皇兄們個個忙著替她攢嫁妝,還揚言誰欺負了皇妹要打上門。大將軍李臨淮:“是小公主,她…覬覦臣的盛世美顏……”
105.9萬字8 170382 -
完結492 章

春宴渡
她只是一個農家的養女,貧苦出身卻不小心招惹了一個男人,被迫做了人家的妾,她委曲求全卻也沒能換來太平安逸的日子,那就一鼓作氣逃離這個是非之地。她拼了命的逃離,卻在窮途末路之時,看到他,她本以為他會披星戴月而來,卻不想他腳踩尸骨,跨越尸海擋在自…
90.6萬字8 15285 -
完結546 章
王爺您的醫妃有點狂
穿越成丑顏農女,空間隨身,神泉在手,丑怕什麼?逆天異能為伴,芊芊玉手點石成金,真是太好了!趕娘倆出府的渣爹想認回她?門都沒有!她的夢想,是建立一支屬于自己的異能部隊,掠殺天下黑心狼,虐盡天下渣與狗!誰知,一朝風云變幻,她看上的男人,他要反-朝-庭,立-新-國!好吧,既然愛了,那就只有夫唱婦隨,一起打天下嘍!這是一個你做獵戶,我是農女,你做皇帝,我是女王,最終江山為聘,獨愛一生的暖寵故事!
102.8萬字8 58725 -
完結368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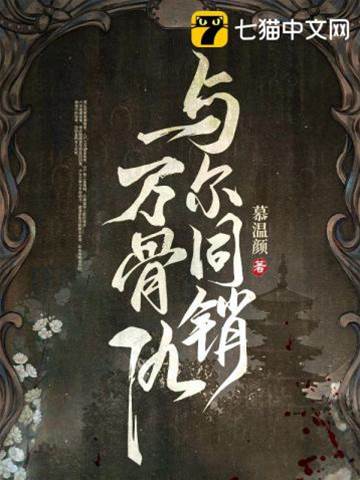
與爾同銷萬骨仇
深山荒野狐狸娶親,人屍之內竟是魚骨,女屍愛上盜墓賊,吊滿詭異人影的地宮...... 六宗詭譎命案,背後隱藏著更邪惡的陰謀。 少女天師與年輕尚書,循著陰陽異路解決命案,卻每每殊途同歸。 暗夜中的枯骨,你的悲鳴有人在聽。
32.6萬字8.18 8221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