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枷鎖》 第51章 第51章
橋市上浮鋪林立,小販在橋面兩側設攤售,來往人群絡繹不絕,頗為熱鬧。
林苑立在一攤位旁看手藝人編草蚱蜢的間隙,暗自打量了下前后跟隨出來的人。
婆子兩人,護院加上抬轎的有六人。
瞧起來對的看管有所松懈。
可暗究竟還有沒有人隨著,也不敢十分確定。
只在心里反復揣測,大概是沒有。畢竟與他既已將話說開,在他看來已了賤籍,如今依附著他日子過得安穩,斷沒再逃跑的必要。既然如此,便著實沒有必要再額外派人盯梢著。
林苑不著痕跡的收回了目。
看著手藝人籃子里那些活靈活現的草蚱蜢,隨口問了句:“皆是蚱蜢嗎?可有旁的小玩意?”
那手藝人見生意來了,忙道:“現的倒是沒,不過可以現編。夫人是想要個什麼小玩意,家禽,鳥,還是閣樓桌椅等,我都能馬上給您編來。”
林苑道:“那你看著編些可些的小之類的吧。”
“好嘞夫人,您就擎等著瞧好了。”
手藝人歡喜的拿出藤草來,在編前問了聲:“那我先給您編個貓狗以及兔子可?”
“的。”
見面前的夫人甚是好說話,手藝人為了多賣些銅錢,上不由打著殷勤:“夫人要不要再編個屬相?給您家中的小公子或小郎耍玩,想必他們定會十分喜歡。”
Advertisement
林苑怔了瞬。
旁的婆子臉微變,沖著那手藝人當即呵斥:“胡說什麼呢!我們家夫人尚且年輕,有兒也是將來的事。做你的活計便是,里瞎咧咧個什麼。”
手藝人知道自己言語冒犯了,趕忙連連道歉。
林苑回過神來,道了句沒事。
他放下心來,手上繼續編著,可卻閉起不敢再隨意說話了。
“等編好了你說的那幾個小,再給我編個小馬駒吧。”
手藝人自然應承下來。
可那那婆子卻陡然屏住呼吸,忍不住悄悄往林苑面上覷過一眼,而后迅速低下頭來。
今夜的床笫之間,晉滁頗有幾分狠辣。
一回過后,林苑險些昏了過去,眼前一陣昏過一陣,好似神魂在外飄,子都似不是自個的。
晉滁撈過床邊案上的參茶,吃了口哺喂了過去。
林苑星眼微餳,似睜非睜著眼,被人抵著迫吞咽著,同時也被迫承著那隨之而來的親纏裹。
等放開了,他就起了來,開床帳喚人抬水進來。待拾掇完后就披了外坐在床沿上,靜等恢復。
林苑勉強恢復兩三氣力后,就撐了坐起,歪靠在床頭上,強提著神半睜著眼看他。
“瞧著殿下,似乎不大如意?”
晉滁的聲線里帶著冷淡:“若沒記錯的話,當日是你先提及要將過往放下的。怎麼,如今你可是要出爾反爾?”
林苑幾乎是立即就明了他今日的反常是源自何。
“只不過……就是個念想。”
非草木,如何能時刻維持冷靜與理智。所以在今個無意被那手藝人及心底事時,饒是知曉此舉大概會令他不快,可還是忍不住想要他編一個瑞哥的屬相。
料定他會不虞,只是沒料到,他竟如此介意。
那也只不過是個……微不足道的小念想而已。
晉滁徑直問:“藏哪兒了。”
“沒藏。”林苑緩緩移開目,朝屜的方向示意了下,聲音低弱:“放那了,上數第二格。”
話音剛落,他就起了,直接來到床榻不遠的木柜前,拉了屜,從那一盒子的小玩意中,將那草編的小馬駒單獨給拎了出來。
一手拎著小馬駒,另一手撈過案上的燭臺,他大步朝走來,而后立在榻前無聲盯視著。
林苑對他解釋:“其實我就只是想著,畢竟生養過一場……”
晉滁不耐的打斷:“手。”
便止了口,不再說了。
慢慢攤開手心來,看著他將那活靈活現的草編小馬駒,重重的擱掌上。
晉滁盯著,無聲迫。
林苑知他意思,也自不會違逆,就前傾了些子,親自將掌心那湊近了他手中燭臺。
干草遇上明火,一下子就燃了起來。
他劈手從掌心里奪過,將燃燒著的草編玩意一把扔在地上,任其燃灰燼。
“忘了嗎?”
林苑低聲:“忘了。”
“記住了,是你先提及要忘了過往重新開始。若你敢出爾反爾,那就休怪孤翻臉無。”
“我記住了。”說到這,林苑緩緩抬眸,清淺的目落在他肅厲的面容上:“兒子,日后總會有的。”
便清楚的看見他的面,陡然變得晦暗不明。
晉滁離開后,林苑兀自等了小半個時辰,卻還是未等來婆子端來避子湯。
心里一突,開始心緒不寧起來。
自打從教坊司搬出來,已有小半個月時間,可每次事后,他不知是忘了還是其他,從未讓人給熬避子湯來。
也不好單獨去買麝香,以防惹他狐疑猜忌,平生事端。在弄不清他想法前不敢輕舉妄,可這般耗著又不是個事,他要的這般頻,饒是有些避孕手段,可還是有些心憂。
今夜都這般暗示,相信他聽得出來。
可他依舊無于衷。
林苑就有些坐立不安了。
他這是想做什麼。
這些時日來,他們之間的相大概平靜,有時候他也能平心靜氣的與談幾句。看得出來,他的確是在試著忘卻過往,也試著想擺對他的影響。
可如今他的做派,倒讓有些懷疑的猜測。
隔了一日后,晉滁再次過來。
這一夜,事后他竟然沒有離開,卻是整宿歇在了林苑這里。
林苑心掀起了滔天巨浪。
接下來幾日,他竟也不是隔日一來,卻是每夜都來。
雖不是每夜皆要行事,可他每夜宿在這,卻是讓夜夜不得安枕。
不敢深眠,唯恐夢中吐出真言。
小小的宅院里,在那一方不算寬大的床榻中,帷帳里的兩人在夜中頸而眠,宛如世間最普通不過的夫妻。
可林苑知道,這是虛假的溫。
只是不知,他知不知。
又過了幾日之后,林苑終于不再猶豫,在清早上目送他上朝離去后,轉就去了東廂房。
這些時日已經攢夠了一副藥,可以趁著煎熬補藥的時候,熬上一碗。
需要一個合理的恃寵而驕的理由,也需要一個能徹底避行房事的理由。
猜你喜歡
-
完結310 章

重生有喜:皇後孃娘撩又甜
前世,鄰居家竹馬婚前背叛,花萌看著他另娶長公主家的女兒後,選擇穿著繡了兩年的大紅嫁衣自縊結束生命。可死後靈魂漂浮在這世間二十年,她才知道,竹馬悔婚皆因他偶然聽說,聖上無子,欲過繼長公主之子為嗣子。......再次睜眼,花萌回到了被退婚的那一天。自縊?不存在的!聽聞聖上要選秀,而手握可解百毒靈泉,又有祖傳好孕體質的花萌:進宮!必須進宮!生兒子,一定要改變聖上無子命運,敲碎渣男賤女的白日夢!靖安帝:生個兒子,升次位份幾年後......已生四個兒子的花皇後:皇上,臣妾又有喜了覺得臭兒子已經夠多且無位可給皇後升的靖安帝心下一顫,語氣寵溺:朕覺得,皇後該生公主了
69.4萬字8.18 60887 -
完結436 章

秀色可餐:夫君請笑納
一窮二白冇有田,帶著空間好掙錢;膚白貌美,細腰長腿的胡蔓一朝穿越竟然變成醜陋呆傻小農女。替姐嫁給大齡獵戶,缺衣少糧吃不飽,剩下都是病弱老,還好夫君條順顏高體格好,還有空間做法寶。言而總之,這就是一個現代藥理專業大學生,穿越成醜女發家致富,成為人生贏家的故事。
98.4萬字8 16809 -
完結164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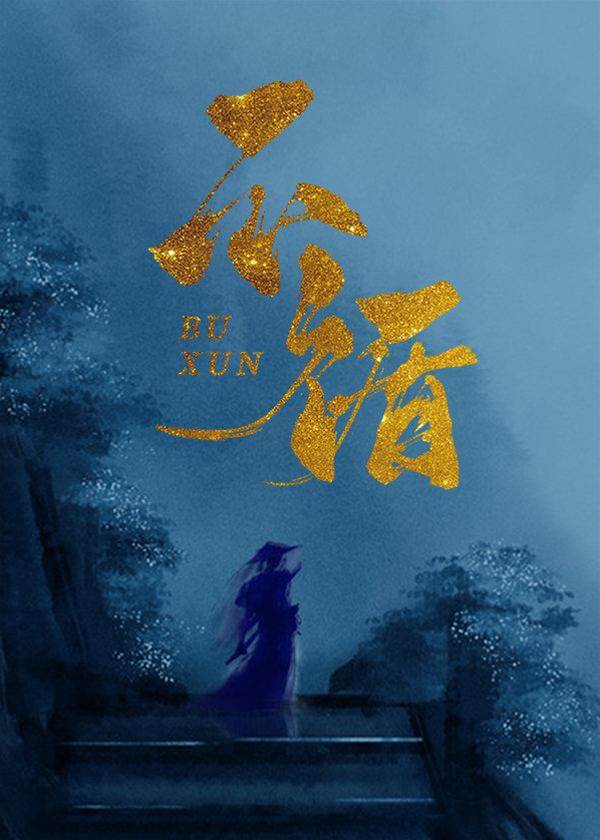
不循(重生)
邵循是英國公府的嫡長女。 父親是一品公侯,母親是世家貴女,宮裡的淑妃娘娘是她姑姑,太子之位的有力競爭者三皇子是她表哥。 人生中唯一的不足就是生母早逝,繼母不親,原本應該榮華富貴不缺,波瀾壯闊沒有的過完一輩子,誰知一場夢境打破了一切—— 邵循夢見自己的堂姑為了給兒子剷除對手,犧牲侄女的名節用以陷害風流成性的大皇子,害得自己清白盡毀,只能在鄙夷中被大皇子納為側妃。 大皇子風流成性,大皇子妃善妒惡毒,邵循醒來後生生被嚇出了一身冷汗。 誰知這夢做的太晚,該中的招已經中了,無奈之下決定拼死也不能讓噩夢成真,為了躲開大皇子,慌不擇路的她卻陰差陽錯的撞進了另一個人懷裡…… * 邵循清醒過來之後跪在地上,看著眼前繡五爪金龍的明黃色衣角,真的是欲哭無淚—— 這、這還不如大皇子呢! * 1雷點都在文案裡 2年齡差大 3請原諒男主非c,但之後保證1v1
49.3萬字8.33 50004 -
完結194 章

曾聽舊時雨
鎮北大將軍的幺女岑聽南,是上京城各色花枝中最明豔嬌縱那株。 以至於那位傳聞中冷情冷麪的左相大人求娶上門時,並未有人覺得不妥。 所有人都認定他們是郎才女貌天造地設的一雙。 可岑聽南聽了卻笑,脆生生道:“世人都道他狠戾冷漠,不敢惹他。我卻只見得到他古板無趣,我纔不嫁。” 誰料後來父兄遭人陷害戰死沙場,她就這樣死在自己十八歲生辰前夕的流放路上。 再睜眼,岑聽南重回十六歲那年。 爲救滿門,她只能重新叩響左相高門。 去賭他真的爲她而來。 可過門後岑聽南才發現,什麼古板無趣,這人裝得這樣好! 她偏要撕下他的外殼,看看裏頭究竟什麼樣。 “我要再用一碗冰酥酪!現在就要!” “不可。”他拉長嗓,視線在戒尺與她身上逡巡,“手心癢了就直說。” “那我可以去外頭玩嗎?” “不可。”他散漫又玩味,“乖乖在府中等我下朝。” - 顧硯時從沒想過,那個嬌縱與豔絕之名同樣響徹上京的將軍幺女,會真的成爲他的妻子。 昔日求娶是爲分化兵權,如今各取所需,更是從未想過假戲真做。 迎娶她之前的顧硯時:平亂、百姓與民生。 迎娶她之後的顧硯時:教她、罰她……獎勵她。 他那明豔的小姑娘,勾着他的脖頸遞上戒尺向他討饒:“左相大人,我錯了,不如——你罰我?” 他握着戒尺嗤笑:“罰你?還是在獎勵你?” #如今父兄平安,天下安定。 她愛的人日日同她江南聽雨,再沒有比這更滿意的一生了。
29.9萬字8 139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