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靈筆錄》 第45章 神秘的男人
周白曼一次無意中發現慕寒止用白布纏裹腹部,開始以爲慕寒止是爲了臺上表演更好的塑形,可是時間長了,慕寒止一天天大起來的肚子已經不是白布能掩飾的。
樹大招風,背地裡妒忌慕寒止的又何嘗一個人,二十年前名聲對於人是很重要的,何況是一個戲子。
說到這裡我多有些能明白周白曼話的意思,慕寒止即便是再出的青,終究也只是一個戲子,和我的職業一樣,古時候是下九流行當,坊間有所謂戲子無義、婊子無的言論,在大多人眼裡,戲子和婊子之間的差距並不大。
在以前婊子與戲子之間沒有明確的界限,一般也賣藝,而藝人也賣,都是吃花飯的,所以被大家瞧不起,所謂的道德義氣,本來就是給有份的人準備的,連份都沒有的人,談不到這些,也沒資格談。
或許現在有這樣想法的人已經很,但是慕寒止偏偏未婚先孕,這話柄是送到別人手中,想不被翻騰都難。
正如同周白曼繼續告訴我們的,慕寒止想藏有了孩子的事被一天天大起來的肚子不攻自破,風言風語也隨之而來,要多難聽有多難聽,以至於慕寒止本沒有心思再演出,這個時候邊正需要一個能相互傾訴和幫助的朋友。
這個人本來應該是周白曼,可是人言可畏,周白曼擔心落下一句以類聚的指責,非但沒有站在慕寒止的邊,反而選擇了疏遠,這也是周白曼在慕寒止自殺後一直揮之不去的憾和過失。
“在你和慕寒止關係疏遠之前,你可曾聽提起過邊的男人?”雲杜若認真地問。
“沒有!”周白曼斬釘截鐵地回答。“寒止幾乎從來不會和我談起這方面的事,不說我也不會問。”
Advertisement
“那你好好想想,邊出現過的男人,有沒有一個名字裡有輝字的?”我僥倖地問。
周白曼細細回想了良久,慢慢對我們搖頭。
“寒止接過的男人大多是團裡的,但我可以保證和這些人都僅限於工作上的流,絕對不會有上的,至於有輝字的,在我認識的人裡面真沒有。”
我和雲杜若聽到這裡多都有些失,周白曼說了這麼多,我們對慕寒止這個人有了新的認識,可不管怎麼看,都不像是有什麼的人,如果真要說有,那就應該是那個一直沒面的男人,慕寒止似乎是在刻意迴避不想讓人知道這個男人的存在。
或許還有一個可能。
我心裡暗暗的想,或許是那個男人不願意讓慕寒止把他公開出去。
“男人……”周白曼忽然想起了什麼,回憶了半天對我們說。“姓輝的男人我不清楚,不過我想起了一件事。”
“什麼事?”雲杜若急切地問。
“寒止很自律生活也很規律,平日裡從來不和任何男人有過多接,更不會有爭執,可有一晚,那還是在寒止肚子沒大的時候,我從練功房回宿舍,已經是晚上了。”周白曼一邊回憶一邊對我們說。“路過劇團後面的花園時,我聽見寒止的聲音,平時說話都很溫,可那一次我聽見的聲音很激和傷心,像是在和誰爭吵。”
“然後呢?”我皺著眉頭問。
“我當時也很好奇,擔心會有什麼事,就走過去喊,寒止聽見我聲音轉過,往前走了一步,好像是故意在遮擋後的人。”周白曼努力回憶當時的況,生怕錯過什麼。“哦,和爭執的是一個男人,我斷斷續續聽見那男人說什麼,再等等,很快……其他的沒聽清楚,我走過去後就再沒聽見那男人的說話。”
“你還能不能回憶起那個男人長什麼樣?”雲杜若有些激的問。
“當時天黑,他又站在樹下我看不見他的臉。”周白曼憾地搖搖頭。“不過……那男人上有一味道,很特別。”
“味道?!”我很認真地看看周白曼。“是什麼味道?”
周白曼往我這邊靠了靠,把頭探向我的聞了一會後,肯定地點頭。
“就是你上這個味道。”
我一愣,雲杜若也吃驚地看著我,我擡起手放在鼻前聞了很久,皺著眉頭詫異地說。
“我……我上什麼味也沒有啊?”
“有!”雲杜若聞了片刻後興地擡起頭。“你聞不見是因爲你已經悉了你上的味道,不過其他人能聞出來。”
“什麼味道?”
“福爾馬林!”
我恍然大悟,天天呆在解剖室裡面,接到的全是,而房間裡瀰漫的正是福爾馬林的氣味,最開始我還能聞到,慢慢的就如同雲杜若說的那樣,我已經習慣了這種味道,完全分辨不出來。
周白曼說那個和慕寒止有爭執的男人上有同樣的味道,能沾染上這種氣味的人,多半是在和醫務有關的地方工作,我突然想起無名案的作案手法,以及蘇梅上的合,這些都是需要極高醫學專業知識的。
而和慕寒止爭執的男人很可能也從事醫務方面的工作,慕寒止案件最大的疑點就是那個從未面的神男人,在二十年後,有一個通解剖和醫學知識的兇手,難道這是巧合!
這次走訪終於有了新的發現,雲杜若仔細詢問周白曼後,其他的並沒有多價值,不知不覺已經是晚上,我們起告辭。
走到門口我忽然很僥倖地問了一句。
“你這兒有慕寒止的照片嗎?”
“有啊!”
周白曼的回答讓我和雲杜若頓時目瞪口呆震驚地看著,周白曼完全不明白我和雲杜若怎麼會瞬間出這樣的表,讓我們在客廳等著,去給我們拿出來,雲杜若和我本坐不住,寸步不離地跟著周白曼,生怕再和劉越武一樣出現什麼意外。
周白曼當著我們面拉開屜,拿出一本很老式的相冊,坐到沙發上,我和雲杜若坐到兩邊,急切的想要看看從未真正見過的慕寒止到底長什麼樣。
周白曼的兒子給我們送水進來,看抱著照片好奇地說了一句。
“我媽把這相冊看的可金貴,從小不讓我們,也不知道里面都是誰的照片。”
聽兒子的話我心裡也能猜到,這對於其他人來說或許就是一本普通的相冊,可想必在周白曼心目中,這是回憶也是懺悔的方式。
相冊被翻開,第一張是一個人在臺上表演的照片,上面的人碧綠的翠煙衫,散花水霧綠草百褶,披翠水薄煙紗,肩若削腰若約素,若凝脂氣若幽蘭,無骨豔三分。
即便是看著照片,我也不得不承認,照片中的人的確是得令人窒息。
“這就是慕寒止!”周白曼嘆了口氣,對著照片歉意地說。“這是演出時拍的,當時說好的,演出的時候我替拍,我演出的時候幫我拍,後來和關係疏遠,把我的照片還給我,可我一直留著的沒捨得給。”
周白曼一邊說一邊慢慢地翻著相冊,上面每一張照片雖然都形態各異,但照片中的人水袖曼舞婀娜多姿,雖施黛可五猶如雕細琢緻的堪稱完。
當週白曼翻開相冊的最後一頁,一張人沒有化妝的照片出現在我和雲杜若的面前。
照片的背景是在房間裡,應該是臥室,人是坐在牀邊,背景的櫃上擺放著兩個緻的花瓶,照片中的嫣然一笑,端莊大方眉目如畫,明豔人,天生的人胚子,周白曼把相冊遞到我們手中,嘆了口氣。
“寒止化不化妝都豔人,每次看見的照片,我就想起以前的事,在臺上的風采亦如發生在昨天。”周白曼嘆息地對我們說。“這張照片是寒止去世之前的三天,我知道曉軒生日快到了,想起之前那麼照顧我,去看,那天寒止心尤爲的開心,說很久沒拍照,讓我替拍一張……沒想到居然了的絕照。”
“這……這就是慕寒止?!”我眉頭一皺還是有些不敢相信的問。
周白曼擡手著眼角的淚花點點頭。
“你……你怎麼沒有死?”
我在說完後,才意識到自己說錯了話,周白曼母親今天過世,我居然說出這樣的話,要不是雲杜若攔著,我會被一屋人直接送到外科然後轉科的。
下了樓雲杜若還在怪我不會說話,可我著頭並沒有在意這些,來回走了幾步疑地說。
“有人回到慕寒止的房間拿走相冊,劉越武在給我們照片時遇害,然後接著是和慕寒止關係最爲親的蘇梅,我們之前一直推斷殺人的機是兇手不想有人知道慕寒止的樣子。”
雲杜若聽到這裡,估計也意識到我當著周白曼說那句話的意思,之前我們關於機的推測是錯誤的,否則周白曼還珍藏的照片會讓爲繼劉越武和蘇梅後第三個被害的人。
可週白曼安然無恙,可見機並不是在慕寒止的照片上,也就是說,被拿走的相冊中以及劉越武給我們的照片上還有蘇梅,所知道的是另一件。
猜你喜歡
-
完結153 章

我是千年大棕子
女主膽小貪財愛吐槽,沒身材沒長相甚至經常沒腦子,男主面癱嗜睡食量超級大,戰鬥力強,這兩個看著讓人覺得不搭調,可在一起時,女主看得懂男主莫名其妙的顏文字,能包容他各種稀奇古怪的習性,男主永遠冷漠生人勿進的模樣,卻唯獨把依賴和僅存的溫情留給女主,保護她疼愛她,這樣的相識相愛相處相守,又真和諧無比。 重點提示:女主是個粽子,全文驚險刺激又歡樂,還有感動,強烈推薦!
45.2萬字5 8638 -
完結410 章

我是倖存者
喪屍病毒忽然傳遍紐約.人類紛紛中招,華裔少年遇此難題,只得挺身而出,在抗擊喪屍的過程中,也遇到了許多角色,高中舞會皇后、紅燈區應召女郎、刻薄的公司高管、黑幫槍手、癮君子…誰纔是真正的英雄?
128.5萬字8 6373 -
完結1716 章

詭寢驚魂
我應聘進了一所大學的女寢當宿管,那些女生熱情的有點反常……夜半的哭聲,著火的寢室,不存在的房間,在記憶的最深處,隱藏著一個光怪陸離的世界…夜已深,夢未半,山鬼吹燈滅,孤魂何處歸?
313萬字8.18 17316 -
連載1380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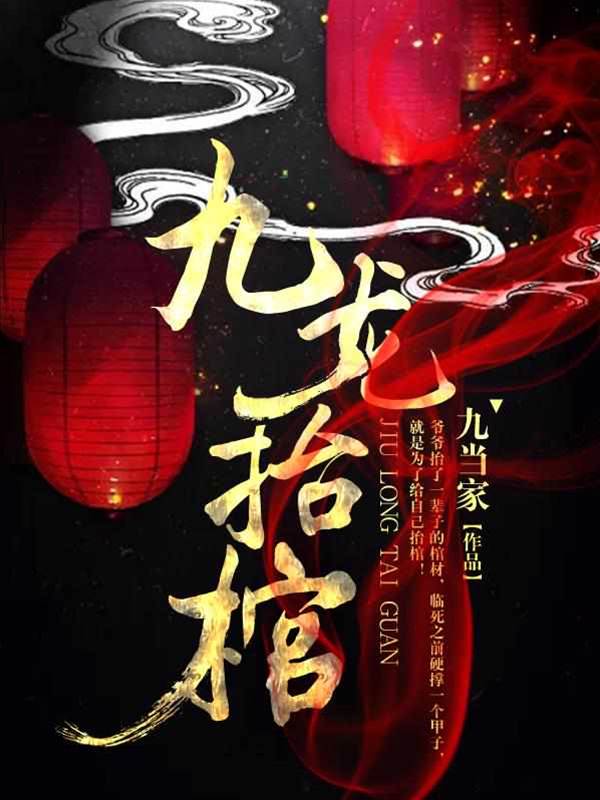
我是一名抬棺匠
爺爺出殯那晚,我抬著石碑在前引路,不敢回頭看,因為身后抬棺的是八只惡鬼……
272.9萬字8.46 26618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