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界大佬的甜妻日常》 第445章 你們是想逼死我麼?(改錯字)
在餐桌邊落座,郁庭川尚未提昨晚的事,依然是往日那番晚輩姿態,顧守業年歲已高,但他不是個老糊涂,曾經又居高位,無論是眼界還是懷,不是尋常的八旬老人能比。
況且,顧老是知道郁庭川的。
早些年,自己小兒子和郁庭川在日本讀書,比起顧政深的三天打魚兩天曬網,郁庭川是真的在讀書,后來回了國,在郁祁東之后接手恒遠,顧政深跟著郁庭川一起做生意,這才把他從紈绔子弟這條道上給掰了回來。
顧政深和郁庭川都過而立,兩人的格卻天差地別。
郁顧兩家向來好,顧守業還記得自己第一次見到郁庭川,郁庭川還是個半大年,不像今時今日這般難以捉,卻也有著不符年紀的沉穩斂。
后來得知這是郁林江在外面的兒子,顧守業也就明白了。
只不過,郁庭川上頭還有個能干的異母哥哥,他就是再優秀,也生生被了一頭。
直到九年前郁祁東出車禍,郁庭川這個郁家次子才顯出來。
雖然顧老不混商界,這些年也有所耳聞,和郁祁東相比,郁庭川在做生意方面更勝一籌,手段也更加強獨斷。
所以,郁林江和這個次子的經營理念難免相左。
郁庭川離開恒遠,顧老作為過來人,不覺得是虎落平之勢。
有些人,即便不靠家族蒙,或許過程艱難了點,但照樣能白手起家,為生意場上的一號人。
再說,郁庭川已經是個三十幾歲的男人,在恒遠這麼多年,手里不可能沒有點家底,如今離開恒遠,自然不會真的一無所有。
顧老端起飯碗的時候,腦海里已經把事過了一遍。
顧政深未婚,雖說在外面有房子,但因為怕二老孤單,他大多數時候還是住在家屬院。
Advertisement
昨晚上,顧政深接到姐夫電話,陪著去醫院,人年紀大了睡眠淺,顧老夫婦倆知道兒子出過門,今天早上也問了,顧政深只說三姐家有點事。
直到黃昏,李靖明下班來了趟家屬院找顧政深,再被顧老問起,顧政深才據實代。
知曉孫做下的事,顧老的臉都黑了。
特別是聽到顧政深說,凌晨在醫院產房前,郁庭川并未理會前去致歉的顧家人。
不理會,那就是沒接道歉。
顧政深和郁庭川多年好友,很了解郁庭川的為人,如若不是被犯底線,他不至于這樣不給顧家面子。
但是將心比心,不管是顧老、顧政深亦或是李靖明,沒人覺得在這事上是郁庭川心狹隘,換做他們中任何一個人,如果自己妻子被推得早產,母子平安尚且好說,要是孕婦和孩子有一個出事,恐怕都做不到對著‘兇手’和悅。
郁庭川在產房前說的那句話,就算不是雷霆盛怒,也是有了火氣,顧老聽完不語,隨后讓李靖明帶話給自己的三兒,讓顧錦云別只顧部隊的事,出時間好好管教一下顧清薇。
至于醫院那邊,顧老覺得還是要去道歉。
既然是他們做錯的事,人家不原諒是一回事,但他們不去道歉,那就是他們失了禮數,錯上加錯。
沒想到,李靖明前腳剛離開,郁庭川就親自登門拜訪。
一頓飯吃完,顧老放下碗筷的同時,抬頭看向坐在左下側的郁庭川,眼神顯得溫和:“阿深晚上有個飯局,你來前剛出去,也是不巧,所以只能讓你陪我們兩個老家伙吃飯。”
郁庭川已經擱筷,正用巾手,聽了顧老的話,也是微微笑:“算起來,上回政深我來顧家吃飯,已經是前年的事。”
“難為你記得。”顧老的眉頭舒展了些:“你這些年事業忙,不出空很正常。”
稍稍停頓,顧老忽然問:“我下午聽政深說,你現在那個妻子今天凌晨已經生下孩子?”
郁庭川點點頭:“早產了個把月,所幸孩子還算健康。”
這話郁庭川說的云淡風輕,顧老聽在耳里,卻不會真聽聽就算了,他的目看向這位世侄,郁庭川的雙眼皮深刻,哪怕神尚佳,但顯然是整夜未睡,白天恐怕也不得休息,以這種態勢過來顧家,怎麼會是來拉家常的?
顧老心里也明白,郁庭川沒有直接點破,是賣他這個長輩的面子,但是他不能打太極,干脆開門見山:“昨晚的事阿深已經告訴我,不提推人,單說言辭不當,已經是父母教無方,下午父親也過來,我讓靖明轉告錦云,可能明天就會帶著孩子去醫院,給你們賠禮道歉。”
說到這里,顧老有短暫的沉默:“……顧家出了這麼個口無遮攔的孩子,我也有責任,平日只覺得是母親慣,沒往細去想,在這里,庭川,幫我向你太太轉達歉意。”
在他們談事的時候,顧老太太已經離桌。
所以這會兒,餐廳里只有郁庭川和顧老兩個人。
郁庭川把團的巾輕丟在桌上,聽完顧老這席話,也知道這個老人是非分明,如若不然,他現在也不會坐在這里。
然而,有些事終究需要有個結果。
“我記得阿姨生嘉芝的時候,已經有四十歲。”
顧老太太是顧老的第二任妻子,顧政深和顧嘉芝是顧老太太所出,顧老前頭三個孩子,是已逝的太太所生,當年顧老太太生兒,因為是高齡產婦,九死一生,一度在圈子里為茶余飯后的談資。
顧老頷首,語氣著緬懷:“那個時候醫療水平沒現在好,我接到家里的電話說要生了,正在部隊里開個重要的會,不好為了私事耽誤工作,等我趕到醫院,已經過了七八個小時,還在產房里出不來。”
“好不容易生下孩子,自己卻整得大出,生生去了半條命。”提到老妻生產的苦,顧老也是慨萬千:“也因為這樣,特別疼嘉芝,覺得這個兒是拿命換來的。”
提到顧嘉芝,顧老重新向郁庭川。
顧嘉芝喜歡郁庭川,在顧家不是,就連他都以為,郁庭川會為顧家婿,結果卻有緣無分。
至于郁庭川娶的那個孩,顧老也知道一二,幾年前顧衡為和個孩在一起要買房,在家里鬧絕食,最后不了了之,去年顧衡回國,又在家里鬧了一場,說不要結婚了,跟他母親大吵一架后出車禍斷了。
顧錦云和繼母關系不錯,有空回來娘家,也會把兒子做的混賬事傾訴給顧老太太聽。
晚上睡覺前,顧老太太就一五一十告訴顧老。
年輕人的糾紛,老人家不想管,但那些事也在他這里掛了號。
現如今,郁庭川重提顧嘉芝出生的場景,顧老心知肚明,并非是與他敘舊,卻不得不順著郁庭川的話往下說,從郁庭川進門到現在,未曾流出大張撻伐的意思,反而是一派尊重的姿態,也因為這樣,他這個長輩被高高架起,有些話反倒不好再講,心里百味雜陳。
顧老也不得不承認,郁庭川確實比顧政深沉得住氣,也更懂得怎麼在和人談判時掌握主權,簡簡單單幾句話,斷了他為孫求的可能。
郁庭川說到顧老太太生的事,話外音就是:您自己經歷過這種類似生離死別的況,應該清楚當時的,昨晚的我亦是如此,您怎麼好意思讓我不計前嫌?
所以郁庭川這里,終歸是記上了!
然而,顧老提不起惱怒,反而心生愧疚,只嘆息道:“清薇推倒你妻子,致使早產,我知道說聲對不起送個花籃是遠遠不夠的,以后你如果有事,只要我力所能及,可以來找我,我這張老臉,還有那麼點用。”
郁庭川卻沒應下這番承諾,而是喊了他一聲顧叔,語氣顯出敬意:“您比我父親年長不,撇開輩分這一點,您和我祖父才算同齡人,記得有一年春節,我跟著政深來家里,您給政深紅包也沒落下我,政深的紅包比我厚,但是里面的錢卻不如我多,您給了我五張面值百元的紙幣,政深卻只有七張50元的紙幣。”
那個時候,‘錢’還不像現在這麼不值錢。
追溯起往事,郁庭川眼里有暖意:“您知我在郁家艱難,所以心生憐憫,這份時至今日我都不敢忘。”
說著,他的視線投向顧老,緩緩道來:“昨天晚上,不管有意也好無意也罷,對我太太的傷害已經造,再多的補救,也只能是事后補救,倘若推人的不是您孫,是孫子,今晚我不會過來坐在這和您講述這些往事。”
如果顧清薇是男的,凌晨在醫院,郁庭川怕是已經手教訓。
顧老聽懂他的言外之意,不置可否。
“年輕是好事,特別是十幾二十來歲,正是可以肆意而活的年齡,等活到我這個年紀,不管是想問題還是做事,早已沒了最初的熱,沖不一定是錯,它代表了活力和激,隨著人年紀越大,對這兩樣東西就變得越。”
桌上,擺著兩杯泡好的綠茶,空氣里飄著茶香,裊裊的熱氣氤氳在郁庭川括的襯衫前,也讓他的眉眼看上去多了幾分溫厚之意。
“只是有時候,就像那句俗語講的,沖也是魔鬼。”郁庭川的語調始終平和,像是和顧老在聊家常:“所以,20來歲也是該懂點事的年紀,除了不縱容,家里父母也該嚴以律己,如果把不好的習慣傳給孩子,譬如口舌之快,將來最終害的終歸還是自己,您說是不是?”
最后幾個字,顧老聽出這位世侄的尊重,他已無話可駁也不想反駁,點了點頭:“你說得對,年輕人需要約束,不然最后害人害己。”
就在這時,郁庭川換了個話題:“您應該知道,我太太年紀不大,為了嫁給我,也鬧出過不笑話。”
笑話,指的是恒遠五十周年慶上發生的事。
郁庭川這樣輕描淡寫的帶過,多是維護之意,話里也盡是寵溺:“小姑娘心思敏,不就吵著和我‘同歸于盡’,事后又悔得要命,倘若有您孫的膽量,當年被人冤枉收下支票,恐怕不僅要打上門,還要攪得男方家里天翻地覆才敢罷休。”
顧老聞言,眼角卻猛地跳了一跳。
“去年,外祖母住院,有人鬧去醫院,得老人家生生吐,為人母的心,我能理解,卻不敢茍同那種扭曲事實的強手法,那時我出差在外,也未明白我太太心里的苦悶,讓獨自下那樣的委屈。”
郁庭川那雙深邃的眼睛,已經對上顧老的目:“您和老太太雖不是年夫妻,這些年一路扶持走來,作為晚輩,也看在眼里。”
聽了這話,顧老的神愈發不好看。
郁庭川繼續道:“我太太前半生過于坎坷,背負了太多不該背負的東西,如今在我邊,我年長不,理應護周全,把好好護在羽翼下,而不是讓再去承那些莫須有的罪名。”
說著,郁庭川的眼神溫幾分:“作為丈夫,我此刻的心,顧叔想必有所會。”
顧老沒有接腔。
半晌,他長長的嘆了口氣:“原來是我教無方,這件事,我會給你和你太太一個待。”
這個話題結束前,郁庭川開腔道:“既然是陳年往事,造如今的局面,也是當年種下的因,不管結果如何,您依舊是我的顧叔,至于郁顧兩家的誼,不該到任何影響。”
顧老久久沉默,不得不承認,聽到郁庭川這樣說,他心頭生不出毫不悅或遷怒,只剩滿滿的嘆息。
這一日,郁庭川離開顧宅,天尚未暗。
他走出顧家的洋樓,背手停步在院子里,拔影落進灰蒙蒙的夜幕里,也落進許東的視線里。
許東等在車上,看著郁總在原地站了好一會兒,這才抬步出來。
……
晚上,顧守業親自前往三兒一家的住。
同去的還有被他回家的顧政深,和他讓顧政深找來的兩個材魁梧的‘保鏢’。
夜里8:26分,李家亮如白晝的客廳卻是哭聲一片,除了顧清薇,還有顧錦云的,這個往日強勢的人,如今泣不聲,哪怕哭泣依舊強勢,質問擲地有聲:“您是我的父親,可是今天晚上,您是想死我麼!”
顧守業坐在沙發上,雙手駐在拐杖上,閉著眼不為所。
李靖明也坐著,沒去看妻。
著姐姐眼角掛淚、哭紅鼻子的狼狽樣,顧政深的結微,卻說不出安或偏幫的話。
他沒想到,當年宋傾城收下20萬支票的事,居然是顧錦云杜撰的。
為的是讓自己的兒子死心。
當顧守業一通電話打給在大馬的孫子,問及孫子和宋傾城的關系,顧衡在電話那端沉默許久才回復:“是我喜歡傾城,想和在一起,本來打算跟我試試看,后來我媽不同意,就說我們不合適,我去大馬后我們沒再聯系。”
沒有什麼真相,比當事人說出來更有可信度。
這一晚,顧守業的態度不容商量,他給了顧錦云兩個選擇——要麼登報向被冤枉的孩致歉;要麼錄下視頻,連帶上顧清薇那份,傳給所有親朋好友,把真相告訴他們。
對格要強、把面子看得比命更重的顧錦云而言,無論哪個選擇,都無異于毀了,還在部隊工作,朋友都是高知分子,如果被人知道曾經造謠生事,以后要怎麼在部隊在圈子里立足?
猜你喜歡
-
連載0 章
嬌寵甜妻鬨翻天
前生,她心瞎眼盲,錯信狗男女,踏上作死征程。 沒想到老天開眼,給了她重活的機會。不好意思,本小姐智商上線了!抱緊霸道老公的大腿,揚起小臉討好的笑,“老公,有人欺負我!” 男人輕撫她絕美的小臉,迷人的雙眸泛著危險,“有事叫老公,沒事叫狗賊?” 寧萌萌頭搖的如同撥浪鼓,並且霸道的宣告,“不不不,我是狗賊!” 男人心情瞬間轉晴,“嗯,我的狗我護著,誰虐你,虐回去!” 從此,寧萌萌橫著走!想欺負她?看她怎麼施展三十六計玩轉一群渣渣!
246.6萬字8 59408 -
完結518 章

團寵女鵝是偏執大佬的白月光
錦城豪門姜家收養了一對姐妹花,妹妹姜凡月懂事大方,才貌雙全,姐姐姜折不學無術,一事無成。窮困潦倒的親生家庭找上門來,姜家迫不及待的將姜折打包送走,留下姜凡月;家產、名聲、千金大小姐的身份、未婚夫,從此以后盡數跟姜折毫無關系。.姜折踏入自己家…
95.4萬字5 132631 -
完結1752 章

腹黑萌寶,總裁爹地寵入骨
溫酒酒愛了傅司忱十年,結婚后傅司忱卻因為誤會選擇了其他女人。當他帶著帶著大肚子的林柔柔回來之后,溫酒酒失望至極,決心離婚。挺著一個大肚子,溫酒酒一尸三命。五年后,溫酒酒以大佬身份帶著兩只小萌寶回歸。瘋了五年的傅司忱將她抓回家中:“我們還沒離婚,你生也是我的人,死也是我的人!”當看到兩只翻版小萌寶時,傅司忱急了,“你們是誰?別搶我老婆!”
162.3萬字8 399631 -
完結1685 章
愛上你劫數難逃
一場代嫁,她嫁給了患有腿疾卻權勢滔天的男人。“我夜莫深不會要一個帶著野種的女人。”本以為是一場交易婚姻,誰知她竟丟了心,兜兜轉轉,她傷心離開。多年後,跟他長得一模一樣的小正太一巴掌拍在夜莫深的腦袋上。“混蛋爹地,你說誰是野種?”
303.9萬字8 22994 -
完結199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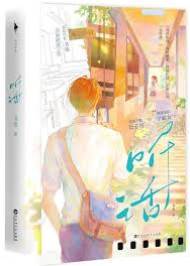
聽話
那不是程歲寧第一次見周溫宴。 她見過他意氣風發,見過他浪蕩不羈,見過他懷裏女孩換了一個又一個。 只是那次,她心動最難捱。 那天室友生日她走錯包間,偶然窺見他懶懶陷在沙發裏,百無聊賴撥弄打火機。 火苗忽明忽暗身旁女生和他說話,他勾着笑半天敷衍回個一字半句。 她回到包廂裏第一次鬼迷心竅主動給他發了信息,【今天聚會好玩嗎?】 下一秒,他回:【你不在沒意思。】 後來他們分手,多年後在風雨裏重逢,她被男友差遣輕視狼狽不堪。 他跨過一衆圍着他殷勤討好的人羣,不顧目光,拉住她的手,塞進一把傘。 冬夜昏天暗地光線裏,他垂眼看她,聲音淡淡:“撐傘,別淋雨。” 那一刻她這才知道,除了他以外都是將就。 朋友問那再後來呢?她淺笑着沒說話。 只是每年西園寺,雲蒸霞蔚煙火繚繞的銀杏樹下多了個虔誠的少女。 那天年初一,青衣僧人說有緣人贈了她一張紙條。 展開一看,字體熟悉,上面寫着‘一歲一禮,得償所願。’ 她下意識回頭,人海茫茫裏,一眼只看見他溫柔背影。
34.2萬字8.18 6032 -
完結94 章

他的鳶尾
【先婚后愛】【蓄謀已久】【暗戀】【甜文】【雙潔】裴琛是京城有名的紈绔子弟,情場浪蕩子,突然一反常態的答應貴圈子弟最不屑的聯姻。結婚后,他每天晚出早歸,活脫脫被婚姻束縛了自由。貴圈子弟嘩然,阮鳶竟然是只母老虎。原本以為只是短暫的商業聯姻,阮鳶對裴琛三不管,不管他吃,不管他睡,不管他外面鶯鶯燕燕。后來某一天,裴琛喝醉了酒,將她堵在墻角,面紅耳赤怒道:我喜歡你十六年了,你是不是眼瞎看不見?阮鳶:……你是不是認錯人了?我是阮鳶。裴琛:我眼睛沒瞎,裴太太。
31.8萬字8.18 7404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