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夜書屋》 第45章 兇手!
黃昏時候的太,像是紅通通的蘋果,又像是小妹妹的臉蛋被烤了。
周澤坐在書店里,整理著最新的一批賬單,書店的運營已經步了拮據,關鍵問題還是在于自己從徐樂那里繼承的財產,實在是太了。
如果不是那次從盜版書商那里回了份額,很可能這店鋪已經沒辦法運轉下去了。
那晚從醫院回來,周澤就將剩下的冥鈔全都燒了,周澤還蹲在門口了半包煙等了好一會兒,的確,沒人過來丟錢了。
按照尸的說法,這波用德去擋災。
鬼給的冥鈔,相當于德,你需要錢時,可以拿來“換”錢,需要避難時,可以拿來抵消掉麻煩。
上次事兒有新聞報道了,一個富豪買兇雇人殺妻。
有一個小道消息稱嫌疑人說好像當時有一個高中生出現打了他們一頓,當然這個不會有人信的,
又不是戰士。
總之,那件事算是落幕了,周澤的冥鈔也沒白燒。
許清朗從隔壁過來,手里捧著兩杯茶,他的生活格調是越來越高了。
原本一個勤向上的有為青年,
在擁有了二十幾套房之后,
也終于開始貪圖步了墮落的節奏。
二人坐在柜臺邊一起喝茶。
“你那位媳婦兒,最后怎麼了?”許清朗問道。
“說要安靜一段時間,和思考一段時間。”周澤回答道。
坦白的過程很平穩,
甚至可以說順利得有些過頭了。
林醫生對自己的喜歡,甚至有一種向“病態”發展的趨勢,但好在,還是一個理智的人。
徐樂死了,他周澤借尸還魂,種種不可思議的事發生在的面前,你讓一下子全盤接,繼續和自己“夢中人”兼職“現任丈夫”過上沒沒臊的幸福生活,
Advertisement
有點難。
“已經不錯了,比我想象中堅強。”許清朗笑了笑,“普通人估計得嚇瘋了。”
周澤不置可否。
許清朗本不該知道這件事,很顯然是有人泄了,
泄者不需要去找就知道是誰,
那位白鶯鶯士。
“對了,問你件事兒。”周澤很認真地問道,“徐樂開店時,就這麼窘迫麼?”
“沒啊,我覺得他過得瀟灑的,不過他死之前我也沒怎麼和他打道,一個很木訥的家伙,賊沒趣。
但他錢應該多的,我記得那時候他經常在書店里接濟他的那些親戚,出手很大方。”
許清朗說完后又瞥了一眼周澤,甚至還出舌頭了,
“還是你有趣。”
一時間,腰肢搖,眼如波,當真讓人心神漾。
“你不去當鴨,真是可惜了,原本可以做一代鴨王的。”
“還能不能好好地聊天?”許清朗生氣道。
“這是贊。”
“呵……”許清朗手指了指周澤,“你還是關心關心你自己吧。”
“關心我什麼?”周澤手指了指這個書店,“最近生意不景氣啊,活人不到幾個就算了,就連鬼都不見幾個。”
“你和你那醫生老婆,準備怎麼發展?我是覺得,只是需要一段時間緩沖一下,然后還是會接的。
畢竟,那種人,說實話,你賺到了,天曉得在這個時代背景下居然還有這種類似古代大家閨秀的產生,父母肯定也是個奇葩。”
“嗯。”周澤點了點頭,自己那岳父岳母,確實很奇葩。
岳父當過醫院院長,自己也經營過一家醫療公司,按理說應該是絕對的功人士,但在某些方面,卻顯得很封建很頑固。
“這樣子的人,只要你馴服了,會心甘愿地給你相夫教子。”許清朗出了向往之,“我也想要這種人。”
“你已經是了。”周澤補刀。
“還是說說你的問題吧,你以后要和生活在一起的是吧?”
“應該吧。”周澤說道。
“那肯定也會睡一起的吧?”許清朗出手,抖了抖,繼續道:“我說的‘睡’,是一個包含著很多復雜作和特殊位的詞,你能懂吧?”
周澤點點頭,他依然不知道許清朗到底是什麼意思。
“嗯,那麼,你的問題來了,你現在用的是徐樂的,如果你們真的睡了,是不是也意味著徐樂把你給綠了?”
許清朗瞇了瞇眼睛,這一刻,他笑得很促狹。
然后,
周澤陷了沉思。
“甚至,你的DNA,也不是原本的你的,而是徐樂的,也就是說,你們在經過了‘睡’這個極其復雜富的詞過程之后,生出來的孩子。
其實也不是你的孩子,而是徐樂和林晚秋的孩子。
對吧?”
然后,
周澤再度陷了沉思。
許清朗越說越起勁,看著周澤繼續沉默,他心里簡直有一種說不出的暢快!
當初白夫人讓手底人抬著八抬大轎過來接自己時,
是周澤出指頭指向自己,
這個仇,他可是記在小本本上了!
周澤喝了一口水,不聲。
“是不是覺得很憂慮很彷徨?”許清朗問道。
“爽的是我自己。”周澤回答道。
許清朗皺了皺眉,繼續道:“但是這是徐樂的,你和睡時,是徐樂的。”
“爽的是我自己。”
“但孩子DNA……”
“爽的是我自己。”
許清朗雙手猛地一拍柜子,呵斥道:
“我咧,你不能想得這麼開啊!”
“反正爽的是我自己,徐樂那貨早就下地獄也不知道走到哪兒去了,可能都喝了孟婆湯投胎去了,我在意這個做什麼?
我爽了就是了。”
許清朗氣得口一陣起伏,他也不知道自己為什麼生氣,
但就是好氣哦!
“好了,不扯了,再扯下去就要變神和上的辯論問題了,都快到哲學的高度了。”周澤示意結束這個有點無聊的討論。
“你高興就好。”許清朗怨氣滿滿。
“對了,有件事需要問你一下。”周澤想到了另外一件事。
“說。”
“你還認識其他鬼差麼?”周澤問道。
“我之前帶著爹媽的亡魂過日子,還敢去認識鬼差?”許清朗反問道。
“好了,我知道了。”
看來還是得時間去文廟那邊看看了,上次看見那個敲鑼的侏儒老者,應該也是有編制的。
“你到底想問什麼?”許清朗問道。
“我想問問鬼差有沒有什麼業績表這類的,升職加薪福利的這種。”
“應該……有的吧。”許清朗沉思了一會兒,道:“你看像白夫人,都能通過積攢功德,從一個逗留人間的鬼回到地獄去謀求一個,你應該也是有的。
那個小蘿莉沒跟你說?”
周澤搖搖頭。
“我也是覺得你這鬼差來得有點太簡單了,我估著,可能是有什麼其他嚴重的事兒需要去理,所以暫時把這差事丟給你應付一下。”
“你的意思是,我這是真的臨時工?”
“呵呵,等人家事理完了,估計你就得騰窩了,到時候人家心好,就對你睜一只眼閉一只眼,如果心不好,直接把你抓回地獄也是有可能的。”
“到底是要去理什麼事?”周澤自言自語道。
接著,周澤腦海中浮現出老道直播時那個畫面中的喝粥青年,
蓉城,
冥店?
再聯想一下小蘿莉在聽到自己提起蓉城時的反應,
好像,
還真是有可能。
但不管如何,自己這個臨時工的份,不能輕易地再還回去,當黑戶的日子,可不舒服。
許清朗回自己店里去了,臨走時給周澤說了聲“元宵節快樂”。
周澤也在收拾東西,同時吩咐白鶯鶯出去給自己買幾條煙和一些圓子回來,他得更改計劃,今晚就去文廟找那個侏儒老者聊聊天。
也就在這會兒,書店門被推開,走進來一個穿著白羽絨服的男子。
“阿樂哥!我來接我爸出院的。”
周澤愣了一下,腦子里開始思索,大概猜出了男子的份,應該是自己大伯的孩子,年紀比自己小一些,和徐樂應該是堂兄弟。
徐大川上次來城里看自己,離開時出了車禍輕微骨折,周澤后來去看過一次,醫療費什麼的林醫生都墊付了,他也就沒再過多關心。
“你好。”周澤回應得有些冷淡。
“阿樂哥,最近手頭缺點錢花花,你看我爸這一摔,起碼回家后還得靜養倆月的,也不能出去打工賺錢了。”
堂弟對著周澤笑了笑。
“給過大伯營養費了。”周澤給過一些,徐大川不肯收,還是周澤塞進他服里的。
“嘿,阿樂哥,我最近又談了個朋友,手頭有點兒,哥,接濟一下弟弟唄。”堂弟這是直接開口要了。
“我這兒,生意也不好。”周澤沒打算給。
“哥,你這就不夠意思了。”堂弟不開心了,道:“上次的事兒還是我找人幫你弄的呢。”
“啥事兒?”
“哥,不厚道了啊,辦完事兒就不認了?我跟你說,我這不是厚著臉皮跟你要錢,你看我這大半年,有上門來跟你提錢的事兒嘛。
上次的事兒,那個司機保證不會說,再說他已經關了大半年了,再關個半年多也就出來了,他腦子蠢才會說破是吧,他口肯定也嚴,不然就從違法駕駛變故意殺人了。
弟弟我這次真的是手頭,哥,你就接濟我千兩千的,等我有錢了再還你不?”
周澤拿起柜臺上的茶杯,聽到這里,忽然微微皺眉,道:
“到底什麼事兒,我聽不明白。”
“哥,你這就打算過河拆橋了啊?
半年前可是你讓我幫你聯系一個卡車司機花錢讓他故意撞死那個醫生的,
你可不能忘了我的功勞啊……”
“咔嚓……”
周澤手中的玻璃杯,
直接被碎了。
猜你喜歡
-
完結514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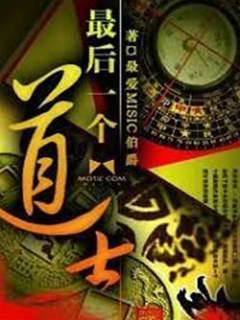
最後一個道士
查文斌——中國茅山派最後一位茅山祖印持有者,他是中國最神秘的民間道士。他救人於陰陽之間,卻引火燒身;他帶你瞭解道術中最不為人知的秘密,揭開陰間生死簿密碼;他的經曆傳奇而真實,幾十年來從未被關注的熱度。 九年前,在浙江西洪村的一位嬰兒的滿月之宴上,一個道士放下預言:“此娃雖是美人胚子,卻命中多劫數。” 眾人將道士趕出大門,不以為意。 九年後,女娃滴水不進,生命危殆,眾人纔想起九年前的道士……離奇故事正式揭曉。 凡人究竟能否改變上天註定的命運,失落的村莊究竟暗藏了多麼恐怖的故事?上百年未曾找到的答案,一切都將在《最後一個道士》揭曉!!!
129.6萬字8 14545 -
完結974 章

規則怪談:全球直播求生
規則怪談降臨,精神分裂的敖武被選中進行直播求生,成功破解規則怪談,可以獲得規則怪談世界的道具、壽命和稱號,失敗則死無葬身之地。落日酒店怪談:暗藏殺機的送餐服務,被鬼替換的住客,通過鏡子入侵客房的詭異,這里處處殺機,生路何在?……圣天使醫院怪談:警報聲所潛藏的秘密,失去記憶的惡鬼病友,醫院走廊游蕩著看不見的“它”……這里陰險詭譎,敖武是否能夠逃出生天?死亡游戲怪談:詭異的眼睛雕紋,七個恐怖的關卡,與鬼游戲,對賭搏命,誰勝誰負……不光如此,規則怪談中帶出超前科技引來的追殺,六年前,敖武所在孤兒院失...
178.8萬字8.18 13886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