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酷丫頭的貼身霸道總裁》 第76章 開學了
我趕拿穩筆記本,手。
心裏掠過一影。
我的本子就在手上,還來拉,是三角眼無視還是故意?故意又是想做什麽?戒備的看著,搖頭,不想理。
自從殷亦桀的事後,經他那一番提醒,還有冉樺提到苗苗寒假約我逛街,我對什麽都更加敏。就連以前毫不在意的事,也能留心起來。比如剛才發現舒服的異樣。這個世界太難以捉,所以我們需要多個心眼,時刻提防。
提防和簡單的懷疑不盡相同,但也有些相似。我戒備的看著苗苗,希能和我保持一個安全的距離,否則我不能保證不自衛。兜裏的刀子一直都在,惹了我會發飆的,相信我。
“走走,出去走走,請你吃甜不辣。寒假給你打電話,沒人接,躲得真牢。聽說你生病了,本來還想去看你的,又怕你家門檻高,進不去。”苗苗對我的戒備視無睹,拉著我胳膊,覺想念我很久了。臉上的笑容很明,仿佛借來春二三鬥,看著很舒服,很刺眼。
我搖頭,趕把本子收好,調整狀態,至三級戒備。
對於的如此熱,我非常困。說實在的,我沒有一點兒好,相反,覺得擔心。
和苗苗這種人往,以前還罷了,但自廖亮的事之後,我就知道,沒那麽簡單,卻也著實太簡單。
的心思,其實表的很白,稍微一用心就能看出來。
或者也不能怪簡單,可能是我對這類的見多了,所以,駕輕就,我心裏有譜。
和殷亦桀比,要看懂想做什麽......嗬,我忽然覺得好笑,真想謝殷亦桀給我的教育,全麵,實用。
“走吧,這會兒又沒事,小花園裏迎春開的可好了,咱們去照個相,回頭放到博客裏,點擊一定高。”苗苗搜腸刮肚,極力要把我連遊說帶綁架的弄走。
Advertisement
“我還要開班會。”我冰冷的瞅著,心裏有些無奈,當著這麽多同學,我還不能太過,否則,對我更不利。
人之,是個很可笑的東西,有時候。
魯迅說:世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便了路。
經典名言。存在即真理。現在換個說法,其實也是真理。那就是:世人本來都很無,裝的人多了,也就了人。世上本無此事,說的人多了,便了真事......
“班會有什麽要,聽不聽都那樣,個班費,發個書,不就完了?”苗苗嘟起菱,不以為然,手下用力,準備拖我。的眼裏,有種堅決,出賣了的熱。
我在想辦法,如何擺,又能稍微顯得不那麽不近人。
我甚至無法悍然推開苗苗,然後大吼一聲。就算我有一百二十個理,隻要我強悍,那就錯了。可磨纏我很不耐煩,還不像殷亦桀,會很客氣很禮貌的和我比耐心;而是直接上手,像街頭賣白菜的潑婦,讓秀才很難對付。
這會兒想想,我的監護人確實夠難得。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想法和堅持,要客氣的讓步和容忍對方,有時候很難。但他昨天就表現的很不錯,今天......就太勉強了。不過我是不是也太強了,一點兒沒考慮他的?那也不行呢,我還小,要我像主持那樣哄他,耶,我吐!
扭頭四顧,我想看看有沒有柱子,可以一頭死;或者有沒有地,讓我鑽進去,從此離遠遠的。其實我也不是不可以揍,但總覺得這樣會讓人愈發坐實對我的猜測,進而影響我本來就不大好的形象並破壞殷亦桀的教育之功勞。
看,我多偉大,都被如此糾纏了還為他著想,死家夥,竟然還在家生我氣,鄙視!
眼角餘看到,冉樺正在一旁有意無意的和趙昀嚼舌,趙昀有些不樂意。
我沒理,繼續想折,一邊應付:“你有什麽事兒嗎?我走了,誰替我班費?”
“請你吃東西,不是事兒嗎?”苗苗愈發抓住我胳膊,準備生拉拽。
“一會兒還要選班幹部。去年大家不認識,選的班幹部有人不滿意,要改選。”趙昀蹭到我們跟前,臉不是太好看,話也說得很生。
呃......嗬......有意思。大人玩深奧的遊戲;我們玩淺顯的把戲。就是不知道,為什麽又牽扯上我。如果我姓香,一定會當自己是餑餑;如果我姓唐,一定會當自己是僧。
挑挑眉,看著苗苗,等著退場。對於趙昀,我現在還不知道該怎麽謝。不過他能開口,我還是非常激的。至讓我不太難看,就算一會兒吵翻了,也不太失人心。
嗬,人心......人心正在四周的角落裏嘀嘀咕咕各自寒假的趣事,一邊兒用眼角切關注我這邊的事況。我突然覺得,人一旦得到了些什麽,或者過的幸福了,就會有忌諱的東西,比如這無厘頭的從來沒對我好過的人心。真要被這虛無的東西束縛手腳,我還活不活了?
想到這裏,我臉冰冷,用力而堅決的推開苗苗,和人心。
“妝可人不會想當班幹部吧?一票有什麽要?”苗苗不樂意的看著趙昀,反駁,一邊手拉我。看著我數九寒冬臉,鼻孔微微嗤笑一下,又趕掩飾。
我白了一眼。我的一票也是一票,你說不要就不要了?誰要你替我做主?
“我想。我需要的一票。”趙昀紅了臉,麵紅耳赤。顯然是初次說謊經驗不足,連口齒都不大伶俐。說完看著我,問,“你會投我一票嗎?”
呃......太狗了!
我暈死,趙昀的演技太差了!要不是在幫我,估計我會笑場。看看他認真的表,我覺得,這一票,在他和苗苗中間,我顯然應該投他。這也太明顯了。
唯一讓我到疑的,就是冉樺為什麽不出麵,是他覺得和我關係不足以與苗苗抗衡嗎?
還是有別的緣故?
又或者,像上次一樣,他勸我,別和苗苗出去?
也許,我似乎該接他的好意,想方設法別跟苗苗出去。
還是在好奇心的驅使下,和苗苗出去一回,看看到底有什麽危險,或者究竟是誰在故弄玄虛?
我現在大概能猜到苗苗應給無好意,但不能確認冉樺究竟何意。
嗬,我很能相信誰,因為沒有誰會無緣無故的幫別人,甚至不惜冒犯其他人。
見到殷亦桀和布萊恩之後,我更覺得有些人指不定就有極複雜的背景,很多事都不能輕信。
但不論如何,現在,我更不相信苗苗,所以,決定不出去。
對趙昀點點頭:“我選你。”
趙昀本來就紅的臉,現在整個是......興的兩眼發亮,差點兒跳起來,剛才的鬱沒了。
“妝可人......”苗苗似乎看到失,非常不願意、不忍心。
“我們要開班會了,你不介意旁聽吧?”我冷冷的看著。
我們班的同學,剛小斑了一下,很快冷靜下來,頭接耳、竊竊私語。
苗苗非常不甘心,左顧右盼,眼裏狠毒一掃而過,非常好心的看著我,低聲音勸我、剛好讓大家都能聽見:“你已經有了殷總,怎麽還可以和別人好?這樣對你和別人都很危險的。他們那種人,最不喜歡自己的人在外麵勾三搭四,一旦鬧起來,你怎麽辦?”
“啪......”我很利落的甩了一掌,冷冷的盯著,一個字兒都沒有。
所有人都看著我,我收到他們探究和嘲弄的目,不想理。
苗苗也愣了,過了好一會兒,嗚嗚咽咽的哭出來,泣道:“你這種孩,從小沒個人教你,將來長大了一定會吃大虧的。我好心和你說,你竟然......算我白費心了......”
我很想再甩一掌,因為果然如我所料,在煽,然後讓所有人都以為,我惱怒、做賊心虛。但我不能,因為再打,我真的會辜負所有對我好的人,玷汙他們的名節,讓人以為我真的很沒教養。所以,我隻能吃下這個啞虧,冷冷的看著:真讓我失!
不過我腦子還沒那麽暈,我很好奇:為什麽這麽對我?我們曾經的友誼,竟然一文不值?
苗苗說完話,發現我沒有毫悔改的意思,反而眼冷得能凍死人,隻好嗚嗚咽咽走了。
我不覺得那一掌有多痛,如果說痛,也許我心裏比還痛。但哭的那麽哀傷做什麽?上次和流氓打架,也沒怎麽喊痛,所以,的用心......
我搖頭,無語。
“妝可人,你......”冉樺站在我前,眼神鬱,不複剛才的熱。
我繼續搖頭,無語。
“別理。我一會兒告訴你。”冉樺非常輕微的說了一句,就到講臺前,那裏正在發書。
暫新的課本,散發著濃鬱的墨香,有種含蓄的優雅。
這世上,能到的氣質已經不多了,能品讀的底蘊更。到都是虛無的浮華,帶著低劣的奢靡,也許不用多久,就能侵占整個世界。因為課本裏,錯別字也漸漸多起來,各種各樣的疏,在手可及的地方。甚至還有個堂而皇的名字,“時代”。
不知道,我們的時代,到底想讓我們到些什麽?還是我未老先衰,在我父親和母親的畸形教育中,以及我的喋喋不休中,過早的離了時代?
當然相對說來,我還是比較喜歡課本,尤其是嶄新的課本。相對於同學、相對於環境、相對於別的地方幾乎滅絕的文化來說,我,選擇課本。這也是我整個寒假都在家看書的原因之一。
捧著厚厚的一摞書,回到自己坐位,慢慢的挲,借這種,平息心頭的點點煩躁和不安。
猜你喜歡
-
完結3579 章

韓先生情謀已久
“收留我,讓我做什麼都行!”前世她被繼妹和渣男陷害入獄,出獄後留給她的隻剩親生母親的墓碑。看著渣男賤女和親爹後媽一家團圓,她一把大火與渣男和繼妹同歸於盡。再醒來,重新回到被陷害的那天,她果斷跳窗爬到隔壁,抱緊隔壁男人的大長腿。卻沒想到,大長腿的主人竟是上一世那讓她遙不可及的絕色男神。這一次,她一定擦亮眼睛,讓 韓先生情謀已久,恍若晨曦,
354.7萬字8 57206 -
完結70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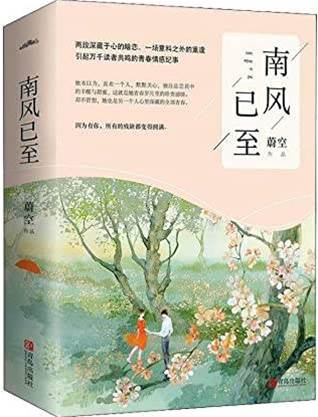
南風已至
——我終于變成了你喜歡的樣子,因為那也是我喜歡的樣子。 在暗戀多年的男神婚禮上,單身狗宋南風遇到當年計院頭牌——曾經的某學渣兼人渣,如今已成為斯坦福博士畢業的某領域專家。 宋南風私以為頭牌都能搖身一變成為青年科學家,她卻這麼多年連段暗戀都放不下,實在天理難容,遂決定放下男神,抬頭挺胸向前看。 于是,某頭牌默默站在了她前面。
22.2萬字8 6582 -
完結491 章

裴教授,你行不行啊
絕世小甜文,年齡差,先婚后愛,1v1雙潔,斯文敗類教授X古靈精怪富家女。劇情一:葉允澄可憐巴巴的看著裴修言:“老公,我作業沒寫完,你跟我們導員熟,你跟她說一聲讓她別檢查作業了好不好。”裴修言抿唇不說話。結果第二天,導員只檢查了葉允澄一個人的作業...下班回家的裴修言發現家空了一大半,葉允澄不見了...
97萬字8 44785 -
完結183 章

乖吝
【甜寵&雙暗戀&校園到婚紗&雙潔&救贖】(低調清冷富家大小姐&痞壞不羈深情男)高三那年,轉學至魔都的溫歲晚喜歡上了同桌校霸沈熾。所有人都說沈熾是個混不吝,打架斗毆混跡市井,只有溫歲晚知道,那個渾身是刺的少年骨子里有多溫柔。他們約好上同一所大學,在高考那天她卻食言了。再次相見,他是帝都美術學院的天才畫手,是接她入學的大二學長。所有人都說學生會副會長沈熾為人冷漠,高不可攀。卻在某天看到那個矜貴如神袛的天才少年將一個精致瓷娃娃抵在墻角,紅著眼眶輕哄:“晚晚乖,跟哥哥在一起,命都給你~”【你往前走,我在身后...
32.4萬字8 9635 -
完結872 章

誘捕玫瑰
五年前,溫棉被人戳着脊樑骨,背上爬養兄牀的罵名。 所有人都說她是個白眼狼,不懂得感激裴家賜她新生,反而恩將仇報。 只有她自己知道,這所謂的恩賜,只是一場深不見底的人間煉獄。 五年的磋磨,溫棉險些死在國外。 重新回來時,她煥然一新,發誓要讓裴家的所有人付出代價。 本以爲這是一場孤注一擲的死局。 卻沒想到,這個將她送到國外的養兄,卻跟個甩不掉的牛皮糖一樣跟在身後。 她殺人,他遞刀,她報仇,他滅口。 終於,溫棉忍不住了—— “你到底要幹什麼?” 而那隱忍多年的男人終於露出了尾巴:“看不出來嗎?我都是爲了你。”
84.4萬字8 2103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