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陵夜》 077章 大喪
077章 大喪
看見周玉芹,一屋子里的渝軍將領俱是站起子,先是與周玉芹行了一禮,繼而便是向著梁建告退。
梁建也沒挽留,沖著眾人揮了揮手,渝軍將領們俱是退出了屋子,會議室里便只剩下梁建與周玉芹二人。
“你怎麼來了?”看見,梁建面上倒也沒什麼驚訝之,只沉聲問道。
“玉芹惦記著司令,所以就來了。”周玉芹微微揚,麗頓生。
梁建也是笑,“你怕是得了消息,知道江北軍會向著川渝進攻,所以才跑來了紹州,是不是?”
周玉芹也不否認,只道;“司令若不想見我,那玉芹回去就是。”
“來都來了,還回去做什麼?”梁建站起子,向著周玉芹走去。
周玉芹則是向著梁建微微俯了俯子,言了句;“玉芹還沒有恭喜司令,金陵如今已是唾手可得,司令的大仇即將得報,玉芹也為司令高興。”
“嗯,”梁建聲音低沉,他角噙著淡淡的笑意,說了句;“我等了這麼多年,為的便是這一日。”
周玉芹亦是微笑,了,吐出了一句;“不知司令攻下金陵後,打算如何置傅家的人?”
梁建眸心微,他沒有出聲,只向著看去。
“怎麼,司令難不是要放了他們?”周玉芹問。
“放了他們?”梁建重復著這幾個字,似是聽了天大的笑話般,“玉芹,你明知我對傅家的人恨之骨,我又怎麼可能會放了他們?”
“玉芹是擔心,司令若對傅家的人趕盡殺絕,只怕司令心里的那個人,會記恨司令。”周玉芹聲音極其平靜,每一個字都十分清晰。
的話音剛落,梁建角的笑意便是去了,他的眼楮如鷹隼般銳利,只盯著周玉芹吐出了幾個字;“夠了!我說過,不要提!”
Advertisement
周玉芹微微一笑,眸心漾著不為人知的苦。
梁建神戾,他轉過子,走到了窗前,隔了良久,梁建閉了閉眼楮,剛開口讓周玉芹出去,就聽屋外傳來侍從的聲音;“司令,金陵派了人過來,想見司令一面。”
“看樣子,是傅鎮濤派了人來祈和,司令不打算見見?”周玉芹聞言,遂在一旁勸說。
“見什麼見?”梁建燃起一支煙,對著屋外吩咐;“把他們拖出去斃了,尸首給傅鎮濤送回去”
“是,司令。”侍從領命退下。
縱使周玉芹跟隨梁建多年,心知他的手段狠,可此時見著他連來使也不放過,不免嘆了口氣。
“你嘆什麼氣?”梁建敏銳的捕捉到了那一抹嘆息。
周玉芹搖了搖頭,“這一路玉芹也是累了,玉芹就先下去休息了。”說完,周玉芹再不曾和梁建說什麼,只對著他行了一禮,禮畢便是離開了會議室。
留下梁建一人,過窗戶,遙遙的向著金陵城的方向看去。
金陵,司令府。
“怎麼樣?梁建說什麼沒有?”看到來人,傅鎮濤立時從椅子上站起子,豈料起來的快了些,頓時一陣猛咳。
這陣子傅鎮濤的子每況愈下,渝軍兵臨城外,求援的電報雪片般的拍往了江北,謝承東卻並未增兵,傅鎮濤每日里猶如熱鍋上的螞蟻,心滿是煎熬。
“司令,梁建把咱們派去的人全給殺了,眼下尸首就在外面。屬下生怕驚著司令,也沒敢讓人抬進邸。”傅鎮濤的屬下聲音恭謹,與傅鎮濤開口。
傅鎮濤心中一寒,渾近乎癱般的坐在了椅子上。
“司令,川渝那邊傳來的消息,是說江北軍已是向著川渝發起了進攻,按理說川渝危急,梁建應當立刻班師,趕回川渝才對,可看他那樣子,倒似乎將川渝拱手相讓,也一定要打下金陵不可。”
傅鎮濤聞言,臉更是灰白,他坐在那里,就連聲音也是有氣無力,著深深的疑,“江南地小兵弱,他何必放著川渝不要,拼死也要來和我作對?”
那屬下沉默片刻,道;“司令恕我多,我總覺得,這梁建的所作所為,倒不像是想要江南,看起來,倒是像跟司令尋仇一樣。”
傅鎮濤點了點頭,“你說的我又何嘗沒有想過,可這梁建狠狡詐,不論我使出什麼法子,也沒法清他的底細,我的仇家雖多,可大多當年都被我斬草除,我倒真不知道哪里出了紕,讓他逃了出去。”
“司令,江北的援兵遠不夠抵擋梁建,倘若渝軍向著金陵發起總攻,屬下只怕咱們的兵力抵擋不住,等梁建攻進了城,到時候可就不堪設想了。”
“想當年我將兩個兒一個送到江北,另一個送到川渝,我籌謀半生,沒想,還是落到今天這個地步。”傅鎮濤聲音沙啞,帶著深深的惆悵。“那梁建害死了良波和良渺,還有老四和老五,我們傅家和他結下了海深仇,他這主找上門了,哪怕江南只剩下一個金陵,我也該和他拼個你死我活,我一個人倒是罷了,可這一大家老的老,小的小……”
傅鎮濤說不下去了。
“司令,屬下聽聞,謝承東極為看重二小姐,更不用說當年二小姐還曾是梁建的七夫人,先前梁建勾結阮朝,也曾說過只要咱們將二小姐還給他,他就會從江南退兵,屬下倒是想,咱們不妨想個法子,讓二小姐回來,若能用二小姐勸得梁建退兵自然是好,他若不肯退兵,咱們也可用二小姐要挾謝承東,讓他派兵增援。”
傅鎮濤心頭一凜,半晌沒有出聲,似是在思索屬下的話是否可行,良久,他終是嘆道;“沒用,謝承東本不會讓良沁回來。”
“若有大喪,于于理,謝承東都沒法阻攔二小姐。”
“大喪?”傅鎮濤咀嚼著這兩個字,瞬間明白了過來,他眼眸一亮,與屬下沉聲道;“你是說,將六姨太……”
“為今之計,倒也只有如此了,倘若二小姐生母去世,無論如何,二小姐都會從江北趕回來,謝承東沒有理由阻止。”
“你說的不錯。”傅鎮濤緩緩點頭,對著屋外喚出了兩個字;“來人。”
“司令有何吩咐?”立時有侍從走了進來。
“去,請六夫人過來。”傅鎮濤吩咐。
傾,就見那侍從腳步匆匆,從院子里奔進了書房,與傅鎮濤開口就是一句;“司令!六夫人不見了!”
“你說什麼?”傅鎮濤大驚失。
江北,司令府。
謝承東回來時,良沁還沒有歇息。
看見他,良沁頓時從沙發上站起子,向著他迎了過去。
“這麼晚還不睡?”謝承東將抱個滿懷,見眼眸中滿是驚慌,遂是皺起眉頭;“怎麼了?”
“瑞卿,梁建已經攻下了紹州,他就快要打到金陵了,是不是?”良沁開口便是這麼一句。
“是,他的確已經打下了紹州。”謝承東點頭。
“那,若是他真攻下了金陵,他不會放過傅家的人的……”良沁攥了謝承東的角,的手指時抖的,聲音更是的不樣子;“我娘還在金陵……”
“你別怕,”謝承東不忍見如此,只攬著的床沿上坐下,握住了的手,“我答應過你,不會讓梁建欺凌傅家,江北軍的銳如今已是埋伏在渝軍後,只等渝軍作,江北軍就會殺他個措手不及。”
“真的?”良沁心砰砰直跳,“外面不是說,你把軍隊派去了川渝嗎?”
“聲東擊西,懂嗎?”謝承東微微一笑,了良沁的臉頰。
良沁見他不似欺瞞自己的樣子,方才微微松了口氣,可仍是有些不大放心,剛開口,就見謝承東在的邊豎起了食指,他的黑眸炯炯,看向自己的眼楮;“若我沒派去銳,你當良瀾還能坐得住?”
良沁微震,這才想起如今快到年關了,傅良瀾每日里只忙著邸里的事,的確不曾見掛心娘家的形,想來,對此事早已知曉。
良沁高高懸著的心到了此時才算是落進了肚子,垂下眼眸,小聲道;“我是真怕,你會對江南不管不顧了。”
“傻話。”謝承東低聲一笑,將帶到自己懷里,良沁著他的面容,心知眼前的男人手中掌握著自己一家老小的生死,微微支起子,摟住了他的頸脖,將自己的子倚在他的膛。
謝承東著白淨純的側,忍不住心中一,他俯吻住了的瓣,良沁的瓣清甜而,只讓他不斷的沉溺下去,控制不住的越吻越深。
輾轉間,正是芙蓉帳暖,春宵苦短。
“司令,”侍從走進廳,對著梁建“啪”的一個立正。
“順利嗎?”梁建回過頭,低聲問道。
“司令放心,老夫人已經被安置在了外城,有咱們的人守著,如今金陵戒備森嚴,咱們的人實在沒法子將老夫人送出來,還請司令恕罪。”
“不,你們做的很好,”梁建淡淡笑起,“能神不知鬼不覺的將一個大活人從傅家帶出來,不錯。”
“多謝司令夸獎,”侍從恭聲開口,傾,卻又是問了句;“司令,屬下有一事不解,您這樣這般大費周章的,為何要把傅鎮濤的這個姨太太從傅家接出來?”
猜你喜歡
-
完結918 章

團寵:七個哥哥又爆我馬甲
【甜爽+係統+團寵+女強+馬甲+輕鬆搞笑】蘇洛被師父踢下山繼承鉅額遺產,但冇想到除遺產外還有七個大佬哥哥!大哥商界精英;二哥醫學天才;三哥著名影帝;四哥科技大佬;五哥第一殺手;六哥梗王黑客;七哥混混校草;哥哥們:最小的妹妹就是用來寵的。蘇洛:不,我想飛。哥哥們:你不想!直到有一天—臥槽,洛洛跟五哥打平手!洛洛也是黑客!洛洛竟然…神秘大佬:我有外掛,隻有我配得上洛洛…什麼?!洛洛也有!團寵:七個哥哥又爆我馬甲
86.4萬字8.18 56939 -
完結493 章
惡魔的寵愛
“以你的身材和技術,我認為隻值五毛錢,不過我沒零錢,不用找。”將一枚一塊的硬幣拍在床頭櫃上,喬錦挑釁地看著夜千塵。“好,很好!女人,很好!”夜千塵冷著臉,他夜千塵的第一次,竟然隻值五毛錢!再次見麵,他是高高在上的王,她是低到塵埃的花。一份價值兩億的契約,將她困在他身旁……
84.9萬字8 14858 -
完結262 章

只要月光就夠了
原來偶像劇也不全是假的 池柚沒想到,畢業后居然會和曾經暗戀過的男神在同一家公司 只可惜生活終究不是偶像劇,再深刻的暗戀也遲早會被時間治好,她沒能和男神發展出什麼,直到離職前在某次部門聚餐時聽到他和別人的對話。 岑理和關系好的同事游戲
38.9萬字8 7437 -
連載612 章

傅總別虐了,夫人已經簽了離婚書
結婚三年,溫涼沒有焐熱傅錚的心。白月光回歸,她得到的只有一紙離婚書。“如果,我有了我們的孩子,你還會選擇離婚嗎?”她想最后爭取一次。當時卻只得來一個冰冷的回答,“會!”溫涼閉上眼睛,選擇放手。……后來,她心死如灰的躺在病床上,簽下了離婚協議。“傅錚,我們兩不相欠了……”向來殺伐果決的活閻王卻伏在床邊,低聲下氣地挽留,“阿涼,不要離婚好不好?”
109.8萬字8.18 34164 -
完結172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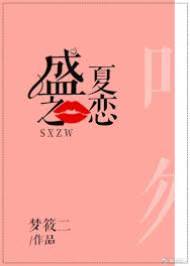
盛夏之戀
那天,任彥東生日派對。 包間外走廊上,發小勸任彥東:“及時回頭吧,別再傷害盛夏,就因為她名字有個夏沐的夏,你就跟她在一起了?” 任彥東覷他一眼,嫌他聒噪,便說了句:“煙都堵不住你嘴。” 發小無意間側臉,懵了。 盛夏手里拿著項目合同,來找任彥東。 任彥東轉身,就跟盛夏的目光對上。 盛夏緩了緩,走過去,依舊保持著驕傲的微笑,不過稱呼改成,“任總,就看在您把我當夏沐替身的份上,您就爽快點,把合同簽給我。” 任彥東望著她的眼,“沒把你當替身,還怎麼簽給你?” 他把杯中紅酒一飲而盡,抬步離開。 后來,盛夏說:我信你沒把我當替身,只當女朋友,簽給我吧。 任彥東看都沒看她,根本就不接茬。 再后來,為了這份原本板上釘釘的合同,盛夏把團隊里的人都得罪了,任彥東還是沒松口。 再再后來,盛夏問他:在分手和簽合同之間,你選哪個? 任彥東:前者。 那份合同,最終任彥東也沒有簽給盛夏,后來和結婚證一起,一直放在保險柜。 那年,盛夏,不是誰的替身,只是他的她。
25.4萬字8.18 7596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