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將就》 第26章 良人知己
【你隨意】
作為宋許的新晉至——當然這是他自封的——齊停指的自然是錯誤的方向,指完他便哼著曲回到包廂,繼續和人為了那幾個點的利潤對拼。
宋許順著小道急步走著,眼見到門口,剛踏出一步,眼前就斜來一只黑袖子,人高馬大的司機憨厚一笑:“宋先生。”
說著,拿出手機對著那邊道:“是,在北門。”
不用猜,宋許都知道電話另一頭是誰。
李宏見他臉不善,也知道這事干的不太地道,收起電話,陪著笑,合手做了一個告饒的作,他也只是個收錢辦事的,還希宋許別太怪罪。
宋許不是不知道這是什麼意思,他現在要走,嚴與非不了拿這些人開刀。可又和他有什麼關系?
可剛一提,那道黑影就立在前,宋許往左他也往左,宋許往右他也往右。
宋許挑眉看著眼前人,那人不好意思般低下頭,確是一不,就那麼橫在路中間。
巷子不算窄,但被人刻意擋著,一時間除了一番手腳,也不太容易出去,可他只是不想看見嚴與非,倒還不至于落跑。
宋許額頭,把抬了一半的腳,又落回原地,笑了起來:“李宏,你母親還好?”
提起這一句,是因為宋許忽然想起,嚴與非這個司機,也同他有些關系。
那時李宏剛來給嚴與非開車,他母親重病,沒有積蓄看診,而嚴與非那陣正為剛接手公司頭疼,又哪里有閑錢幫一個隨時可以替換的司機,可宋許看著嚴與非的面子,從私庫里開了一筆,利息也不要,慈善一般投了進去。
自那以后李宏就對嚴與非的事是一萬個上心。心盡到了,嚴與非自然覺得他好用,就把他留到了現在。
Advertisement
宋許本不是那種攜恩求報的人,可有人要恩將仇報,他也不會白著。
李宏一聽這話,張了張,想說點什麼,最后又什麼都沒說。
宋許對他的恩,他一直都記得,可嚴與非是他老板……
正思索的空檔,李宏胳膊被人拎著一甩,他一時不備,又怕還手傷著人,只好被挨了一下,撞在墻上。
宋許看他表,就猜到七八分,料到這人打定主意要堵自己,心上涌現的不僅是煩,還有別的,做個比喻,那差不多就是被喂過的流浪狗反咬一口的惡心。
宋許把李宏扯開,從他面前大步躍了過去,李宏手一撐地,立馬站了起來,灰也顧不得,想追上去,卻被宋許落下來的一句話釘在了原地。
真是一對白眼狼……
宋許其實只是自言自語的喟嘆,可沒想到李宏聽見這話,兩條像是被被水泥砌在墻里,怎麼也邁不開了。
宋先生確實對他不薄,哎。
懷著這樣的心思,那奉命的,怎麼也落不出去了。
因為有些愧疚,等嚴與非黑著臉的追來時,李宏還試圖擋了一下,想勸勸他。
“老板……”
沒說完,腰上就挨了一腳。
“廢……”
嚴與非見他沒留住人,面鐵青,踹了他一腳后看都沒看,轉向巷口走去。
宋許坐在車里正點火,可發機轟隆兩聲,又一撲通兩下一停,沒了聲息,就在宋許要試第三次的時候,車窗被人敲了兩下。
宋許抬頭,嚴與非雙手抱杵在門口,面無表。
宋許很快收回目,琢磨這開了沒幾年的車到底哪出了問題。
直到嚴與非把玻璃拍的框框作響,連周圍的居民都探出頭來看,他才搖下車窗。
“下車……”
嚴與非不耐煩道,他剛和呂肖樊了手,臉上被傷,又被宋許一路躲著,心差到了極點,懶得多說一個字。
宋許婉拒:“不了……”
嚴與非一下子失了耐心,從半開的窗戶打開車門,把人拽了出來。
宋許力氣沒他大,掰了兩下沒擺開,也了氣:“嚴與非!”
嚴與非沒有回頭,手里的力度倒是不減:“你那車有問題。”
雖然是我人的手腳,但后半句嚴與非只在心里默默補上。
“我看是你有問題!”
宋許被拽的也了火。
出了巷,就是做生意的道,行人來來往往,不被他們這吵架一般的作吸引了目,已經有好事的正在掏手機。
嚴與非不要臉,宋許要,真鬧到網絡上,嚴家背后的勢力肯定把他的信息護的死死的,而看不慣自己的人那麼多,肯定會被人添油加醋說上一筆。
看到投來的目愈加多了起來,宋許咬了咬牙,決定不再掙扎,跟著嚴與非上了車。
車上有宋許親自挑的香,安神平氣,宋許聞了幾口,心中的燥意稍稍減緩,把剛才在人前攢著沒罵出來的話,咽到了肚子里,用狗咬我我不必咬回去這句老話,勸了勸自己,而后閉上了眼睛。
“去哪……”
宋許問。
“回家……”說到這兩字時,嚴與非的神也放緩些許。
宋許被他話里話外的眷膈應的睜開了眼睛,他著邊人,嘆了一口氣:“嚴與非,你今天我來,到底是什麼意思。”
那些假意的愧疚與歉意,除了讓他更添心理不適,沒有任何意義。
嚴與非看著窗外,沉默片刻:“讓呂肖樊給你道歉。”
宋許笑了:“原來那是道歉嗎?”
那可真是見識了,這人睜眼說瞎話的能力。
沒想到嚴與非看他一眼,皺起眉:“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你不知道?”
宋許眼睛大睜,像是看見了什麼匪夷所思的事似的,連著重復了兩句。
這人怎麼裝無辜還裝上了癮?
雖然他知道一和嚴與非說話自己肯定會被他氣著,可宋許還是被這話激的忍不住開口,他先了鼻梁,讓自己盡可能心平氣和。
“好,我問你,我沒跟你說過呂肖樊用他叔的關系扣我手底下的貨?
我沒跟你說過嚴文仗著你媽越過我調人事?我沒跟你說過封俞跟他那倆兄弟一個里出氣跟著風給我添堵?恩?嚴與非?”
明明想著氣,可說到最后,還是忍不住直了背,手也忍不住用力握。
嚴與非回頭看他,又垂下眼,了,可最后一字都沒有說。
“嚴與非,說話!”
這一聲從間出,聲音是宋許自己都沒聽過的狠厲。
宋許真厭他這幅惺惺作態表,明明是手起刀落從自己心上割的劊子手,卻最裝一臉無辜不知。
嚴與非閉上眼,啞聲道:“對不起……”
這些話宋許都和他說過,可他只覺得是玩鬧之舉,后來宋許漸漸不說了,他還以為是他們和解多時。
直到今天他才知道,那些玩笑般的嫌棄,偶爾讓他換個伴的提議,都是真心。
回報他的,是宋許一聲冷笑。
道歉的話,是虧欠者的自我排解,這句話,還是嚴與非曾和他說起。
“以后呂肖樊他們不會在出現在你面前了。”
這是他目前能給宋許的承諾。
“那秦景呢?嚴文嚴武?白音然?”
宋許扯了扯角。
嚴與非看向他:“合利還和白家有合作,嚴文嚴武……我會讓他們見你。”
宋許表冷漠,對此不置一詞。
雖然他看錯了很多,但嚴與非在這一點上永遠不會讓他失,丟棄沒用的,保留有利的,永遠靠價值取舍,他早知道會是這樣。
所以才會對嚴與非的執意挽留不一心他現在覺得他值得,可不止那天,又會厭棄。
半晌,宋許搖搖頭輕笑幾聲,他又不是第一天看清,不必置氣。
他邊帶著笑意,眼底冷漠至極,目投向窗外,從飛速倒退的樹影上掠過,像是剛才的事沒有對他造任何影響。
實際上他是在訓練自己竭力擺嚴與非對他的影響力。反正孔家的工程早晚會完工,他也終有一天會離去。
早把嚴與非從自己上剝離開,就早安寧。
嚴與非看見宋許眼底的疏離,心像是被扎了一下:“你別笑了。”
宋許收了笑,倒不是因為嚴與非話:“那秦景呢?”
說著,宋許睨了眼嚴與非,心里對這句話補了一個完整版。
你的知己良人,秦景。
剛剛的話里,似乎無人提及這個名字。
到了家門口,嚴與非下車替他開了門,直到進門,他才又問了一遍。
進門前,嚴與非站在他后,兩人的影在燈下疊到一起。
其實秦景還有用,嚴與非想,可看著宋許的側臉,和兩人疊的影子,嚴與非突然覺得,那個人也不是那麼重要了。
他按住宋許的肩膀,先一步斷絕他躲避的可能,咬住宋許的耳朵,極暗示的輕輕磨著。
“你隨意。”
猜你喜歡
-
完結163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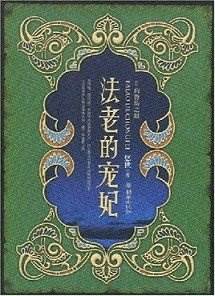
法老的寵妃
埃及的眾神啊,請保護我的靈魂,讓我能夠飛渡到遙遠的來世,再次把我帶到她的身旁。 就算到了來世,就算已經過了好幾個世紀,我和她,以生命約定,再相會亦不忘卻往生…… 艾薇原本是生活在二十一世紀英國侯爵的女兒,卻因為一只哥哥所送的黃金鐲,意外地穿越時空來到了三千年前的古埃及,而那只黃金鐲就此消失無蹤。艾薇想,既然來到了埃及就該有個埃及的名字,便調皮地借用了古埃及著名皇后的名字——「奈菲爾塔利」。 驚奇的事情一樁接著一樁,來到了古埃及的艾薇,竟還遇上了當時的攝政王子——拉美西斯……甚至他竟想要娶她當妃子……她竟然就這麼成為了真正的「奈菲爾塔利」!? 歷史似乎漸漸偏離了他原本的軌道,正往未知的方向前進……
71.2萬字8 5714 -
完結183 章

南春暖嫁
這世界上分為三種人,男人、女人,還剩下一種就是像池意南這樣的瘋子,很不幸,蘇暖瑾不僅招惹了這個瘋子,還坑爹的嫁給了他。 婚后睡前的某一天晚上: 池意南掀開被子,目光灼灼的落在女人的小腹上:“暖謹,你很久沒運動了。” 蘇暖瑾悠悠抬頭,摸著小肚子,撇嘴:“肉多冬天更保暖。” 池意南不為所動,俯身靠近:“不如讓我幫你減減。” 蘇暖瑾眸色一緊,身子后仰。 池意南瞇眼,無節操的更進一步:“更喜歡哪種姿勢?” PS:本文不算多肉,只是有些情節需要,不要被文案嚇到啊,九卿君保證絕不棄坑,放心跳吧! 主角:池意南、蘇暖瑾 配角:林景生、秦然、陸子驍 其他:都是姨媽啦 (強取豪奪+婚戀文+** 男主 一個號稱瘋子的男主 霸道強勢陰晴不定喜怒不形于色 女主再折騰也逃不出男主手掌心啊 )
16.5萬字8 22598 -
完結405 章

離婚后前夫向她服軟
他娶她,因為她長得酷似他的白月光。白月光回來,她被冷眼嘲諷:“你這個瞎子也敢肖想冷墨琛?”離婚后,冷墨琛發現替身前妻竟然打了個漂亮的翻身仗,身邊寵她的優秀男人更是多如繁星。優秀男人們:感謝冷總給的機會!悔到吐血的冷墨琛猩紅著眼眶把她扣在辦公桌上:“復婚,立刻!”“奉勸冷先生一句,別愛我,沒結果。”
82.3萬字8 93701 -
完結37 章

讓全世界知道我愛你
三年前,他殘忍的讓她打掉孩子,在婚禮上另娶他人,三年後她帶著一個得了絕癥的孩子回來,落在了他的手裏,一次次的羞辱,一次次的折磨,以愛的名義,他把她傷到極致,從來沒有想過要停止,直到一張帶血的DNA擺在他的麵前,他才知道,她從來沒有背叛過她,可是為時已晚……
4.6萬字8 10169 -
完結742 章

夜宴
徐歲寧跟洛之鶴結婚的前一晚,陳律死死拽著她的手腕,顫著聲音說:“明明是我,先跟你好的。”愛情多不可靠,所以我最喜歡,夜里盛宴狂歡,白日一拍兩散。 ...
94萬字8 6964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