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宮有福》 第92章 第92章
92
這下福兒終于弄懂了。
合則這署就相當于皇后娘娘的坤元宮, 只有住在坤元宮的皇后,才是正兒八經的皇后。
若坤元宮被人所占,皇后則面掃地, 無法在皇宮里建立自己的威嚴,是時闔宮上下都會瞧輕皇后,皇后想做什麼事, 也無法得心應手。
久而久之,皇后有名卻無實, 被人奪權甚至鳩占鵲巢。
聽完福兒的說法, 衛傅苦笑不已:“你為何要拿母后做例子。”
“這例子不是比較清晰明了?你看你懂場上的事, 我懂宮里的事,其實我倆說的都是一件事。如此說來,那署要趕搶回來才是。可如何搶呢?他既然打定主意要占著了,肯定有對付我們的方法。”福兒苦惱道。
而那邊, 大郎想咬爹爹的手,可爹爹一直不給他咬,還用手推他腦門。
他靠近一點,就被推開了,連續幾次下來,他惱了怒了, 發出一聲憤怒地嗚咦聲, 坐直打了衛傅的手一掌。
“你看你,活該吧,不給他啃就不給他啃,偏偏你要推他, 惱了。”當娘的幸災樂禍。
“壞!”大郎脆聲道。
“對, 他壞, 我們別理他。”
福兒把兒子抱過來,大郎也知道跟娘是一國的,當即一頭扎進福兒懷里。
“不理!”
說這話時,他還一只眼睛來,瞧瞧爹的反應。
小兩口被這憨小子給逗笑了。
福兒湊趣道:“好,咱們不理!”
又攬著抱著他,大郎也回抱著娘,眼饞給臭爹爹看。
“我覺得這事不能拖,快刀斬麻,最好打他個措手不及。人家在當地待了這麼多年,方方面面的事和人都悉,指不定多挖幾個坑絆著你,拖久了更不好搶回來,就算搶回來,到時候也沒用了。”威嚴已失。
Advertisement
衛傅道:“我也是這麼想的,所以我打算明兒一早便去署。”
“他不來請你,你上門找他,會不會損了你的面?”
“你想——”
“那幾個馬匪。”
福兒眼睛一亮。
.
經過一晚上的調整,蘇利神清了氣爽了,思路有了,心里也沒那麼慌了。
一大早起來,他吃了兩碗用田胭脂米煮得紅棗粥,吃了一籠龍眼包子,一碟涼拌。
這頓早飯,在關甚至在建京都不算什麼,可在這黑江之畔,也就只有真正的豪商富戶才能用得起。
吃罷,他抹了抹,來心腹打算讓下面人安排一下,等會兒去接迎那位新上任的安使大人。
既然要做戲,就要做全套,京城來的,人又年輕,最是經不得手下人捧,順著意把捋順了,哄好了,接下來的事就好辦了。
可蘇利已經好多年沒扮過孫子了,他覺得自己不一定能扮得像,遂還在心里演練了好幾遍,覺得差不多了,才滿意地站了起來。
正準備踏出門,突然心腹跌跌撞撞跑進來,撞了他滿懷。
“什麼事這麼慌慌張張?”
“總管不好了……”
蘇利不喜下面人他大人,喜歡下面人他總管,所以他手下平時都記這麼他的。
“什麼不好了?一大早上的,晦不晦氣?”蘇利沒好氣斥道。
“那個安使、安使……”
“安使怎麼了?”
“他居然一大清早,拉著捉來的馬匪,從住來到總管府,說來的路上到馬匪劫掠,正好新上任,就拿這些馬匪開刀。”
心腹過來氣,終于把話說順暢了。
可他接下來的話,卻讓蘇利變了。
“他是用繩子把馬匪們一個個串起來,一路讓人拉到總管府的。黑城難得見這樣的事,后面跟了許多來看熱鬧的百姓,現在府外面可熱鬧了。可由于您代過,門子不敢放那位安使進來,他也不惱,就站在大門前,現在聚集的百姓越來越多……。”
.
黑城的署,其實是蘇利仿造大燕慣制建出來的。
就是前衙后宅的格局。
此時衙門的大門前,聚滿了人。
要說黑城人最厭惡什麼,莫過于馬匪。
這些人葷素不忌,有時到普通百姓,都會把你搶劫一空。關鍵是府也不作為,以至于黑城壯年男子人人帶刀,一旦出城,不管是打獵還是采參,都要結伴而行。
此時見新上任的安使大人,捉了這麼多馬匪,還說要當眾審案,圍觀的百姓都拍手稱快。
可在衙門前站了多時,大門竟然不開。
有人思及總管平時作風,不有些同新來的安使大人,也有人不得這個只敢在百姓頭上作威作福的總管趕倒霉。
也有許多做商人打扮的人,遠遠站在人群外看著。
匪從來只有與勾結,才能大行其道,稍微明眼點的人,都能看明白前陣子城里瘋傳新安使消息背后的勢態。
這位新上任的安使抓了這麼多馬匪上門,不是大水沖了龍王廟,自家人送到自家人手里了?
總之,眾生百態,而所有人的目都聚集在閉的衙門大門上。
等了差不多一刻多鐘的時間,眼見聚來的人越來越多,這時大門突然從里面打開,匆匆走出來一個穿常服的干瘦男子。
劉長山上前一步,冷喝道:“終于知道開門了?讓你們的守備出來,好大的狗膽,上到來,竟敢不出來接迎,看等我回去不稟了鄂將軍治了你們守備的罪。”
蘇利直接被這一番話打蒙了。
他就是守備啊?為何此人說他不來?這才發現自己匆忙之下竟忘了穿袍。
又聽提及了鄂將軍,他頓時慌了,以為劉長山是建京那邊派來護送新安使的武將。
至此,他終于想到自己了什麼。
這黑城于極北之地,朝廷怎可能命新安使一個人上路?即使京里不派人,建京也會派人護送,那自己的所作所為,是不是全落在鄂將軍手下人的眼里?
一時間,蘇利只覺得冷汗直冒。
黑城的九月過半,天已經極為冷了,即是如此,他的背心也頃刻被冷汗打。
他到底是怎麼被豬油蒙了心,還是在黑城這地方當土皇帝當慣了,才會覺得自己記能拿新任的安使?
大一級死人,他憑什麼覺得他一個小小守備能拿經略一地的安使?
不管蘇利是如何想法,劉長山在喝出那一番話后,順手就把他搡了開,往衙門里闖。
一行二十個兵卒,個個都是彪形大漢,那陣勢可把蘇利后的心腹和手下給嚇蒙了。
又見總管也被嚇得不敢噤聲,竟就任這群人闖衙門中,而隨其后看戲的百姓們,一窩蜂地都涌這不常開啟的衙門大門。
……
當初蘇利為了圖省事,也是想展現威風。
特意把署蓋了前衙后宅的格局,可前面的衙門極會用到,也沒有衙役。他是武將,帶的自然是手下兵丁。
一群大老,你讓他們斷案審案,那是不可能的,只有蘇利為了顯示威風時,這衙門才會大開,他會借著守備地方的由頭,來公開置些與自己不對付的人或勢力,為自己造聲勢。
但那也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也就只能欺負些小商人,或是普通百姓,稍微有點勢力的,為了權衡利弊,他也不敢招惹。
此時偌大的公堂,只公案上的灰塵被劉長山等人抹去了。
衛傅一朱紅的袍,來到公案后坐下,就這麼開始審起案來。
由于苦主是他本人,十多個馬匪經過整整一天的寒冷、以及傷勢的摧殘,早已是奄奄一息,自然供認不諱。
不過衛傅并未當場判了他們的罪,而是暫時將這些馬匪收押,并當眾宣稱半月接百姓對這些馬匪的訴狀,是時數罪并罰,一并置。
由于這一番架勢做得極足,圍觀的百姓俱是拍手好。
已經有人在仔細認人了,看馬匪有沒有搶過自己。
因為方才安使大人說了,讓他們不用害怕被報復,他可在署里私下接他們的訴狀,并承諾他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剿掉為禍一方的馬匪。
說起剿滅馬匪時,安使大人深惡痛絕,顯然還沒到任就被馬匪劫掠,也讓他吃了不苦,痛恨至極。
自然讓那些曾被馬匪禍害過的百姓同,因此對新上任的安使大人也有些信心了。
隨著馬匪被帶下去關押,圍觀的百姓也都散去了,大堂里只剩下頗有尷尬又有些難安的蘇利,以及他心腹手下,和衛傅一行人。
“安使大人,其實下就是本地的守備,下姓……”
衛傅做出詫異之態。
“那方才倒是劉大人給誤解了?”
他又做出‘劉大人’非本直屬手下,本也不好訓斥,你懂得的姿態。蘇利自然心領神會,同時更是忌憚這位建京來的‘劉大人’。
“安使大人,昨日下隨同拙荊一同回娘家,不知大人已到,今晨回來才聽說,正想去接迎大人,沒想到大人竟……”
其實說這話的同時,蘇利看著衛傅年輕俊的臉龐,心中各種念頭往出冒。
昨日便聽說這位安使著實年輕,沒想到竟如此年輕,還生得如此好相貌。通派頭,尤其那矜貴姿態,像極了某個王公勛貴家的記子弟。
其實也是黑城消息太過閉塞,蘇利著實不知衛傅份,甚至不知他是新科狀元郎,只知道人是京城那邊過來的,連新任安使很年輕,也是昨晚守門卒稟上來的。
因此他忌憚‘劉大人’的同時,也忌憚上衛傅了,心想他是不是某王公國戚家的子弟。
衛傅做出一副我理解的模樣,又道:“無妨,昨日本和妻眷在那宅子里歇息得還不錯,反正不過住一晚,不當什麼的。”
這話都說這樣,他該怎麼說?
蘇利心里正尋思著,忽然聽聞一聲道:“夫君,大郎困了,讓這大人先命人帶我們下去歇息吧,你們再慢慢談公務?”
蘇利這才發現公堂上竟還站著個抱著孩子的子,之前他也沒注意,應該是站在方才圍觀的那些百姓里。
“這位便是夫人吧?”他忙道。
福兒大大方方地笑了笑,道:“大人不用多禮,只是孩子尚小,能否命人帶我們先去后面的宅子里歇息?”
“這——”
“怎麼?難道有什麼不便之?”福兒問。
衛傅也投以疑目。
蘇利尷尬道:“也是下不知大人何時會到,本打算最近遷宅,但一直因為有事耽誤了,如今下的家眷都還住在后宅……”
福兒打斷道:“那這可怎麼辦?難道還讓我們住昨晚那宅子?”
故作不滿之態,看向衛傅。
不待衛傅說話,又跟蘇利道:“大人你看這樣行不行?你現在可能挪出一個小院來?先給我們暫時落腳,我給你一日時間,一日若不夠,兩日夠不夠?兩日應該夠你們遷出去了吧?”
“這——”
“難道兩日也不夠?是不是因為人手不夠?姐夫,要不要你幫幫他們?”福兒面向劉長山說道。
一聽福兒竟然劉長山姐夫,蘇利更覺得這伙人不好惹。
想想,‘劉大人’是鄂將軍的手下,鄂將軍總管整個遼邊一帶三地,這位新安使又是京城來的,疑似某王公勛貴家的子弟。
真鬧出什麼來,劉大人只會幫妹婿去鄂將軍那里告狀,而不會向著他說話。
“夠了夠了,”蘇利冷汗直冒,陪著笑道,“不用兩日,一日就夠了。”
送衛傅一行人去了小院稍作歇息,蘇利便匆匆去安排遷宅的事了。
進了房間門后,又把門關上。
衛傅道:“夫人,你看為夫的方才演得好不好?”
猜你喜歡
-
完結644 章

獸黑狂妃:皇叔纏上癮
“本王救了你,你以身相許如何?”初見,權傾朝野的冰山皇叔嗓音低沉,充滿魅惑。 夜摘星,二十一世紀古靈世家傳人,她是枯骨生肉的最強神醫,亦是令人聞風喪膽的全能傭兵女王。素手攬月摘星辰,殺遍世間作惡人。 一朝穿越,竟成了將軍府人人可欺的草包四小姐,從小靈根被挖,一臉胎記丑得深入人心。 沒關系,她妙手去胎記續靈根,打臉渣男白蓮花,煉丹馭獸,陣法煉器,符箓傀儡,無所不能,驚艷天下。 他是權勢滔天的異姓王,身份成謎,強大逆天,生人勿近,唯獨對她,寵之入骨,愛之如命。
116.9萬字7.5 400695 -
完結169 章

暴君的寵后[重生]
傳言北戰王性情暴戾,喜怒無常,死在他手裡的人不知凡幾。前世安長卿聽信傳言,對他又畏又懼,從不敢直視一眼。 直到死後他才知道,那個暴戾的男人將滿腔溫柔都給了他。 重生到新婚之夜,安長卿看著眉眼間都寫著凶狠的男人,主動吻上他的唇。 男人眉目陰沉,審視的捏著他的下巴,“你不怕我?” 安長卿攀著男人的脖頸笑的又軟又甜,“我不怕你,我只怕疼。” 而面前的男人,從來不捨得讓他疼。 —————— 最近鄴京最熱鬧的事,莫過於北戰王拒絕了太后的指婚,自己挑了丞相府一個不受寵的庶子當王妃。 眾人都說那庶子生的好看,可惜命不好被北戰王看上了,怕是活不過新婚之夜。 所有人都等著看北戰王府的笑話。 可是等啊等啊……一直等到北戰王登基稱帝,等到庶子封了男後獨占帝王恩寵,等到他們只能五體投地高呼“帝后千秋”,也沒能等到想看的笑話。
50.7萬字8 38486 -
完結255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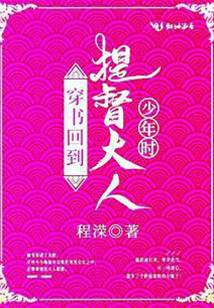
穿書回到提督大人少年時
她書穿成了女配,可憐兮兮地混在公堂的男男女女中,正等著知縣大人配婚。 女年十七,父母不嫁者,使長吏配之。 按照劇情她注定是炮灰,超短命的那種。 她不認命,急切的視線在人堆裡可勁兒地扒拉,終於挖掘出他。 夭壽呦,感情這小哥哥,竟是男二! 連女主都無法覬覦的狠人! 這位爺有秀才功名在身,卻被至親算計,入宮成為殘缺不完整的太監。 他生生地熬過種種苦難,任御馬監掌印太監,最後成了人人敬畏的提督大人。 他曾顛沛流離,人人嫌惡,也曾位高權重,人人討好。 成為看盡人生百態,孑然一生的權宦。 但這都不是重點,重點是他壽終正寢! 只要她抱緊他的大腿兒,定能擺脫螞蝗般的至親,待日後做了大宦官之妻,更是吃香的喝辣的,還不用費勁巴拉的相夫教子。 小日子簡直不要太美好,撿大漏啊! 他一朝重生,再回少年時,尚未入宮,更未淨身。 眼下,他還是小三元的窮秀才,父暴斃而亡,母攜家資再嫁。 他浴血歸來,渾身戾氣,可一時善心,就多了個嬌嬌軟軟的小娘子! 說啥他這輩子也不淨身了,好好地考科舉,走舉業,給她掙個誥命夫人做,再生幾個小崽子玩玩兒……
44.7萬字8 23041 -
完結794 章
盛寵天下:不良醫妃要休夫
大婚之日,軟弱的草包嫡女雲安安被庶妹陷害與他人有染,渣男將軍更是將她打到死,並且休書一封將其掃地出門。 鳳眸重視人間之時,二十一世紀賞金獵人雲安安重生,洗盡鉛華綻,瀲灩天下。 “小哥哥,結婚麼,我請。” 雲安安攔路劫婚,搖身一變從將軍下堂妻成為北辰國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攝政王寵妃。 世人都說攝政王的寵妃是個不知檢點的草包廢物,可一手銀針起死人肉白骨,經商道成為天下首富,拳打皇室太子腳踏武林至尊又是誰? “王爺...... 王妃說她想要當皇帝。 “ 北辰逸眼神微抬,看著龍椅上的帝王說道”你退位,從今日起,本王的夫人為天。 ”
155.3萬字8 14973 -
完結135 章

偏執帝王掌心囚:千金為奴恕不從
【隱忍堅毅侯府假千金*狠厲偏執竹馬渣帝】身為濮陽侯府嫡女,宋玖兒享盡榮光,可一朝身世揭露,她竟是冒牌貨!真千金入府,爹娘棄她、世家恥笑,而深愛的未婚夫蕭煜珩,卻疏離避著自己。哀莫心死,宋玖兒嫁與清貧書生,可未曾料到,雨催風急的夜,房門被踹開。新帝蕭煜珩目光沉沉,陰鷙抬起她的下頜:“朕允你嫁人了嗎?”她被虜入宮中做賤婢,受盡磨難假死出宮卻發現有喜。幾年後,聽聞帝立一空塚為後。小女兒杏眸懵懂,“娘親,皇上真是深情。”宋玖兒微微展眉,“與你我無關。”蕭煜珩曆盡萬難尋得那一大一小的身影,赫然紅了眸:“你是我的妻!”
21.3萬字8.18 7810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