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風一度共纏綿》 第247章 你被他騙了!
喬溫爾,這個已經銷聲匿跡許多年的人,看到此時此刻的樣子,我十分吃驚。
在我的印象里,喬溫爾簡直就是“狐貍”的代表,然而現在,站在我面前的,是一個材走形的人,已經發福,雖然盡量想表現得優雅,但只讓人覺得俗不可耐。
唯一沒變的,就是那勾魂的眼神,然而我是個人,所以這招對我沒用。
喬溫爾能一進來就喊我程安安,肯定是陸慕舟告訴,我就是程安安,否則即使我們在路上肩而過,也不會知道我是誰。
可是,陸慕舟讓我見喬溫爾做什麼?
我心生疑,沒有馬上應答,而是審慎地上下打量。
“來,先坐下。安安,肚子了嗎,先點些東西吧。”
陸慕舟仿佛一個和事佬,打開菜單,招來服務生,自己點了幾樣,而后向我,給我打了一個手勢,讓我自己挑。
我并不是來吃飯的,也沒什麼胃口,現在看到喬溫爾更加倒胃口,我可不會忘記當時對我做了什麼事。
不過也多虧了,否則我和陸承北也不會更近一步。
端坐著,我幽幽看了陸慕舟一眼,他安排喬溫爾以及這位從沒見過面的男人和我共坐一桌,總不會只是為了促進。
點完餐,陸慕舟才終于要進正題。
他微微笑了一下,對我說,“安安,見到老朋友,有什麼想說的嗎?”
“老朋友?可不算是我的老朋友。”涼涼回了一句,我覺得不需要在他們面前做樣子,現在又不是搶點擊率,沒人會在意我說的話是輕還是重。
聞言,喬溫爾的臉變了變,應該是有點生氣,但還是保持著微笑。
“安安,我們到底共過事。”
“啊,是啊,是一起鬧過事吧?陸老板,你到底想和我說什麼?”
Advertisement
不太喜歡這種被甕中捉鱉的覺,我有些耐不住子。
其實我在看到喬溫爾的時候,心里就有一種很不好的預,這種預將我的耐心消磨殆盡。
陸慕舟的笑容一僵,而后看了喬溫爾一眼,對方像收到信號一般,突然站了起來,對著我,“程小姐,我想對陸先生,我是說陸承北,你還有很多不了解的地方。”
聽到“陸承北”三個字,我心里咯噔一聲,喬溫爾和我說我不了解陸承北,難道就了解。
冷笑一聲,我斜睨著,想看看到底想說些什麼。
喬溫爾轉頭看了一眼陸慕舟,而后緩緩坐下,似乎是覺得自己的緒太激了一些,有些不合常理。
“程安安,你覺得你了解陸承北多?你眼中的陸承北是不是就是真的陸承北?”
我以為喬溫爾一開口就是陸承北有多麼多麼不堪,多麼多麼不折手段,然而忽然問我這麼一句,我一下被噎住。
老實說,我也捫心自問過自己這個問題,我到底了解他多,在我面前的陸承北是不是真實的,他對我“真”多。
然而,這個問題不會有答案,因為我不會去向陸承北驗證。
大概是我的遲疑讓喬溫爾看出貓膩,趕趁熱打鐵,“雖然我們以前有過節,但同樣是人,我就給你一個忠告。”
說到這里,喬溫爾故意頓了一下,的停頓讓我心里更加不舒服,但又很想知道到底想說什麼。
“陸承北,他這個人沒的。”
沉默了一會兒,喬溫爾忽然深沉著臉說了這麼一句。
我盯著,說到陸承北無,沒人比我更懂,喬溫爾說真的還真沒有資格這麼說。
“哦。”冷冷回一句,我不太當回事,“如果你只是要和我說這個,我想就免了吧,大家都沒那個國時間閑聊。”
我此話一出,陸慕舟便微微笑了一下,“安安,別心急,慢慢聽下去。”
得到陸慕舟的鼓勵,喬溫爾了腰桿,如今看起來全然沒有以前那種囂張跋扈不可一世的樣子,反而有些戰戰兢兢畏畏的。
都說歲月催人老,但我看歲月是把喬溫爾作為青春飯的那些特質全部都給催沒了。
該怎麼說呢,如果我當時沒有從主播界退出,也沒有遇到陸承北的話,會不會就在他們兄弟兩個的爭斗中變炮灰,和喬溫爾一個下場呢?
但是世界上哪里有那麼多如果,我只是看到喬溫爾就想起以前不愉快的那些日子,繼而對的話,一個字都不信。
“程安安,你應該還記得徐吧?”
喬溫爾提到徐,我冷不丁打了一個寒,渾都起了一層淺淺的皮疙瘩。
這個名字,我已經五年多沒聽人提起了,我還記得當初和電視臺的那個渣男相識,還是因為他長得像徐來著。
也許因為徐是我第一個暗,或者說真心喜歡的人,所以即使過了這麼久,我一想起,口還會痛。
他當時那麼年輕,那麼有才華,卻因為我面前的這個人跳樓自殺,我是真心為他不值。
我不知道喬溫爾現在突然提起他是想說什麼,難道想說,其實徐的死和沒關系,而是和陸承北有關嗎?
我只要腦袋還沒壞,就不會信的鬼話。
然而讓我驚詫的是,喬溫爾還真的這麼說了。
十分慎重而認真地對我說道,“現在我和他也不是那種關系,所以沒必要為他瞞,其實徐就是陸承北弄死的,你想知道原因嗎?”
說到這里,喬溫爾才稍微恢復了一些以前的那種矯造作。
我沒應聲,但是一直盯著。
喬溫爾自說自話,繼續說道,“那是因為我當時算是他的人,但是徐不識時務,雖然不是特意讓人做了他,但徐確實是因為陸承北死的,只因為他嫌他礙眼,死他就像一只螞蟻。”
“……”雖然心里不想相信,但是喬溫爾這麼說,我覺得還有點像是那時起的陸承北可能做出的事。那時候的他沒有現在這麼,也更隨心所一些。
但是,僅憑喬溫爾一面之詞,我還是不信。
徐的死,某種程度造了我很長一段時間的墮落。
現在回想起來,仿佛還是會呼吸的痛一般。他對我的意義和陸承北不同,因為沒有得到的初永遠都是最好的一樣。
如果真的是陸承北做的,我想我很難原諒他。
心里有疑,不過我表面上沒有表現出來。
“你對他,你覺得你有什麼特別有價值的地方嗎?我看應該沒有吧?也就是說,為了既得利益,他可以毫不猶豫拋棄你。”
“不會,他不會的。”只有這一點,我很快打斷,陸承北如果真的想拋棄我,就不會為我做那麼多事,即使只是為了維護尊嚴,我都會深信不疑這一點。
然而,喬溫爾卻諷刺地笑了,“程安安,你還真的當你是陸承北的真命天?你先看清楚他現在在做的事吧,你肯定以為他是假結婚,但是假結婚有這麼搞的嗎?俆家能給他想要的經濟支持,他即使和俆若言沒有,也一定會照單全收。你別被他騙了,陸承北可是一個什麼都做得出來的人!”
“溫爾,別這麼說,,我們就事論事,不要摻雜個人。”陸慕舟此時還很假惺惺地出來說一句公道話。
他這麼說,我心里越不爽。
“我只是說事實。”被陸慕舟一提醒,喬溫爾才有所收斂。
但是這個事實,未免說得太過特意,反而失去了說服力。
空氣突然安靜了下來,這個空檔,服務生上了餐。
陸慕舟點了多,看起來香味俱全,但是毫勾不起我這個吃貨的食。
“你要是還有點人的自尊,就離開他,省得被他賣了還幫人數錢。”喬溫爾又怪氣地說了一句,而后說還有事,不留下吃飯,便當先離席。
喬溫爾離開,桌子就空出一個口子,但是我今天的心已經完全被破壞了。
陸慕舟見我一直沒筷子,便問我,“安安,不合胃口嗎?”
我抬眸看他一眼,閃爍著眼神,訕訕回道,“沒什麼,我不是很。”
“這樣。”陸慕舟自己喝了口水,而后幽幽對我說了一句,“其實剛才喬溫爾所言,也并沒有夸大。安安,陸承北的為人……我不想落井下石,但確實不怎麼樣。”
“你和他都過節,自然會這麼說。”如果說喬溫爾的話我半信半疑的話,那陸慕舟的話,我便全然不會信。
他和陸承北的矛盾那麼深,自然什麼中傷的話都說得出來。
然而他臉上掛著的那種自信笑容,卻讓我有些不安。
“我知道我說的話你不會信,但是別人說的話,你總該信一些吧?”
說完,陸慕舟給坐在他旁邊的那個中年男子使了個眼,介紹道,“這位先生是現在還和陸承北公司有投資關系的老總,他有些東西想讓你聽聽看。”
“讓我聽?”
疑地看了對方一眼,只見這個老總不知道從哪里拿出了一個錄音筆一樣的東西放在桌子的正中央,而后按下播放鍵。
然后,我便聽到了陸承北的聲音。
猜你喜歡
-
完結131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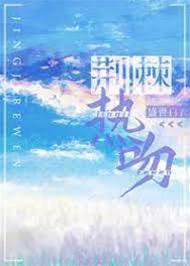
荊棘熱吻
季弦星有個秘密,她在十六歲的時候喜歡上了一個人——她小舅的朋友,一個大她八歲的男人,后來,無論她怎麼明示暗示,鐘熠只當她是小孩。她安靜的努力,等自己長大變成熟二十歲生日那天,她終于得償所愿,卻在不久聽到了他要訂婚的消息,至此她一聲不響跑到國外做交換生,從此音訊全無。再見面時,小丫頭長的越發艷麗逼人對著旁邊的男人笑的顧盼生輝。鐘熠走上前,旁若無人的笑道:“阿星,怎麼見到我都不知道叫人了。”季弦星看了他兩秒后说道,“鐘先生。”鐘熠心口一滯,當他看到旁邊那個眉眼有些熟悉的小孩時,更是不可置信,“誰的?”季弦星眼眨都沒眨,“反正不是你的。”向來沉穩內斂的鐘熠眼圈微紅,聲音啞的不像話,“我家阿星真是越來越會騙人了。” 鐘熠身邊總帶個小女孩,又乖又漂亮,后來不知道出了什麼事,那姑娘離開了,鐘熠面上似乎沒什麼,事業蒸蒸日上,股票市值翻了好幾倍只不過人越發的低沉,害的哥幾個都不敢叫他出來玩,幾年以后,小姑娘又回來了,朋友們竟不約而同的松了口氣,再次見他出來,鐘熠眼底是不易察覺的春風得意,“沒空,要回家哄小孩睡覺。”
51.8萬字8.18 232480 -
完結2033 章
盛世婚寵:帝少難自控
她的孩子還未出世便夭折在肚子裏!隻因她愛上的是惹下無數血債的神秘男人!傳聞,這個男人身份成謎,卻擁有滔天權勢,極其危險。傳聞,這個男人嗜他的小妻如命,已是妻奴晚期,無藥可治。他說:夏木希,這輩子你都別想從我身邊逃開!你永遠都是我的!她說:既然你不同意離婚,卻還想要個孩子,那就隨便到外麵找個女人生吧!我不會怪你。五年後她回來,發現那個男人真的那麼做了。麵對他已經五歲的孩子時,她冷冷地笑著:秋黎末,原來這就是你放棄我的原因?那時她不知道,這個男人已丟掉了一隻眼睛……而這個五歲的孩子,竟也滿身是謎!——那是夏與秋的間隔,夏的末端,是秋的開始。秋,撿到了失意孤寂地夏的尾巴。夏,許諾終生為伴,永不分離。經曆了離別與失去,到那時,秋,還能否依舊抓住夏的氣息?
566.6萬字8 14283 -
連載1657 章

雙寶媽咪是大佬顧挽情
五年前,顧挽情慘遭未婚夫和繼妹算計,與陌生男子共度一夜,母親因此自殺,父親嫌她丟人,將她驅逐出家門。五年后,顧挽情帶著龍鳳胎回歸,一手超凡醫術,引得上流社會無數人追捧。某德高望重董事長,“我孫兒年輕有為,帥氣儒雅,和你很相配,希望顧神醫可以帶著一雙兒女下嫁!”追求者1:“顧神醫,我早就仰慕你,傾心你,希望可以給我個機會,給你一雙兒女當后爸,我定視為己出。”
166萬字8 338525 -
完結442 章

把她送進監獄後,慕少追悔莫及
慕南舟的一顆糖,虜獲了薑惜之的愛,後來她才知道,原來一顆糖誰都可以。一場意外,她成了傷害他白月光的兇手,從京都最耀眼的大小姐,成了令人唾棄的勞改犯。五年牢獄,她隻想好好活著,卻背著“勞改犯”的標簽在各色各樣的人中謀得生存。再遇慕南舟,她不敢愛他,除了逃,還是想逃!慕南舟以為他最討厭的人是薑惜之。從小在他屁股後麵跑,喊著“南舟哥哥”,粘著吵著鬧著非他不嫁,有一天見到他會怕成那樣。他見她低微到塵埃,在底層掙紮吃苦,本該恨,卻想要把她藏起來。她幾乎條件反射,麵色驚恐:“放過我,我不會再愛慕南舟了!”慕南舟把她禁錮在懷中,溫柔纏綿的親她:“乖,之之,別怕,叫南舟哥哥,南舟哥哥知道錯了。”
85.7萬字8 63357 -
完結561 章
離婚后孕吐,總裁前夫追瘋了
隱婚三年,他甩來離婚協議書,理由是他的初戀回來了,要給她個交待。許之漾忍痛簽字。他與白月光領證當天,她遭遇車禍,腹中的雙胞胎沒了心跳。從此她換掉一切聯系方式,徹底離開他的世界。后來聽說,霍庭深拋下新婚妻子,滿世界尋找一個叫許之漾的女人。重逢那天,他把她堵到車里,跪著背男德,“漾漾,求你給我一次機會。”
117.1萬字8 25757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