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偷心媽咪嫁到:總裁,你快跑!》 第77章 超級的不爽3
意夫人一下到一樓,就看見意俊彥倚在沙發上,瞪大著眼睛,仰頭著天花頂的吊燈出神。
意夫人迷地也跟著一眼,未見新奇的事,才皺著眉問:“你怎麽跑進人家小汐的房間去了?很生氣!”
意俊彥的也不,倒是了,“我已經說了,我喝醉了,進錯房間。”
意夫人突然往他邊一坐,低聲音很是欣喜地問:“你是不是對人家做了什麽?”
意俊彥子一僵,連忙坐直子,沉聲說道:“媽,我什麽都沒做,就是以為是自己的床,躺了上去,還沒反應過來,就被一腳踹下床了。”
聰明如他,怎麽會不知道,一旦承認了剛剛自己所做的事,老媽還不他負責,娶藍汐嗎?他才不會這麽笨!
“真的什麽也沒做?”意夫人仍不相信,而且,還在兒子的眼神裏,發現了一些東西,兒子分明在撒謊,不然為何眼神閃爍?
“信不信由你,我很累了,冒也很難,我去洗澡睡覺了,媽你也早點睡。”意俊彥扔下這幾句話,就不等意夫人反應過來,上了樓。
其實,此時他也很煩悶,剛剛發呆,便是在想一個問題,他為什麽隻對藍汐一個人的有反應呢?剛剛隻是兩人的在一起,他便無法控製自己的。
現在,他沒有心再回答老媽的問題,隻想再衝一個冷水澡使自己清醒。
明知道自己冒沒好,他還是不怕死地,冷水往自己臉上、上灑。
第二天,意俊彥的冒更嚴重了,他覺頭很沉,早晨意夫人喚他起床時,他把被子一蒙,就賴在床上,一直到睡到日曬三竿。
因為肚子,他不得不爬了起來。
就當他穿著睡袍走下樓,就見在廳裏與兩個孩子正玩跳棋的藍汐突然猛一瞪他,然後對兩個小孩說:“承承,諾諾,玩跳棋太煩了,媽咪今天帶你們去海上樂園看海豚如何?”
Advertisement
兩個孩子一聲耶,跳了起來,拍手好,“好啊好啊!上與爹地!”
藍汐卻說,“不了,你腰疼,你爹地不舒服,媽咪帶你們去,隻買媽咪一人票,可以省錢哦!”
“這樣啊!那好!”兩個孩子同時點頭,一邊一個拉著藍汐的手,當著意俊彥麵,消失在他視野。
當再也看不見那一大二小的影,意俊彥的角竟揚了起來。
他發現,藍汐在生他的氣,就如妻子生丈夫氣,通常都會冷戰,冷戰卻是朝他瞪眼,要不就是不屑看他。
現在藍汐的表現,令他很滿意。
他終於報到仇了,昨天他被氣得七竅生煙,今天換藍汐,他怎麽可能不得意呢?
意夫人很頭疼!頭疼兒子不爭氣。
就如現在吧,兒子與幹兒的冷戰整整持續了一周,兒子冒越來越嚴重,不時的咳嗽,本來應該休息的他,卻持續一周每天去上班。
下了班後還進書房,挑燈工作。
而幹兒說到做到,把鎖給換了,每天晚上抱著兩個孩子一起睡。
二人不僅沒有升溫,反而越來越僵了,這可讓為難了,覺自己都使不出技了。
坐在沙發上,一直在哀聲歎氣,恐怕沒有一個婆婆像這樣悲催的,還要擔憂兒子與媳婦二人來不來電。
“唉……”又一聲歎息,已經不知道自己歎了多次了。
承承與諾諾被保鏢送回家,看到的便是意夫人一個人坐在沙發上長噓短歎。
“,你怎麽了?”一人抱一邊,兩個孩子異口同聲問。
意夫人手,擁住二人,說道:“在頭疼。”
諾諾說:“諾諾給你,哪裏疼呢?”
意夫人欣地笑,說“頭疼的啊,是你爹地與媽咪在冷戰,你媽咪都不理你爹地呢!兩個人,一周又見不上一麵了。你爹地早出晚歸,你媽咪晚起早睡,這算什麽啊。”
承承說:“那你再想辦法讓爹地與媽咪說上話啊!”
意夫人搖頭:“孫子啊,這紅娘沒那麽好當啊,什麽方法都試過了,你媽咪就是不肯和你爹地一起吃晚飯。”
諾諾撐著下,眼珠轉啊轉,“那怎麽辦好呢?”
意夫人隨口說道:“除非我們都不在家,留你爹地媽咪在家,兩個人才可以說上話。”
承承哦了一聲,說“諾諾,老師不是說,要去野炊嗎?我們要一起去!”
意夫人一聽,一拍自己額頭,誇張道:“對哦!還是兩個孫子聰明!陪你們去野炊,你們老師說可以帶家人去嗎?”
承承點頭,“可以,老師說要去比較遠的地方,可以帶上爹地媽咪。”
意夫人瞪大了眼,高興得尖“真的啊!太棒了!太棒了!陪你們去野炊,看你爹地與媽咪還來不來電!”
諾諾眨著眼睛:“來電是什麽意思?”
意夫人輕笑:“來電就是……”故意言又止,舉起兩個手指比了比,暗示曖昧。
結果兩個孩子一臉茫然,意夫人隻好歎息道:“就是,你們爹地媽咪一定不會再冷戰,能說上話了。”
“哇!那太好了!”諾諾欣喜地。
“孫子,你們老師說野炊是哪天啊?”意夫人記起正題,問道。
“星期五啊!野炊完就放假。”承承回答道。
“真的!那太好了,我們野炊完後,不回家了,給三天時間你爹地媽咪相哦!”意夫人好開心啊!真的太巧了,正頭疼怎麽找個借口帶著兩個孩子開溜,現在就是最好時機。
想想就開心要笑。
藍汐逛街回到家,前腳剛踏,就見意夫人神兮兮地著。
“幹媽?有事嗎?”東西還沒有放下,就直覺地問。
意夫人點頭如搗蒜,支吾了好半天,才假裝猶豫要不要開口,言又止,“唉,算了,明天再來跟你說。”
藍汐被調起了好奇心,追問:“幹媽,你有什麽事就直說,我聽著。”
意夫人張了張,然後開口說話了,說出早已想好的臺詞,“小汐,是這樣的,兩個孫子的學校啊,周五,就是後天啊,組織野炊活,學校老師不放心小孩子們,要家長們跟著,我瞧你在生彥的氣,也不好把你們拉在一塊去。所以,我思前想後,還是覺得我與林媽陪兩個孫子去便好了,你和彥在家裏,你就照顧一下他,給他做做飯,彥不會做飯,也不喜在外麵吃,你就辛苦一下……”
“什麽?”藍汐有些不能接,卻不敢有怨言,隻是輕聲問:“幹媽,我也一起去吧,讓林媽給他做飯就好了啊。”
才不要與意俊彥單獨相,誰知他會不會哪筋不對,又來欺負?
意夫人沒想到這個幹兒沒那麽好騙,大腦飛快運轉,說道:“這個不好了,是這樣的,野炊完後,我想帶兩個孩子去那些一起學食的貴婦人家坐坐玩玩。那些貴婦啊,老是誇他們的孫子怎樣怎樣,幹媽氣不過啊,想想我的兩個孫子不知道比他們的孫子孫聰明可多倍,幹媽也好出口氣。不過以前,幹媽一張臭,說你……說你不在世上了,你說我若是突然帶著你去,孩子們喊你媽咪,幹媽這不是自掌,怎樣自圓其說了?”
說完這些話,意夫人心裏笑啊,好聰明啊,這樣的理由也說得出來。
是看死了藍汐的賢淑乖巧懂事,才敢說出這樣的話來。
果不其然,這個幹兒終於中計了。
藍汐終於點頭答應了,“我明白了,我不會為難幹媽你的。”
會遵守意俊彥的要求,絕不會給意家傳出一點緋聞的,哪怕是對外,也不能稱自己是孩子的母親。
“真的?你不怪幹媽?”意夫人佯裝愧疚,“我對外這麽說你,你不會怨幹媽曾經惡毒詛咒你嗎?”
“怎麽會?那時你也不知道我是誰,而我有可能一輩子也不會出現在你眼前,那與死了有什麽區別呢?”藍汐輕笑,“何況,我那時形式所時,也是對外說孩子爹地不在世了,所以,誰也不能怪誰。”
想起以前自己說意俊彥死了,會不知道那種為難的滋味嗎?
意夫人喜悅地笑了:“你能這麽想就好了,那就這麽決定了,我帶著兩個孫子去野炊,三天不回來,這三天裏,就麻煩你來照顧彥了,那臭小子不會開瓦斯,讓他自己做飯到時別弄出個瓦斯炸或火災就完了。這房子啊,是你幹爸唯一留下來的產,我們都要珍惜護別讓它損壞了。”
又一次搬出一個已死的人,藍汐啞口無言,隻能連連答應:“幹媽,我知道了,我不會讓他著的。”
雖是答應,可是仍舊忍不住低咕幾句。
意夫人又說道,“還有,那臭小子最近咳嗽越來越嚴重,晚上煲些雪梨湯給他喝止咳。”
“好,知道。”藍汐皺著眉點頭。
那個狼,還真是!幹媽不在家還有人來服侍他,想想便覺得心裏很冤很悶。
“還有,他別熬夜早些睡,最近看他天天在書房忙工作,好像忙的,我怕他的子撐不下去,你要隨時觀察他的狀況。”
“知道了。”
幹媽真嘮叨,意俊彥又不是孩子,子好不好為什麽要去觀察啊。
實在不想與意俊彥單獨相,那一夜,讓覺自己被汙辱了,本來第一次,他強吻,就覺得他輕佻把當往常的那些人,這讓覺有些惡心。
這意俊彥的吻了多人啊?想起別的人的口水沾在自己上,就恨不得天天瀨口,或是大吐特吐。
“那我就放心的把兒子給你了!”
意夫人突然一拍的肩膀,語重心長,容不得反悔了。
猜你喜歡
-
連載476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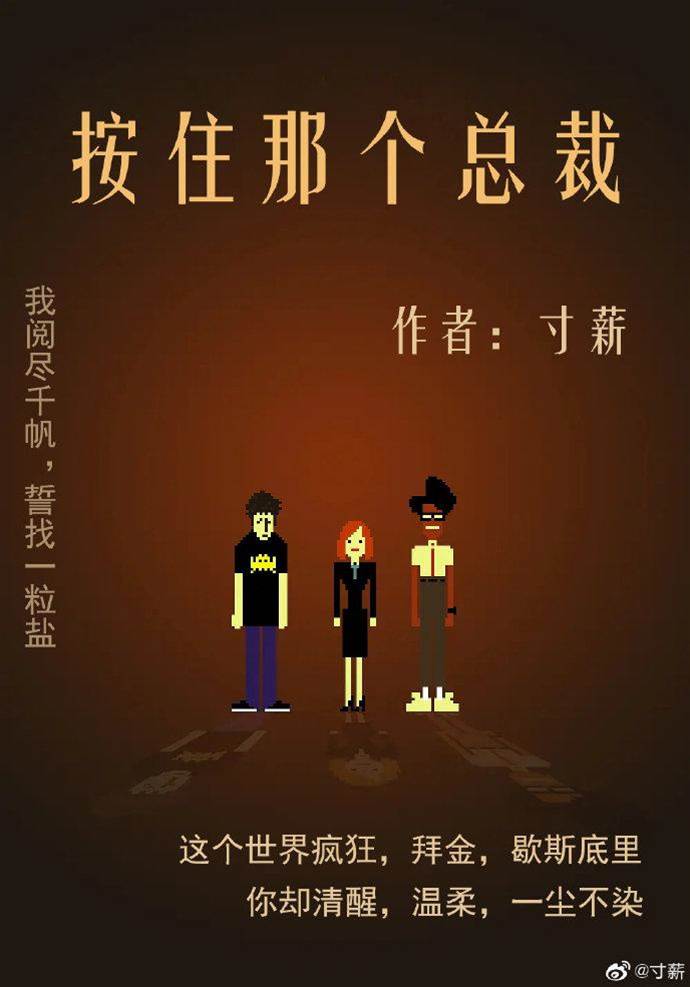
定制良緣
本文原名《按住那個總裁》——————————霸道總裁們在同一部小說里會有怎樣的故事?在這個總裁滿地走,土豪多如狗的世界里,阮長風經營著一家專門打造總裁夫人的事務所即使出廠配置是一無所有的灰姑娘Eros事務所也會幫您覓得如意郎君只是生活中難免會有滿目瘡痍的真相等待您去慢慢發掘-----------------------淺喜似蒼狗,深愛如長風所愛隔山海,山海皆可平----------------------------本文內含多重反轉,人物隨機黑化新手上路,車速不穩請多海涵
103.5萬字8.18 769 -
完結1540 章

陸夫人你高攀不起
結婚三年,陸景盛從來不在乎阮舒。她以為,石頭總會焐熱的,沒想到她等到的結果,是他要她的命。愛情太難了,阮舒不要了。陸景盛再見到阮舒時,怎麼也想不到,萬丈光芒的總裁首富竟然是自己的前妻。記者:“阮總,您年紀輕輕就能做到今天的地位,是有什麼秘訣呢?”阮舒:“別靠近男人,會變得不幸。”第二天,蹲伏阮舒的記者們發現,冷酷無情著稱的陸總,竟然成了他們的同行!“阮總,我有個合作想和你談談。”“什麼?”
139.3萬字8 153601 -
完結859 章

萌寶助陣:媽咪快親親爹地
景延琛睨著麵前的女人,眸子裏滿是鄙夷,“他們的父親是誰你不知道?你到底被多少男人……啊——” 額頭兩角瞬間鼓包。 四個奶包子趾高氣昂,“敢欺負我們媽咪的下場,讓你額頭長犄角!” “臭小子!信不信我關你們黑屋……” 四個彈弓齊齊對準他額頭。 景延琛舉起雙手,“我進黑屋子吧!” …… “三少,親自鑒定報告出來了,他們全是你的孩子!” 景延琛拿著鑒定結果給奶包子看,被奶包子們嫌棄了!
95.9萬字8 62184 -
完結139 章
想對你依賴
裴茉聽聞家里長輩曾在她幼時周歲宴上,與友人為她定下過一枚娃娃親,原是談笑一說,本不作數,她也沒放在心上。后來那日,陵城名門江家老爺子帶外孫回國,聽聞這位外孫年紀輕輕卻已執掌整個江氏,手腕狠辣,沉穩有魄力。而那日在小花園里,裴茉卻見到了占據她整個青春的男人。他長身玉立,生了一雙深情眼,夏風吹過他的額發,是記憶里一塵不染的矜貴模樣。也依舊從骨子里散發著若有若無的疏離。婚后。禹景澤可謂是好好先生,對她呵護至極,眾人也對這樁門當戶對的婚事津津樂道。但裴茉知道,他娶她,是為了讓病重已久的江老爺子安心,對她好,是出于責任。不摻半分喜歡。直到一天,男人把她抱在腿上親吻,聲音無奈卻真摯:“茉茉,我喜不喜歡你,還看不出來嗎。”裴茉揪著他一絲不茍的領帶,“你不說……我怎麼知道。”“我不說,嗯?”男人慣會使壞,她招架不住地睫毛輕顫:“你今天沒說。”聞言,禹景澤低低笑了聲:“這麼說,確實是我的錯了。”他親了親她,以最純情的方式,“今天也喜歡你。”
20.5萬字8 19919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