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牌女助》 第882章 碰她一下都不行
那是一種微弱類似的聲音,一聲一聲,模糊了從鼻腔還是嚨發出的。剛開始岑青禾迷迷糊糊還沒太在意,但伴隨著這種聲音,也沒再睡著,意識逐步清醒,慢慢睜開眼睛,眼的就是一面陌生的牆壁,嚇了一跳,心一慌,還以爲自己癔癥了,但是隨後回過神來,不在家,這是在車上。
對,火車上。
緩了口氣,岑青禾了有些發的胳膊,從側面朝裡,變平躺。
這一平躺倒好,忽然餘瞥見左手邊坐了個人。
每一個包廂裡面都是一側上下鋪休息,另一側擺放著沙發和小桌,供旅客白日裡落腳,岑青禾沒想到,原本應該在上鋪休息的男人,此時正坐在沙發上,上赤,下穿著四角短,叉著,手裡面拿著手機,手機沒耳機,之前迷迷糊糊聽到的那些聲,現在清晰明瞭,就是從他手機中傳出來的。
包廂中唯一的源就是他手機屏幕中傳來的,那照得他一張臉上油四,膩歪無比。
別說岑青禾吃過豬也見過豬跑,估計這會兒就是個智障也知道他在幹嘛。
一般人很難想象這種半宿半夜,被個陌生男人坐在旁看小片的覺,岑青禾甚至懷疑他故意跑到下面來看,就是爲了跟面對面。
這種念頭一出,頓時火冒三丈,騰一下子翻坐起來,蹙眉說道:“這兒是公衆場所,麻煩你戴上耳機,要看去上面看。”
男人目移到岑青禾臉上,脣角一咧,自以爲很邪魅,其實很膩歪的問道:“要不要一起看?”
說話間,他還故意把聲音調大了一些,那些讓人面紅耳赤不忍直聽的迷之聲,瞬間充斥了整個包廂。
Advertisement
岑青禾眼睛一瞪,嘿,好說好商量不行是吧?
懶得再跟他說半個字,直接掀開被子下牀,穿上鞋就去開包廂門,等找到列車員的,丫個死變態,不要臉就讓他丟人丟個夠。
男人見狀,很快從沙發上竄起來,一把拉住岑青禾的手臂。
岑青禾尖一聲,嫌他髒,誰知道他剛纔用這隻手做過什麼沒有,現在又來抓。
男人不讓出門,一直在對比著噤聲的手勢,岑青禾使勁兒甩去一時間沒甩開,還沒等還手,估計前後最多也就五秒鐘的樣子,包廂房門被人從外面一把開,整齊的靳南出現在門口,定睛一瞧,一個只穿著的男人,拽著岑青禾的手臂,他登時目兇,一手拉過岑青禾,擡腳就找著男人的肚子踹去。
男人怎能得住靳南的大力一踹,直接往後栽倒在沙發上,又從沙發上滾到地下。
靳南猶不解氣,衝進包廂裡面對他拳打腳踢,最狠的一下,他揪住男人的頭髮,直接把頭往桌子上撞。
男人發出聲嘶力竭的喊,還高呼著‘救命’。
岑青禾衝過去攔著靳南,照他這個打法,真的會出人命。
靳南被岑青禾死命拉出包廂,臨出門之前還一腳踹在男人小骨上,男人嗷嗷的喊著,整個人抱頭一團。
這邊這麼大的靜,左右兩側包廂的人都出來看,列車員也聞訊快步趕來,車廂中線昏暗,可靳南還是突然擡手扣著岑青禾的後腦,把的臉按在自己肩膀,岑青禾詫異,想擡頭,他低聲音說:“別讓人拍照。”
岑青禾後知後覺,現在算是半個公衆人,如果被人拍到這一幕,估計還沒等下車,網上就得天翻地覆,要去濱海蔘加婚禮的,不能給孔探和丁然找麻煩。
所以一不,額頭抵在靳南肩頭,隔著白的亞麻t恤,是他上灼熱的溫,剛纔瘋了似的打人,這會兒停下來,劉海兒下面都是汗。
列車員開始只來了兩個,後來一看包廂中倒在地上的男人,滿臉都是,地板上也被掃出一條條的痕,端的嚇人,趕用對講機把其他同事都過來。
這會兒更多包廂中的旅客醒來,出門看熱鬧。
醫護人員趕來,先幫裡面的男人理傷口,有人詢問靳南怎麼回事兒,靳南氣得臉煞白,抿著脣瓣一言不發。
他不想說,不想從自己口中說出他看見了什麼,還有沒看見的,吃沒吃虧?吃了多虧?
岑青禾跟他認識久了,多也得清他的格,見他不出聲,主說道:“那人半夜三更坐在我對面看黃片,還開外音,我讓他關掉,他不關,我想出來找人,他拉著我不讓我走,幸好我朋友就住隔壁,我喊人過來才逃過一劫。”
列車員在包廂裡面找到男人的手機,確定裡面正在播放著作片,對於這種變態,大家上不說,但也都覺得靳南打的對,打的好,如果一個孩子邊沒人照應,指不定要怎麼欺負。
兩名男列車員把傷口止住的男人架出包間,靳南道:“這種人渣,要麼下車滾蛋,要麼我看他一次打他一次。”
列車員安道:“您冷靜一下,現在您朋友需要您的陪伴,距離列車停靠下一站還有三個小時,我們會跟當地的相關機關取得聯繫,一定會依法理。”
另一名列車員進包廂裡面,把屬於男人的行李和品全部清空,讓旅客們各自回去睡覺,儘量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免得對整列車的行程產生不必要的延誤。
包廂地板上的已經被人用紙巾乾淨了,靳南不喜歡別人看熱鬧一般的看著岑青禾,所以拉著進了包廂,順手把門合上。
聽到外面腳步聲漸遠,岑青禾這才鬆了口氣,“嚯,嚇死我了,我好怕他們跟你較真兒,說你把人打那樣,要你負責任。”
靳南坐在牀邊,一言不發。
岑青禾不由得打量他的臉,輕聲問:“怎麼了?”
靳南結微,似是經過了很大的心裡掙扎,這才薄脣開啓,沉聲問:“他沒怎麼你吧?”
岑青禾一臉天真無邪,低聲音回道:“他就是抓了我胳膊一下,我剛一喊你就衝進來了,劈頭蓋臉給他一頓揍,剛開始我還覺得他欠揍,但他真的沒把我怎麼著,你打得他滿臉是,我就怕他反咬你一口,幸好他已經不會說話了,我希他認命,老老實實下車,別再找麻煩。”
靳南端詳臉上的細微表,半信半疑,“真的?”
岑青禾就差拍著脯保證,“我是那種能吃虧的人嗎?你都說我囂張跋扈了,如果他真敢我,沒等你進來,我估計他已經見了。”
雖說如此,可靳南心底還是懊惱,他不是個特別會表達的人,所以話一出口,變作,“都說了不用你陪我坐火車。”
這滿是負面緒的聲音,一般人聽見一準心裡不好,好像誰倒似的。但岑青禾就是莫名的get到靳南的意思,並且毫不覺得他這話有任何不妥。
坐在他對面的沙發上,大咧咧的勸道:“哎呀,別生氣了,這不沒什麼事兒嘛,活久見活久見,都長這麼大了,還能不遇見幾個變態猥瑣男嗎?”
靳南不吭聲,一張俊臉臭得要命,不知道的還以爲剛纔被打得頭破流的人是他。
岑青禾看著他的臉,故意逗道:“我不會跟紹城說的,這事兒就當沒發生過,怎麼樣?”
“我……”
他不是怕商紹城怎麼想,他自己擔心,自己憋氣不行嗎?
但是話到邊,靳南忍住了。
岑青禾鮮看他這副言又止,話都已經說出口,但卻說一半的樣子,畢竟他都是不怎麼開口的人。
擡手拍了下他的膝蓋,岑青禾衝他一揚下,低聲道:“你看,現在變態走了,這包廂清淨了,咱倆聊天聊天,打牌打牌,多好?”
靳南跟生不起氣來,原本一口氣已經頂到口,可看這副沒心沒肺的樣子,他只能默默地吞回去,一片驚濤駭浪,最終愣是被他控制到無波也無瀾。
“怕不怕?”他輕聲問,一不小心語氣就帶著幾分外泄的溫。
好在岑青禾沒察覺,如常回道:“不怕,我還覺得刺激呢,出門在外,一路波瀾不驚的算什麼?”
靳南這種人,都忍不住給了一記白眼,岑青禾咯咯笑著,心大的說道:“那人也真夠倒黴的,看個片被打得頭破流,我都怕他以後產生心理影,一著看片就頭疼。”
靳南問:“你還敢在這邊睡覺?”
岑青禾不假思索的回道:“敢啊,不是有你在嘛。”
靳南心底起一奇妙的波瀾,他很難形容那是怎樣的一種覺,類似溫暖,但明明是他保護,後來很久之後,他一個人琢磨才明白,估計那是一種被需要的吧。
他努力剋制著不去放縱,不去喜歡,但他不能否認,他想保護,哪怕是以朋友的份,以睡在隔壁旅伴的份,無論哪一種都好,他可以不跟在一起,但他希一直都是現在的樣子,時而跋扈,時而需要人保護。
猜你喜歡
-
完結88 章

狙擊蝴蝶
李霧高考結束后,岑矜去他寢室幫忙收拾行李。 如果不是無意打開他抽屜,她都不知道自己曾丟失過一張兩寸照片。 - 所謂狙擊,就是埋伏在隱蔽處伺機襲擊。 ——在擁有與她共同醒來的清晨前,他曾忍受過隱秘而漫長的午夜。 破繭成蝶離異女與成長型窮少年的故事 男主是女主資助的貧困生/姐弟戀,年齡差大
27.7萬字8 8157 -
完結521 章

錯惹惡魔總裁
洞房對象竟不是新郎,這屈辱的新婚夜,還被拍成視頻上了頭條?!那男人,費盡心思讓她不堪……更甚,強拿她當個長期私寵,享受她的哀哭求饒!難道她這愛戀要注定以血收場?NO,NO!單憑那次窺視,她足以將這惡魔馴成隻溫順的綿羊。
141.7萬字8 14730 -
完結169 章

盛寵之權少放過我
她千不該萬不該就是楚秦的未婚妻,才會招惹到那個令人躲避不及的榮璟。從而引發一系列打擊報復到最后被她吃的死死的故事。
45.5萬字8 11480 -
完結779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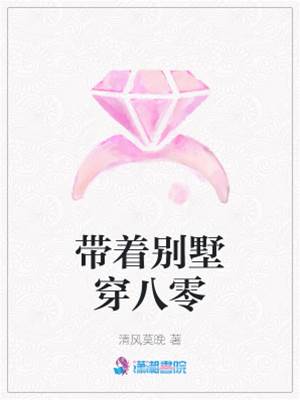
帶著別墅穿八零
二十一世紀的蘇舒剛繼承億萬遺產,一睜眼穿成了1977年軟弱可欺的蘇舒。在這個缺衣少食的年代,好在她的大別墅和財產也跟著穿來了。然后她就多了個軟包子媽和小堂妹要養。親戚不懷好意上門說親,想讓她嫁給二婚老男人,一進門就給人當后娘。**梁振國退役轉業后,把戰友的兩個遺孤認養在名下,為了更好的照顧兩個孩子,他想給孩子找一個新媽。人人都說鎮上的蘇舒,膽子小,沒主見,心地善良是個好拿捏的,梁振國打算見一見。**為了帶堂妹逃離老家,蘇舒看上了長得高大英俊,工作穩定的梁振國。一個一帶二,一個一帶一,正好,誰也別嫌棄誰...
60.8萬字8 59526 -
完結394 章

千億前妻帶崽歸來,馬甲藏不住了
江司妤和薄時宴協議結婚,做夠99次就離婚。 在最后一次情到深處的時候,江司妤想給男人生個孩子,不料男人記著次數,直接拿出離婚協議書。 江司妤愣住,回想結婚這三年,她對他百依百順,卻還是融化不了他這顆寒冰。 好,反正也享受過了,離就離。 男人上了年紀身體可就不行了,留給白月光也不是不行! 江司妤選擇凈身出戶,直接消失不見。 五年后,她帶崽霸氣歸來,馬甲掉了一地,男人將人堵在床上,“薄家十代單傳,謝謝老婆贈與我的龍鳳胎..”江司好不太理解,薄總這是幾個意思呢?
72.4萬字8 5900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