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零嫁男主》 第69章 落幕
曲立黨青黑著臉出來, 回頭了一眼公安局大門,咬牙暗恨。
這些人如此可惡,見他即將失勢就翻臉無,一點面子都不給。
那他還非要做這件事不可, 好他們都看看, 他曲立黨仍舊是屹立不倒!
憋著這氣,曲立黨憤憤離開。
回到家, 許虹母得知撈人失敗, 頓時失不已, 哭嚎連天。
“兒啊兒,媽沒用,你姐也沒用, 救不出你呀,想到你要苦, 媽就不想活了,讓我死了吧,別拉我別拉我……”
許虹趕忙把人拉住,“媽, 你死了我怎麼辦,弟弟還要救啊,你不能死, 立黨肯定有辦法。”轉頭期待地看向曲立黨。
曲立黨冷眼瞧著們母演,直到此刻消停了才終于開口道:“有嚎的功夫,不如先跟我說說許強跟著混的那幫人。”
公安局那邊沒法再手,那就只能試試另一個方向。
他曲立黨還沒倒, 他不信解決不了眼下這區區一件小事。
許虹母不清楚他的心思, 只以為他真的在為許強打算, 連忙將知道的況都倒的一干二凈,不敢有任何瞞。
曲立黨從中剝繭,敏銳地拉出一個關鍵人來。
那個被許強拜了碼頭的大哥或許可以一見,這次被抓的可不止許強等一眾小角,其中還有個所謂的‘二哥’呢。
如果許強份量不夠,那這個‘二哥’應該可以打對方幫忙的吧。
曲立黨想到這點,當下便出去打聽那人的消息。
他以前的關系并不是全沒了,只是上面的路打不通而已,下面三教九流的還有,只要他當著革命委主任一天,下邊有的是小蝦小魚搶著來依附結他。
但這里面并不包括許強加的那個團伙大哥,人家在曲立黨打聽到他的時候就已經收到消息,靜等著他送上門呢。
Advertisement
曲立黨并不知道,所以從自己以往看不上眼的雜魚手里得到想要的信息后,還回家準備了一下,最后才帶著禮面面地前去拜訪。
擱以前,一個混混團伙的老大,本不值當他費這個功夫,但現在他即便不想承認,也清楚自己的力量已經沒有那麼大了,不好好收拾準備一番,人家不一定給他面子。
昔日威風八面鼻孔朝天的革命委主任登門,團伙老大以及眾多小弟可是稀奇的不行,一個個跟看猴戲似的出來圍觀。
曲立黨在無數雙眼睛下落座,心中倍難堪,但他是有所求,目的還沒達,自然不能撂臉子離開,還要好聲好氣地和團伙大哥寒暄,然后道明來意。
團伙大哥看夠了他的低頭俯首姿態,才嘆口氣慢悠悠開口道:“按說曲兄弟親自上門來說這事兒,咱怎麼也得幫把手,但……”
他面為難地看向曲立黨,言又止。
曲立黨心里咯噔一下,面上不聲地試探:“是有什麼難嗎?”
團伙大哥好似就等他這句話,抱怨道最近上頭開始收風口怎麼怎麼樣,他不好隨便冒頭啊,沒看他連自己的拜把子二弟都沒敢撈,哪里還顧得上管一條小雜魚。
曲立黨拿別人當雜魚,現在人家也拿他小舅子當小雜魚,跟在他臉上咣咣砸一樣,是在明晃晃打他的臉。
偏偏他還不能為此生氣,只當沒聽出來對方的譏諷之意。
團伙大哥上說是難辦,好像沒有一點辦法似的,但他表現出來的悠閑姿態可不是這麼個意思。
那態度,那架勢,分明是想看看曲立黨的誠意。
如果誠意足夠,一切好商量。
但若是誠意不行,那曲立黨今天想要囫圇出去,恐怕不會那麼容易,起碼也得被刮掉一層皮吧。
不然當他們總堂會是這麼好來的?
團伙大哥及其手下們沒有遮掩這層意思,幾乎是明明白白地給曲立黨,等著看他表現。
曲立黨來時便預料到這一趟不好走,所以他早有準備,想與一群豺狼打道,不提前備點怎麼行。
他將帶來的手提箱遞上,“小小禮,不敬意。”
話是這樣說,但看他那副自信的樣子,手提箱里面裝的肯定是好東西,所以他才篤定團伙大哥看了會滿意。
團伙大哥瞧了他一眼,旁邊立馬有手下將箱子接過去打開。
不大的手提箱里塞著布團,中間位置躺著個華斂且充滿歷史厚重的件。
“古董?”
團伙大哥有點眼力見,手里也不是沒有些好東西,一下便看出這玩意不簡單。
曲立黨知道禮送對了,矜傲一笑點頭道:“是,宋朝的,想來應該能請得起大當家出手吧。”
看剛才團伙老大眼睛冒的架勢,他以為這次想談的事八九不離十了,卻低估了某些人的貪婪之心。
“就這?”團伙老大拿起那件看了看,撇撇隨手扔到桌子上,像是不太滿意。
曲立黨看得心頭發慌,下一刻便聽對方哈哈笑著說:“既然曲老弟有好東西,當然得讓哥哥看個遍才好從中選出最得意的啊,要不哥哥晚上去你家一頓,正好看看你都有啥寶貝。嘿嘿,曲老弟你說行不?”
話是問曲立黨,但他知道他們并沒有給他更多的選擇,他若是想順利離開,除了答應沒有第二條路走。
曲立黨此時有些后悔,不該因為一時之氣而試圖與虎謀皮,結果目的還沒達到,他先財被對方盯上了。
可事走到這一步,已經容不得他后悔,只能著頭皮繼續往下走,走一步算一步,憑他的能力,他不信最后不能反制為主。
如果他將這些人收攬在手心,想辦什麼事不,到時他即便做不革命委主任,也沒人敢惹他。
曲立黨這樣暢想著安自己,被團伙大哥扣在這里大半天,直到天晚夜幕降臨,他才被放出來,帶路去自己家。
許虹和媽還在家焦灼等待,看到曲立黨回來立馬迫不及待地湊上來問結果。
曲立黨趕們去置辦酒菜,他要招待貴客。
“都啥時候了,還置辦什麼酒菜招待什麼貴客!”許媽不滿大罵,抬頭卻對上團伙大哥兇戾的眼神,頓時嚇得一哆嗦。
曲立黨嫌棄地推開,介紹說:“這是我請來幫忙撈許強的人,你們不幫忙招待就算了,也別把人得罪了。”
許媽一聽是找來救兒子的,再看團伙大哥立刻不覺得他兇戾不是好人了,能救兒子,他就是個大好人啊。
許媽跟看到菩薩似的,立即跑去張羅酒菜。
曲二嬸嫌們煩,去了閨家不在,現在家里就只有兩個人,許媽去忙活后,團伙大哥的視線便落到許虹上。
許虹被他兇戾的氣勢嚇到,本能地后退一步。
團伙大哥一見,呲牙笑了,指著許虹對曲立黨說:“這是你媳婦?待會兒吃酒讓也上桌,陪咱哥倆喝兩杯。”
這個時候風氣還很保守,一般家里男人喝酒,人是不上桌的,除非……
許虹聽了臉一變,連連后退想躲,卻被團伙大哥一把揪住扯過去,哈哈大笑著的臉。
曲立黨看得臉都青了,趕上前阻攔道:“大哥您別,懷孕了,胎相還不穩,怕是不能喝酒,我陪您喝,喝完給您看多多的寶貝。”
團伙大哥這才松開手,掃興道:“只是讓上桌助個興,又沒想做啥,瞧把你急的,算了,不愿意也罷,哥哥走還不。”說著人轉準備離開,看架勢真的要走。
曲立黨這下也顧不上維護媳婦了,一邊忙著攔住人,一邊示意許虹趕快答應下來。
不就是賠個桌敬杯酒嘛,又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矯個啥,這可是為了救弟弟,他都要為此出一大波,還想當什麼貞潔烈婦!
許虹委屈,許虹不肯。
但是曲立黨干脆出了許媽,許媽得知后果斷替應下了。
許虹便也只能別別扭扭半推半就上桌陪客,雖然趁機吃了不好菜,但也被強著勸著灌了不酒,最后什麼時候趴在桌上失去意識的都不知道。
曲立黨沒管,拿出幾樣寶貝給團伙大哥賞玩,兩人的作被燈映照在許虹后的墻壁上,像是張牙舞爪的怪。
第二天許虹醒來頭疼裂,肚子也不舒服,但好消息是弟弟的事終于有辦法解決了。
許媽和都很歡喜,卻發現曲立黨一點高興的意思都沒有,好像誰欠了他八百萬一樣。
曲立黨痛失不暗中在那些年收斂的寶貝,他能高興起來才怪,幸好把這件事解決后,他曲主任的威勢肯定能穩一穩,鎮一鎮那些看不起他的家伙們,也算有舍有得了。
而拿到他寶貝的團伙大哥還算言而有信,回去放好東西后徑直往公安局走了一趟。
他并沒有尋那些警察什麼的,試圖拉關系走后門,而是直接提出探拜把子二弟,然后和他聊上一會兒,事迅速有了轉機。
衛誠和汪小舅這邊的團隊隨之接到公安局的消息,說‘二哥’招認并一力擔下了所有責任,最后極有可能只有他被嚴刑發落,其他人則最多被拘留關上一段時間,并不會有太嚴重的刑罰。
汪小舅:“…………”
他娘的還能這樣的?!
他們忙活一場,人家這樣一搞,好像他們都白費功夫了。
衛誠搖頭:“不算白忙活,起碼送進去一個頭目,沒了他,其他人就是一盤散沙,以后不會再有什麼威脅。”
汪小舅跺腳,“我知道,可就是憋氣啊,眼看都要把一群人全送進去了,結果突然給咱來這麼一出,真的大丈夫?覺他們不講武德!”
衛誠倒是沒多大意外,剛才就說了,那個二哥算是這幫人的頭目,平時胡作非為都是由他帶頭,他這時候如果敢一力承擔所有責任,是能夠將其他人都撇清,只法判他一個的。
他對此有所預料,但猜測幾率不大,沒想到還真發生了。
這后面若是沒人推,他可不信。
衛誠思及那人‘二哥’的稱呼,大概能猜到背后出主意的人是誰。
但對方鉆的是律法空子,走的門路也讓人挑不出病,他們想借此將他扯出來不大可能。
他沒忘記,打散那伙游的街頭霸王才是他們此次的主要目的。
現在目的已經達到,而那個‘大哥’也不溜手,他們沒必要貿然招惹上對方。
就是可能會讓樂喜失了。
樂喜得知后確實有一點點失,沒想到都到這個份上了,還能讓許強給逃過一劫。
該說不愧是主弟弟嗎?上是不是有主環的庇護啊,這樣都能沒事。
幾天后,隨著主要人認罪伏法,這件事迅速落下帷幕。
結果不出所料,被抓的人里只有‘二哥’需要承擔刑事責任,被重判了十年,其他人都是民事責任,分別被拘留警告教育等等,還有需要給苦主家屬們大筆的賠償。
那些家屬見主要人坐牢,沒坐牢的又賠了他們不錢,對此已是很滿意了,自然不會再追究什麼。
事定局,汪小舅他們明白這樣已經是極限,再揪著不放反而會顯得他們是鬧事的,于是便招呼大伙收了手。
然后等許強他們出來時,他帶著朋友暗中將人挨個胖揍一頓,警告以后再在街上看到他們這群人,必定見一個打一個,見一次打一次,說到做到。
許強起初還想報警求助,妄想也把汪小舅等人抓進去蹲幾天。
可他在警察那里才留了案底,人警察本不鳥他,或者隨便將他應付走,懶得為他這點蒜皮的小事浪費力氣,他報了也沒什麼用。
許強氣得肝疼,不信邪地到街上晃悠一圈,轉頭又被摁住打一場,才徹底服了,滾回家老實養傷。
猜你喜歡
-
完結890 章

蛇仙相公慢慢來
一場重病,讓我懷胎十月,孩子他爹是條蛇:東北出馬仙,一個女弟馬的真實故事……
202.3萬字7.67 80747 -
完結834 章

寵婚蜜愛:傅先生他又想娶我了!
結婚兩年,兩人卻一直形同陌路。他說:「一年後,你如果沒能懷孕,也不能讓我心甘情願的和你生孩子,那好聚好散。」她心灰意冷,一紙離婚協議欲將結束時,他卻霸佔著她不肯放手了!!
77.3萬字8 94329 -
完結267 章

被渣後小叔叔寵我入骨
那一夜,淩三爺失身給神秘的女人,她隻留下兩塊五和一根蔫黃瓜,從此杳無音訊……被養母安排跟普信男相親的栗小寒,被一個又野又颯的帥哥英雄救美,最妙的是,他還是前男友的小叔叔。想到渣男賤女發現自己成了他們小嬸嬸時的表情,她興高采烈的進了民政局。結果領證之後,男人現出霸道本性,夜夜煎炒烹炸,讓她腰酸腿軟,直呼吃不消!
73.5萬字8 32067 -
完結183 章

成蝶
分手多年後,路汐沒想到還能遇見容伽禮,直到因爲一次電影邀約,她意外回到了當年的島嶼,竟與他重逢。 男人一身西裝冷到極致,依舊高高在上,如神明淡睨凡塵,觸及到她的眼神,陌生至極。 路汐抿了抿脣,垂眼與他擦肩而過。 下一秒,容伽禮突然當衆喊她名字:“路汐” 全場愣住了。 有好事者問:“兩位認識” 路汐正想說不認識,卻聽容伽禮漫不經心回:“拋棄我的前女友。” - 所有人都以爲容伽禮這樣站在權貴圈頂端的大佬,對舊日情人定然不會再回頭看一眼。 路汐也這麼以爲,將心思藏得嚴嚴實實,不敢肖想他分毫。 直到圈內人無意中爆出,從不對外開放的私人珠寶展,今年佔據最中央的是一頂精緻又瑰麗的蝴蝶星雲皇冠。 據傳出自商界大佬容伽禮之手,於他意義非凡。 好友調侃地問:“這麼珍貴的東西,有主人了嗎?” 容伽禮不置可否。 殊不知。 在路汐拿到影后獎盃當晚,滿廳賓客都在爲她慶祝時,她卻被抓住,抵在無人知曉的黑暗角落處。 路汐無處可躲,終於忍不住問:“容伽禮,你究竟想幹什麼?” 容伽禮似笑非笑,語調暗含警告:“你以爲……回來了還能輕易躲得掉?” 路汐錯愕間,下一秒,男人卻將親手設計的皇冠從容的戴在路汐發間,在她耳畔呢喃:“你是唯一的主人。” ——在廣袤的宇宙空間,蝴蝶星雲終將走到生命盡頭,而我給你的一切,比宇宙璀璨,亙古不散。
27.2萬字8.18 5293 -
完結206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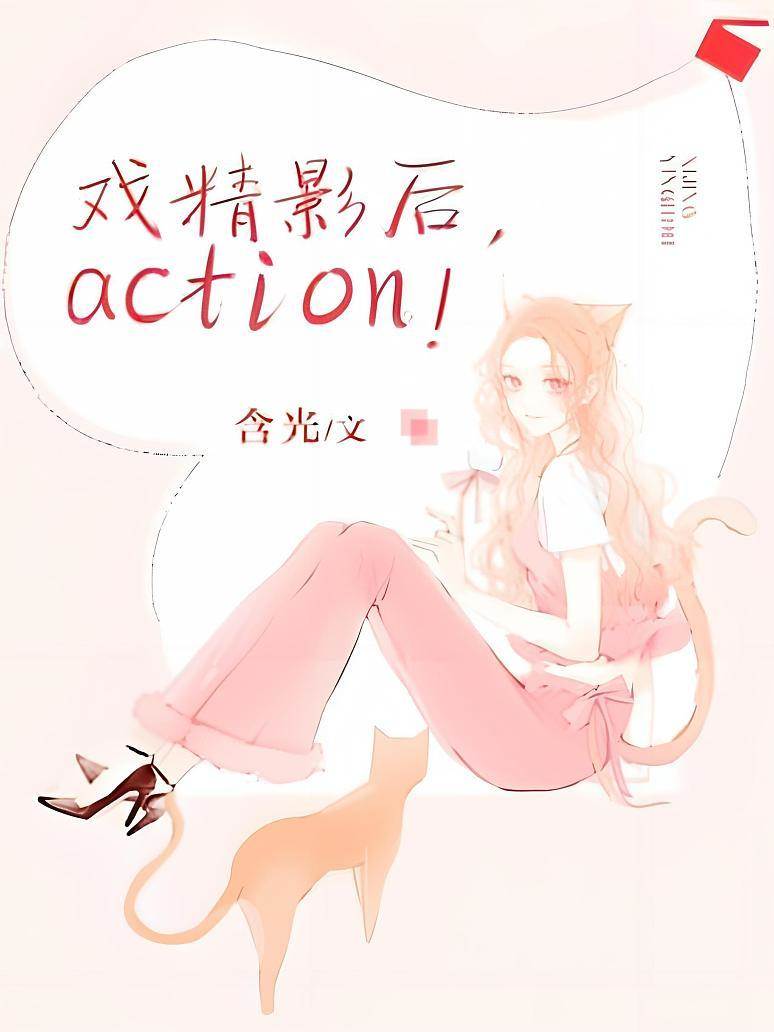
戲精影后,action!
影后楚瑤瑤被人害死一命嗚呼,醒來后已經是20年后,她成了臭名昭著的十八線女明星。 渣男渣女要封殺她?小助理要踩她上位?家里重男輕女要吸干她?網友組團來黑她? 最可怕的是身材走樣,面目全非! 影后手握星際紅包群,這些全都不是問題。星際娛樂圈大佬們天天發紅包,作為影后迷弟迷妹只求影后指導演技。 第一步減肥變美。 第二步演戲走紅。 第三步虐渣打臉。 第四步談個戀愛也不錯……隔壁的影帝,考不考慮談個戀愛?
40.3萬字8 196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