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人間妄想》 第21章要走私人關系嗎
尉遲出聲:“怎麼會來公司找我?”
鳶也道:“我這次是代表高橋來的。”
“談合作?”
“對。”
尉遲猜得到是為了哪個合作來的,那塊地皮是要招商了,雖然還沒有正式對外公布,不過想要功就得快人一步,高橋有強大的消息網,能最先得到這個消息也實屬正常。
只是……尉遲黑眸深邃,幽幽地看著:“走私人關系?”
他聲線沒什麼起伏,但“私人”兩個字從他里說出來,就多了幾分像云一樣,抓不住又明晃晃的曖昧。
昨晚浴缸里的水從腦海里漾而過,鳶也耳燥紅,一時不敢直視他的眼睛,又不甘愿認輸,邦邦地回:“不行嗎?”
尉遲起朝的方向走去,悉的男氣息近,鳶也背脊微僵,結果他徑直從的側經過,只留下輕輕的一句:“怎麼會不行?”
尚在心猿意馬,他已經擺出了要談正事的態度。
鳶也不想在他面前怯,忙整理起思緒,轉在他面前的椅子上坐下,從包里拿出一份文件,往前一遞:“這是我草擬出來的方案,你先看一下,我認為我們高橋是尉氏最好的合作對象。”
尉遲拿起手機想查東西,看見右下角的信息有一條未讀,順手點開,本以為是垃圾消息,不曾想卻是幾張照片。
看著,他的眸清寒了許多,復而抬起頭,凝視著鳶也。
臉頰上在寧城的傷已經好了,所以只上淡妝也看不見任何瑕疵,眼皮上畫了金橘的眼影,既不妖也不清寡,干凈通,從一側打過來,照出鼻尖細細的絨,不乏幾分可,但是他目下移,落在的襯衫上。
“你早上出門好像不是穿這件服,換了?”
Advertisement
“啊?是啊。”鳶也沒想到他還記得早上
穿什麼。
雖然都是白襯,但細節還是有差別,原來那件是蕾領加小系帶,而這件是一個荷葉領加小系帶。
倒也不是故意選一件元素差不多的,巧而已,但在旁人看來,都換了服卻還選款式差不多的,不是蓋彌彰是什麼?
尉遲放下手機,眸子霧沉沉:“為什麼換服?”
鳶也說:“原來那件不小心弄臟了。”
“怎麼弄臟的?”他又問。
“咖啡漬。”
尉遲眼里有一深究:“自己去買的服?”
聽到這里,鳶也覺出他語氣里的微妙,心下莫名,又覺不太舒服,不由得反問:“不然呢?”
將文件遞出去后,手還在桌子上沒有收回來,聽出語氣里的不耐,尉遲忽然抓住的手腕,猛地將拉到自己面前:“我以為你是個聰明人,知道什麼該做,什麼不該做的。”
鳶也眉心一跳,倏地抬起眼皮對上他的眼睛,他的聲音平緩,但這份平和下卻有一沉:“我高估你了麼?”
他的意思非常明白,幾乎就是把“我都警告過你了你竟然還敢這樣做”這句話砸在鳶也的腦門上。
鳶也愣怔,第一反應是記起他曾警告不準再去找白清卿,不準再去春路14號打擾那對母子的生活的事。
的手腕被他抓住,不得不傾在辦公桌上,鳶也抿道:“那次之后我就再沒有去找過白清卿。”又沒有忤逆他的意思,好端端的擺臉干什麼?
“所以你昨天去醫院做什麼?”
果然是因為白清卿來質問?鳶也想起小金庫里那番“真論”,臉也冷了下來:“去醫院當然是去看醫生,否則你以為我去做什麼?砸白清卿幾百萬讓離你遠點嗎?”
就只見過白清卿一次,那一次白清
卿就拿演了一出戲,十足十的白蓮花,尉遲很會將舊事重提,突然又追究起這件事,難不是那朵蓮花又開了?
真是人在家中坐,鍋從天上來。
鳶也沒好氣道:“麻煩你轉告白小姐,看些瑪麗蘇電視劇,這種劇編得出來,我還懶得做呢。”
尉遲眼神黑沉銳利,薄微抿。
他很會將自己的緒外,反正鳶也和他結婚這兩年,只在最近見過幾次他不高興,而且都是和白清卿有關。
第一次是發現去春路找白清卿。
第二次是現在,也是因為白清卿。
鳶也口發悶,郁氣翻涌,想再鄭重聲明自己沒去找過白清卿,但看到他的臉,忽然又覺得沒意思極了,火氣一熄,換一句嘲諷:“真當誰都稀罕稀罕的東西似的。”
此話一出,有沒有殺敵一千不知道,反正是被傷了一千二,有什麼尖銳的東西藏在郁氣下刺著,鼻尖有酸意涌上。
兩人之間沉默了有足足十五分鐘。
直到線電話“嘀”的一聲響起。
尉遲按下接通。
“尉總,會議時間到了。”黎雪的聲音。
尉遲淡淡道:“好。”
然后就起,不看鳶也一眼,直接出了辦公室。
鳶也呼出口氣,本是想減窒悶,結果腹部作痛,極不舒服,轉倒了杯水喝下,還是不好,又吸到一平時在尉遲上聞到的味道,眼睛也有些酸了。
好好的來找他談合作,他偏要跟提白清卿……這就是傳說中的孽力回饋吧?公私不分走后門,他就在談正事的事提那個人。
鳶也盯著尉遲的座椅,咬牙切齒地說:“尉遲你這個混蛋,等你沒錢了,我就砸你幾百萬讓你離我遠點。”
但想到尉氏的規模和這幾年不斷攀升的市值,這個夢想
可能有點不切實際,改口:“算了,還是先等我攢夠幾百萬吧。”
躲在里間聽了一場夫妻吵架的秦自白,沒忍住“噗”的一聲笑了,還好聲音不大,沒讓外面的鳶也聽見,他打開一條門,剛好看到鳶也離開辦公室的背影。
才說認識尉遲十幾年沒見過他生氣,這不就惱了嗎?只是不知道,他究竟是為什麼生氣?
為白清卿母子?未必吧。
知道尉遲四年前那件舊事的秦自白揚起角,只覺得這件事有意思的。
鳶也出了尉氏大廈,本想回高橋,包里的手機突然響起。
腳步一頓,拿出手機一看,竟然是表姐……不是宋鴦錦,而是的親表姐,舅舅的兒,從小跟十分要好的陳桑夏。
“鳶鳶,在忙嗎?”陳桑夏爽朗的聲音從聽筒里傳耳,頓時驅散了鳶也在尉遲那里的氣。
“沒有呢。”
“那正好,我來晉城公干,剛忙完,有兩個小時自由活的時間,我們可以見一面。”
鳶也笑著說:“好啊,你在哪呢?我過去找你。”
“嗯,我把地址發給你。”
鳶也得了地址,馬上就了車過去。
算起來,和陳桑夏有兩年沒見面了,不是不想見,而是陳桑夏一年到頭都在海上飄著,很難有假期。
趕到約定地方,鳶也遠遠就看到陳桑夏在清吧門口等,便三步做兩步撲過去,一把將抱住:“好久不見啊!”
陳桑夏笑著回抱:“是啊,所以一有機會就馬上聯系你。”
鳶也發現竟然把頭發剃了斷寸,詫異極了,不捧著的臉仔細看起來。
“陳桑夏”這個名字聽起來婉約,其實本人從小就是個假小子,這些年在海上風吹日曬,皮黑了好幾個度,襯得相貌愈發英氣。
鳶也贊嘆:“帥哦…
…”
陳桑夏了自己的小刺頭,洋洋得意:“是吧?我也覺得,但是大哥讓我沒把頭發留出來之前別回家。”
的大哥,也是鳶也的大表哥,鳶也笑說:“大表哥一向心,沒準現在就在家里盼著你回去呢。”
說笑了兩句,就一起進了清吧,點了幾杯飲品,伴著輕音樂,邊喝邊聊。
從海上的趣事聊到小時候的糗事,從遇到的奇葩客戶到老板同事的奇葩好,許久未見,隨便一個話題都能聊得捧腹大笑。
但笑著笑著,陳桑夏忽然說:“我總覺得你好像不太開心?”
角笑意一滯,鳶也拿起一杯葡萄紫的酒搖了搖,沒有喝,反過來鄙視:“你個常年斷網的2G懂什麼?現在就流行憂郁神,我是跟流,樹立人設。”
陳桑夏側頭看著:“可是我就是覺得,小時候的你才是真開心。”
“你都說那是小時候的事了。”鳶也淡笑。
人是會長大的,也是會變的。
陳桑夏喝了口酒,說:“我還記得四年前,你到青城找我們,讓我們收留你,還不讓大哥和家里知道,那副失魂落魄的模樣,可把我們嚇壞了,從那之后,你就越來越不一樣了。”
四年前麼……鳶也微微瞇起眼睛,盯住那盞璀璨的水晶燈,想起來了,那時候得知媽媽真正的死因,承不住,就買了張機票飛去青城找陳桑夏和小表哥,住了快一年才回晉城。
大概是那段記憶太痛苦,才過去四年,就已經有些模糊不清。
鳶也苦笑著搖搖頭,也不愿深思,畢竟不是誰都能承得住,“爸爸殺了媽媽”這種荒誕又殘酷的真相。
手忽然被握住,鳶也抬起頭,對上陳桑夏關切的目:“我一直想問你,你當初怎麼會突然決定嫁進尉家?”
(本章完)
猜你喜歡
-
完結2579 章
蝕骨危情:爹地,媽咪又跑了
被親人設計陷害,替罪入牢,葉如兮一夕之間成了人人喊打的過街老鼠。監獄產子,骨肉分離,繼妹帶走孩子,頂替身份成了謝總的未婚妻。六年監獄,葉如兮恨,恨不得吃血扒肉。一朝出獄,她發現繼妹和謝總的兒子竟和自己的女兒長得一模一樣……在眾人眼中不解風情,冷漠至極的謝總某一天宣佈退婚,將神秘女人壁咚在角落裡。葉如兮掙紮低喘:“謝總,請你自重!”謝池鋮勾唇輕笑,聲音暗啞:“乖,這一次冇找錯人。”一男一女兩個萌娃:“爹地,媽咪帶著小寶寶離家出走啦!”
230.7萬字7.35 475716 -
完結787 章

閃婚密愛:我的老公是大佬
童年沒有想到自己有一天會成為總裁夫人,更不會想到這位總裁竟然是自己上司的上司。幸虧她只是個小職員,跟這位總裁沒什麼交集。要不然她跟總裁隱婚的消息遲早得露餡。不過童年想方設法的隱瞞自己的婚史,總裁倒是想方設法的證明自己結婚的事實。 “當初不是說好了對外隱婚,你巴不得讓全世界的人知道是怎麼回事?”面對童年的掐腰質問,許錦城戴上耳機看文件假裝聽不到。反正證已經領到手了,童年現在想反悔也沒用了。某人露出了深不可測的笑容。
100.6萬字8 34339 -
完結128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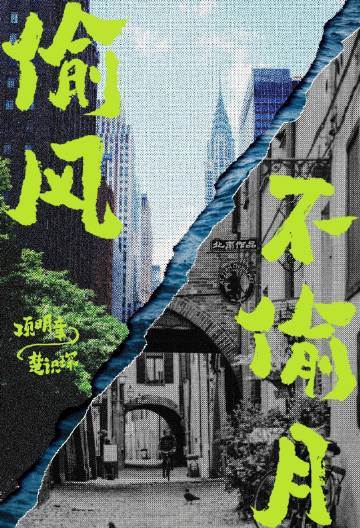
偷風不偷月
穿越(身穿),he,1v11945年春,沈若臻秘密送出最后一批抗幣,關閉復華銀行,卻在進行安全轉移時遭遇海難在徹底失去意識之前,他以為自己必死無疑……后來他聽見有人在身邊說話,貌似念了一對挽聯。沈若臻睜開眼躺在21世紀的高級病房,床邊立著一…
39.3萬字8 6359 -
完結511 章

大院嬌妻純又欲,高冷硬漢破戒了
軍婚+先婚后愛一睜眼,溫淺穿成了八十年代小軍嫂。原主名聲壞、人緣差,在家屬院作天作地、人嫌狗厭,夫妻感情冷若冰山。開局就是一手爛牌!溫淺表示拿到爛牌不要慌,看她如何將一手爛牌打得精彩絕倫,做生意、拿訂單、開工廠、上大學、買房投資等升值,文工團里當大腕,一步步從聲名狼藉的小媳婦變成納稅大戶,憑著自己的一雙手打下一片天。——周時凜,全軍最強飛行員,他不喜歡這個算計了自己的妻子,不喜歡她年紀小,更不喜歡她長得嬌。初見紅顏都是禍水!后來媳婦只能禍害我!
94.6萬字8.18 10882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