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日提燈》 第83章 前行
晏柯的目轉向白散行,被束縛在姜艾后的白散行恨恨地了姜艾一眼,再與晏柯對上目,冷笑道:“怎麼,你難道還覺得老子會替你保守不?你自己是賀思慕的殺父仇人,還道貌岸然地站在那邊,騙殺我這個唯一的知者,賀思慕知道了不把你挫骨揚灰才怪。”
姜艾笑著向晏柯走近幾步,羅搖曳,悠悠道:“晏大人之前那麼張,原來不是怕白散行去找你,而是怕王上見到白散行會知道當年的真相啊。我真是覺得奇怪,你借白散行的勢力除掉了前鬼王,又借思慕的手除掉了白散行,稱王之路上不就剩思慕這一個絆腳石了麼?怎麼這麼多年安安分分當個右丞,果真就不再想那王座了?”
靠近晏柯,手放在邊,小聲說:“前鬾鬼殿主,那可憐孩子背后是你罷,右丞?你想要思慕的鬼王燈,對不對?”
晏柯冷著臉著姜艾,一言不發,眼里的芒閃爍。
姜艾掩而笑后退幾步,笑得風萬種花枝,道:“右丞有這麼大一個把柄在我手里,居然還敢來質問我?白散行他日做了指正你的證人,思慕還要謝我呢。”
“你想要什麼?”
“我想要什麼?你知道我對王座毫無興趣,這王座上是你還是思慕對我本沒區別。不過晏大人,我看你可憐多說幾句,你又想要王座又想要思慕,可別太貪心。”姜艾退到白散行邊,眼里含了幾分冷意:“世上并無雙全法,你總要和思慕撕破臉。若他日你為王,可別忘了今日我幫你瞞。”
手指向大門,做了個請的姿勢。晏柯看了片刻,冷笑著消失在煙霧之中。
姜艾的笑意淡下去,確認晏柯的氣息完全消失后,解開了白散行的束縛對他說了句:“演得不錯啊。”
Advertisement
白散行似乎有些憤憤不平。
然后走向院子后的房間,把房門打開。房門后赫然是一座華麗的翡翠鑲金屏風,屏風上施加了數道匿法咒,有個子端坐在屏風之后捧著一卷書看著,腰間的燈發著幽幽藍。
姜艾道:“王上,他承認了。”
賀思慕合上鬼冊,抬起眼睛穿過屏風雕鏤的隙看向姜艾,道:“嗯,我聽到了。”
姜艾沉默了片刻,還是忍不住問道:“思慕……王上,前鬼王的事,你是什麼時候知道的?”
“猜得七七八八。”賀思慕的手指在鬼冊上漫不經心地敲著,道:“我爹不會殉,能害他的人不多。白散行雖然囂張叛逆但是不屑于趁人之危,當時我爹沉溺于亡妻之痛,他不應當挑這個時候對我爹下手。況且若是他做的,早就昭告天下了,怎會用殉這個幌子。”
“那晏柯……”
“晏柯是怎麼死的,你知道麼?”
姜艾愣了愣,搖搖頭。
“他是皇子,封王,造反,被抓,逃跑,再舉兵,再被打敗。起起伏伏三次后,終被車裂棄尸于市。”賀思慕翻著鬼冊,淡淡道:“他的執念是權力,是為至高無上天下之主,怎麼可能屈居人下。”
那些遙遠的過去或許晏柯自己都已經記不清了,但是鬼冊上記得明明白白,鬼冊上記載的都是些不會消失和改變的東西。賀思慕時常翻著那記載著所有惡鬼生平和弱點的鬼冊,枯黃的紙頁告訴,邊這些惡鬼的厄運和惡意是什麼,壑難填,無止無盡。
其實在這個鬼域里,只相信這本鬼冊和的鬼王燈。
姜艾隔著那道致華麗的屏風看著賀思慕,看著這個姑娘在人世里長大,又看著在鬼界里為王三百年,卻突然覺得看不明白了。
“所以你說不喜歡惡鬼,其實是在折磨晏柯?”
“讓他做我的下屬,得不到王座也得不到我,看得見不著,不是很有趣麼。這九宮迷獄之外的迷獄,比灰飛煙滅煎熬得多。”
賀思慕平靜的聲音從屏風后傳來。
“不過,我是真的不喜歡惡鬼。若我能喜歡惡鬼,像你和白散行似的那也好。”
這話讓姜艾想起半年之前,賀思慕突然送給這個素白綁著鈴鐺的鐲子的時候。
當時問——這是什麼?
賀思慕淡然地丟出石破天驚之語——白散行的心燭。
驚詫不已,便見賀思慕說當年保留了白散行的心燭,帶到了九宮迷獄外面點著,一直由禾枷一脈保管。第三十代的禾枷是個厲害又手巧的家伙,將這心燭加以改造,做了能縱制心燭之主的法。
姜艾便懷疑道——王上,你把這個法送給我?
——其實你和白散行之間并不是完全沒有分罷。只不過他太過自負想要控制你,把你得太了。你以為他死的時候,我見你很難過。
——思慕……
——現在換你控制他了,他在九宮迷獄里吃了許多苦頭,我剛剛把他喚醒帶出來。若你愿意便再給他一次機會。姜艾姨,你對我很好,我希你幸福。
那時和此刻賀思慕除了讓姜艾到陌生之外,還讓覺到有些傷心。想這個孩子早就知道一切真相,知道自己的父親因誰而死,知道貌似親近之人的覬覦,在三百多年的時間里不聲,也沒有試圖告訴過誰,依靠過誰。
可賀思慕也還是個小姑娘啊,總共活了四百歲,在人世里曾嬉笑怒罵,在父母膝頭撒的姑娘,怎麼就到今天這個地步了呢。
姜艾走到屏風之后,賀思慕似乎有些意外地看著,看見了姜艾眼里的不忍,擺擺手笑起來道:“姜艾姨,你別這樣。晏柯掌控不了你,未免節外生枝他定要加快籌備,盡早起兵反叛。正好讓我看看還有哪些有異心的家伙,省得我以后一個個去找了。到時候還需要你支持我呢。”
“那是自然的。不過……思慕,你為什麼挑這個時候?”姜艾有些不解,賀思慕畢竟已經知道這些事三百多年了。
賀思慕想了想,道:“其實我等他謀反等了很久,一直沒等到,倒也不是很著急。”
或許是因為不知道為父親報完仇之后,這條路該往哪里去。原本就在大霧彌漫的路上走著,原本還有一盞復仇的燈,以后就連燈也沒有了。
頓了頓,賀思慕說:“不過近來我覺得,或許是時候做個了結了,我該往前走了。”
姜艾覺得賀思慕現在的神很悉,總是在提起人世里那個小朋友時出這樣的神。這句話里并沒有提到他,不過姜艾卻有種覺,賀思慕是在說他。
人世里的段胥得了景州,齊州起義軍又肯歸順,便開始琢磨起來要打幽州了。正好駐守幽州的丹支大將正是他的老朋友,當年率兵越過關河直下兩州直南都的萊。
那場讓丹支痛失三州的儲位之爭終于落下帷幕,萊支持的六皇子終于坐穩了儲位,他得了無數封賞了丹支的上柱國大將軍,本不用再親自奔赴前線。不過一聽說這次大梁帶兵的兵馬大元帥是段胥,萊立刻跳起來要求出征,帶著十萬兵直奔幽州,將景州、齊州平叛不力的將軍砍了腦袋,儼然是要一雪前恥將段胥趕回去,并要他把占下的地都吐出來的架勢。
段胥不替被砍頭的將軍們到冤枉,景州那位將軍以為唐德全要歸降丹支,平叛自然平得漫不經心,誰知斜里殺出一個他把這潭水攪渾了,再想認真平叛已經來不及了。齊州那位將軍倒是盡職盡責,架不住趙家是基深厚的大家族,齊州十個人里有五個姓趙,都沾著點兒親帶著點兒故,趙家本家從前上下打點早把齊州從府到軍隊吃了,揭竿而起自然一呼百應勢不可擋。
當然最關鍵的因素還是在于幽州,幽州險要,每個關卡均有重兵把手。大梁的軍隊在云州州虎視眈眈,丹支這些兵力就不敢輕易分去平叛。
段胥悠悠抵達了齊州,和趙興虛與委蛇一番,搬出蔚州歸順的錢義的逍遙日子安他。趙興明里暗里的意思是不想離開齊州去南都封,段胥知道他心里盤算什麼,便說趙家在齊州樹大深,若趙興在南都出了什麼差錯齊州這邊本沒法代,大梁自然會竭力保他的安危。再說南都繁華得不行,日子肯定比齊州舒服多了。
趙興和段胥都清楚,如果趙興離開了齊州,至三十年之是回不來了。趙興和錢義不一樣,錢義是忠肝義膽的綠林好漢,本在蔚州沒有什麼勢力。趙興則是盤踞齊州的土皇帝,商軍三路通吃,留在齊州便是管不住的大患,自然要放在皇上眼皮子底下看著。
正在此時南都卻傳來消息,說皇上暈厥五日方醒,欽天監算出是北邊破軍星有異象沖撞了皇上,而破軍又正好對應齊州一帶。
皇上立刻下詔,要從齊州來的趙興暫緩南都封。趙興可高興得不行,而段胥則有些頭疼。好在趙興雖然不聽他的話,但至也不會在后面搗,段胥便暫時也不去管了。
“欽天監是怎麼回事?風夷國師怎麼會讓他們算出這麼些東西?”段胥不由嘆道。
給他帶來南都消息的羨坐在營帳中,淡淡道:“風夷國師已經離開南都去云游,不再是國師了。欽天監那些人卯足了勁兒要給皇上多呈些帖子,好站穩腳跟。”
“國師離開南都?”段胥有些驚訝。
禾枷風夷為保護王室一般不會離開南都,他此時離去,莫不是鬼界有了什麼事?此前思慕來找他的時候,也提過最近鬼界不太平。
段胥雙手疊于邊,正出神思考,卻聽羨繼續說道:“還有最近的消息,方大人那里出了些事,他被降職了。”
猜你喜歡
-
完結847 章

穿書後,我嬌養了反派攝政王
(章節內容嚴重缺失,請觀看另一本同名書籍)————————————————————————————————————————————————————————————————————————————————————————————————————棠鯉穿書了,穿成了炮灰女配,千金大小姐的身份被人頂替,還被賣給個山裏漢做媳婦,成了三個拖油瓶的後娘!卻不曾想,那山裏漢居然是書里心狠手辣的大反派!而那三個拖油瓶,也是未來的三個狠辣小反派,最終被凌遲處死、五馬分屍,下場一個賽一個凄慘!結局凄慘的三個小反派,此時還是三個小萌娃,三觀還沒歪,三聲「娘親」一下讓棠鯉心軟了。棠鯉想要改變反派們的命運。於是,相夫養娃,做生意掙錢,棠鯉帶着反派們把日子過得紅紅火火!後來,三個小反派長大了。一個是位高權重當朝首輔,一個是富可敵國的大奸商,一個是威風凜凜的女將軍,三個都護她護得緊!當朝首輔:敢欺負我娘?關進大牢!女將軍:大哥,剁掉簡單點!大奸商:三妹,給你遞刀!某個權傾朝野的攝政王則直接把媳婦摟進懷。「老子媳婦老子護著,小崽子們都靠邊去!」
145.2萬字8.33 120041 -
完結188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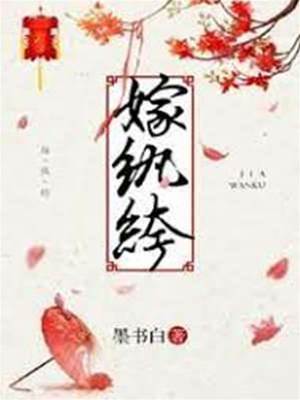
嫁紈绔
柳玉茹為了嫁給一個好夫婿,當了十五年的模范閨秀,卻在訂婚前夕,被逼嫁給了名滿揚州的紈绔顧九思。 嫁了這麼一人,算是毀了這輩子, 尤其是嫁過去之后才知道,這人也是被逼娶的她。 柳玉茹心死如灰,把自己關在房間里三天后,她悟了。 嫁了這樣的紈绔,還當什麼閨秀。 于是成婚第三天,這位出了名溫婉的閨秀抖著手、提著刀、用盡畢生勇氣上了青樓, 同爛醉如泥的顧九思說了一句—— 起來。 之后顧九思一生大起大落, 從落魄紈绔到官居一品,都是這女人站在他身邊, 用嬌弱又單薄的身子扶著他,同他說:“起來。” 于是哪怕他被人碎骨削肉,也要從泥濘中掙扎而起,咬牙背起她,走過這一生。 而對于柳玉茹而言,前十五年,她以為活著是為了找個好男人。 直到遇見顧九思,她才明白,一個好的男人會讓你知道,你活著,你只是為了你自己。 ——愿以此身血肉遮風擋雨,護她衣裙無塵,鬢角無霜。
81.5萬字8.46 50163 -
完結2012 章

戰神王爺是妻奴
一朝穿成被人迫害的相府癡傻四小姐。 從死人堆里爬出來,隨身攜帶醫藥實驗室和武器庫。 對于極品渣渣她不屑的冷哼一聲,迂腐的老古董,宅斗,宮斗算什麼? 任你詭計多端,打上一針還不得乖乖躺平! 絕世神功算什麼?再牛叉還不是一槍倒! 他,功高蓋世,威震天下的戰神王爺。 “嫁給本王,本王罩著你,這天下借你八條腿橫著走。” “你說話要講良心,到底是你罩我,還是我罩你呀?” “愛妃所言極是,求罩本王。” 眾人絕倒,王爺你的臉呢?
362.3萬字8 38042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