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成了虐文女主她親哥》 第111章
君懷瑯被薛晏放開時, 面有些發紅,息也了方寸。
他了幾口氣,才后知后覺地有些驚慌, 轉頭往巷口看去。
幸好, 外頭雖人來人往的,卻沒人往他們這個方向看一眼, 更沒人往這里來。
君懷瑯松了口氣,卻后怕了起來。
“日后在外頭,不許再這樣來了!”他一邊整理袍,拍去袍上的塵土,一邊低了聲音斥責薛晏道。
但因著二人剛吻過的緣故, 他氣息不勻,斥責的聲音也并不眼里。
“嗯, 知道了。”薛晏站在面前低頭看他,眉眼間都是笑,答應道。
“這讓人瞧見可如何是好?”君懷瑯接著道。“你也太莽撞了些,怎麼偏在大街上就忍不住……”
他說一聲,薛晏便跟著應一聲, 乖巧過頭了, 反倒像是在逗著他玩似的。
君懷瑯察覺到了,抬頭看向薛晏。
薛晏這才站直,一本正經的樣子。
“我一直注意著外頭的靜。”他正道。“你這麼招人的模樣,我怎麼可能給別人看?”
君懷瑯更氣結了。
他雖能言善辯,但在這種事上向來說不過薛晏。他橫了薛晏一眼,整理好袍,便率先走了出去。
……即便人家沒看到,這兩人一同從暗巷里出來, 也很說不過去啊!
君懷瑯的耳都是紅的,僵地走出了巷子。
不過這街上熱鬧極了,眾人來來往往的,也并沒注意到他們。
君懷瑯走在前頭,薛晏就跟在他后半步的位置。
君懷瑯并無意跟他置氣,但方才吻得激烈,這人又這般惡劣,他此時便有些拉不下臉,再回頭去跟他同行。
二人便就這樣一前一后地走在街上。
這條街上今日人來人往的,尤其熱鬧。路邊上擺攤賣小件的、耍雜技的、賣燈的,還有飄著香氣和炊煙的吃食攤子,喧喧嚷嚷地挨在一起,五花八門。
Advertisement
君懷瑯四下看著,也覺得稀奇。
就在這時,一串紅彤彤的冰糖葫蘆橫在了君懷瑯的面前。
那糖葫蘆裹著薄薄的一層糖,晶瑩又鮮艷,瞧上去饞人得很。
他抬頭,就見薛晏跟在他后,手里握著那串糖葫蘆。
“喏。”薛晏說。“賠你的。”
君懷瑯不接,他就一直將那糖葫蘆舉在那兒,跟著他。
君懷瑯只得抬手將那串糖葫蘆走了。
“下不為例。”他小聲道。
薛晏低聲一笑,跟著便追上了那半步的距離,挨著君懷瑯走在了他旁邊。
君懷瑯咬了一口糖葫蘆。
這小食雖然常見,但君懷瑯幾乎從小到大都沒吃過。他從小要學的就多,每日都需見許多先生。除了要出府應酬之外,他很出門,更沒怎麼在大街上閑逛過。
更何況,府有各式各樣的糕點零食,也不必他們去外頭,吃這等路邊上賣的小。
他小時候見得,只會偶爾好奇,等年歲大了,更不會特意去路邊上買這類孩子吃的事。
故而此雖是尋常,在君懷瑯這兒,卻是稀奇得很。
他一口咬下去,泛黃的晶瑩糖在齒間碎開,裹挾著山楂酸甜的水,頓時,一酸甜在他齒間彌漫開來。
君懷瑯的眉頭都不由得舒展開了。
“好吃?”旁邊的薛晏覷著他的反應。
君懷瑯點了點頭,眼都不由自主地瞇了起來,也沒注意到,自己邊掛了一小塊糖。
薛晏抬手替他將糖渣取了下來,低聲笑道:“怎麼跟沒吃過似的。”
君懷瑯笑著點頭道:“確實沒怎麼吃過。”
薛晏笑道:“怎麼,國公爺還管你這個呢?”
君懷瑯噗嗤笑出了聲,同他開玩笑道:“是啊,那可如何是好?”
薛晏順著他的話,正道:“那以后我買給你吃,我有經驗得很。”
君懷瑯被他逗得直笑:“你有什麼經驗?”
他自然不知道,薛晏說自己有經驗,確實不是假話。
他在燕地的軍營里長大,按著軍營中的規矩,平日里是不能隨便出的。
偶爾出一次營,正好見集市上的小販賣糖葫蘆。一整扎的稻草上,滿了鮮紅滴的紅果,燕地天寒,冬日里賣的糖葫蘆凍得結結實實,咬起來直涼牙。
但燕地的軍營里本沒有零食,那種酸甜多的味道,小時候的薛晏嘗過一次,便忘不了了。
再后來,他在軍營中挨了打,了傷,就會翻墻出去,給自己買串糖葫蘆,再翻回來。
燕云寒冷的深夜里,一串凍得邦邦的糖葫蘆,就是薛晏唯一的止痛藥。
故而這酸甜味雖說平庸至極,對于薛晏來說,卻是印在靈魂里的甜味。
薛晏聽到君懷瑯問,低低一笑,只說道:“這你就別管了,反正以后,不了你的糖葫蘆吃。”
君懷瑯笑著直點頭,還將手里的糖葫蘆遞到薛晏面前:“那我便先謝過你。口頭謝沒什麼誠意,不如分你一口?”
他將糖葫蘆遞過去時,才發現上頭的那顆,是自己咬了一半的。
他便連忙要將手收回去。
但他的手卻被按住了。
薛晏抬手,一把握住了他想要收回的手,將糖葫蘆拽了回來。
跟著,他便將最上頭的那半顆吃進了里。
“哎——”君懷瑯攔他不住,只得眼睜睜看他將那顆被自己咬掉了一半的紅果吃下。
薛晏笑著放開了他。
“果然。”他說。“比燕云的好吃些。”
——
進寶知道,為下人,向來要有召之即來、揮之即去的自覺。
比如之前,他主子拉著世子殿下不知道到哪個角落里卿卿我我去了,他就要站在川流不息的人堆里,眼觀四路耳聽八方,等著他主子重新回來。
再比如剛才,他家主子過人堆,跑到路邊給世子殿下買了串糖葫蘆,二人有說有笑的,世子殿下還將糖葫蘆喂給主子吃,他便眼觀鼻鼻觀心,權作自己是個什麼都看不見的瞎子。
再比如現在,到了用到他的時候了。
說起來,今日集會辦得熱鬧,還全是他一手策劃的。金陵的百姓向府衙報備,要在夜里搞慶祝活,但百姓們手里沒錢,金陵府衙也的,活自然辦不了多熱鬧。
進寶跟薛晏一提,薛晏立馬讓他自己去撥錢,看著安排。
進寶知道,他家主子說的“看著安排”,那就是往熱鬧里辦的意思。
畢竟他主子還要帶著世子殿下去逛街不是?
反正他主子有的是錢,進寶也不心疼。故而街上今日的彩帶花燈,全是進寶一手安排的,就連街道上的小商販、耍雜技的,都是進寶按著報備的攤位單子,以薛晏的名義,給他們不計利息地貸了進貨的補。
也正因為此,今日這慶典才能辦得如此熱鬧。
但進寶不知道,到頭來苦的還是自己。
江南本就小玩意多,世子殿下又是個大門不出二門不邁的公子哥,故而看什麼都新鮮。不過他雖四下里看著,卻只挑幾個買,至于其他的,進寶就要看自家主子眼行事了。
他主子沒回頭,那就說明世子殿下沒多喜歡。他主子若是回頭瞥他一眼,進寶就懂了,要自己上前去問攤主,前頭那位公子都看過哪幾樣東西,全都包起來。
逛了一路,進寶手里的東西越來越多,讓他不得不用暗號傳喚出一個錦衛來,讓那錦衛幫自己搬東西。
卻不料,那個錦衛是個油舌的壞心眼。看到他手里大包小包的,便只顧著嘲笑他,進寶將東西遞給他讓他幫忙拿,他卻連連躲開。
“主子只讓屬下保衛安全,可沒讓屬下拿東西啊?”那錦衛跟進寶,笑嘻嘻地道。“這種陪主子逛街的差,還是公公自個兒消吧?”
說完,幾個呼吸間,人就跑了。
進寶氣得要拿手指他,又騰不出手來,眼看著自家主子要走遠了,便只好快步跑著跟上。
而前頭的君懷瑯,自然對這些一無所知了。
金陵夜市上的件新奇別致,不過他也知自己買來不過玩玩,買多了都是浪費。故而他看上了什麼小,都是比較比較,挑出一個來。
他給自己買的東西,倒都是給一對弟妹、母親、姑姑和薛允煥買的。
他買下來,薛晏便替他拿過去,故而君懷瑯更不敢買多,怕薛晏拿不下。
二人走著,便一路逛到了深。
就在這時,薛晏停了下來。
君懷瑯跟著他停下來,側過頭看去,就見薛晏停在了一個小攤前。
方才薛晏一直是目不斜視的,只跟著自己逛,君懷瑯一時好奇,不知道是什麼東西了薛晏的眼,能讓他停下腳步。
就見是個賣玉佩的小攤子。
這攤子上賣的自然不會是什麼好玉,但這攤主卻心靈手巧,玉佩上的絡子打得致得很。
“這位客,可看上哪個了?”那攤主一見薛晏飾,就知他非富即貴,連忙迎上來問道。
薛晏指了指攤上的一個方向:“這個。”
君懷瑯跟著看去,便見那兒掛著一對玉佩,是簡單的玉玨樣式,沒什麼花紋,底下淺青的絡子,打的是同心結的樣式。
那攤主連忙給他取下來:“公子可是要送人?這玉佩是一對的,沒法兒自己戴……”
就見薛晏側過頭去,看了君懷瑯一眼。
小攤上點著燈,并不太亮,只足夠照亮攤上的品。燈之下,薛晏的半張臉匿在黑暗中,但出的那一側,目灼灼。
他隨手丟了一錠銀子給攤主,接過了那對玉佩。
“是要送人。”他說。“送給我夫人。”
猜你喜歡
-
完結247 章

重生傾天下:王爺獨寵妃
蘇茹雪前世錯愛蕭銳澤,致使自己在產子的那天被冤枉造反,隨後滿門抄斬,連剛出生的孩子也一同死去。 她因死後怨氣凝結,重回人間變成蘇家嫡女,卻冇有前世哥哥姐姐姐相幫,獨自一人複仇。 她被接回是因為代替妹妹嫁給那快要病死的六皇子,避無可避之下她選擇答應。 新婚之夜,她遇到了第一晚威脅她的男子,眼裡滿是驚訝:“怎麼是你?你溜進來搶親不成?” 蕭景辰一把抬起她的下巴,“也不是不可以。” 新婚小嬌妻竟不認識自己的夫君,這場好戲有得演!
44.5萬字8 8572 -
完結173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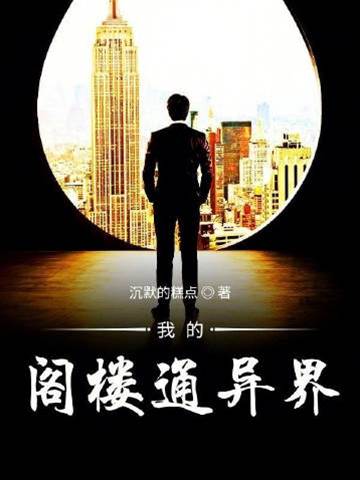
我的閣樓通異界
王歡受傷退役,堂堂全運會亞軍落魄給人按摩。 租住閣樓竟有傳送門通往異界空間,寶藏無數。 命運改寫!他包攬奧運會所有短跑金牌,征服諾貝爾文學獎,奧斯卡金像獎,格萊美音樂家獎。 他製作遊戲滅掉了暴雪,手機滅掉了蘋果,芯片滅掉了英特爾,飛機滅掉了波音。 他成為運動之神,文學之神,音樂之神,影視之神。 稱霸世界所有領域,從奧運冠軍開始。
71.3萬字8 24792 -
完結476 章

重生后成了前夫的掌上珠
唐菀爲清平郡王守了一輩子寡,也享了一輩子的榮華富貴,太平安康。 內無姬妾爭寵煩心,上有皇家照應庇護,就連過繼的兒子也很孝順。 她心滿意足地過了一輩子,此生無憾閉上了眼睛。 再一睜眼,她卻重生回到了十五歲那年的夏天。 自幼定親的未婚夫一朝顯貴逼她退婚,迎娶了他心中的白月光,她嫡親的堂姐。 他愛她堂姐至深,念念不忘。 唐菀成了京都笑柄。 眼看着堂姐嬌羞無限地上了花轎,風光大嫁,郎情妾意,情投意合。 唐菀淡定地決定再嫁給上一世她那前夫清平郡王的靈位一回。 再享受一世的榮華富貴。 只是萬萬沒有想到,剛剛抱着清平郡王的牌位拜了天地,上輩子到她死都沒見過一面,傳說戰死於邊陲生不見人死不見屍的清平郡王,他回來了! 清平郡王:聽說王妃愛我至深,不惜嫁我靈位,守寡一生也要做我的人。 唐菀:…… 他護她兩世,終得一世圓滿。
79.4萬字8.33 21863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