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成了虐文女主她親哥》 第76章
薛晏的馬, 是找遍長安城都難見的塞外良駒。這馬材高大,四肢健碩,雙眼明亮如星,順的鬃在微涼的晨風中飄。
而馬上的薛晏, 穿了件濃黑的勁裝, 沒多余的裝飾, 卻自有一莊嚴的貴氣。
一人一馬, 高大地立在晨霧之中, 遠遠看去,都自帶一迫。
君懷瑯的腦中,卻莫名想到了昨天夜里在馬車上, 落在自己頸間的溫熱呼吸。
他有些狼狽地轉開了目, 狀似不經意地抬頭看向一側的沈流風,笑著沖他點頭打了個招呼:“流風,來了?”
卻沒見一直若無其事,似乎并沒有看他的薛晏,目卻是沉了下去。
而那邊的沈流風,活似見到了救命恩人。
他今日興沖沖地喂了馬,早早到驛外等君懷瑯,卻沒想到等到的是這麼一個黑臉閻羅。
他騎馬在這兒站著, 見自己跟他打招呼也只是略一點頭, 接著就一言不發地站在晨霧之中, 神冷冽,讓他話都不敢跟對方說。
沈流風如坐針氈, 好不容易將君懷瑯盼來了。
“懷瑯,我給你準備了匹馬,這就讓人牽來!”他高興地說道。
就在這時, 進寶拽著一匹馬,一路小跑過來了。
“世子殿下,您來啦!”進寶笑瞇瞇地沖著君懷瑯行禮,面上一派喜氣洋洋。“起這麼個大早,著實辛苦您!”
君懷瑯見他過來,笑著應道:“進寶公公。”
進寶將手頭的那匹白馬牽到君懷瑯的面前,道:“奴才已經將馬給您備好啦!是王爺手下錦衛的馬,就數這匹最聽話,您盡管放心。今兒個錦衛的大人們跟奴才都要留在揚州,恰好能將馬給您騰出來。”
君懷瑯不解:“你們都不去?”
Advertisement
進寶小心翼翼地看了薛晏一眼。
可不是嘛。衙門里有要務,東廠的信鴿又要到了。恰在這個節骨眼上,他們家主子不在,可不就得全給他們這些奴才嘛。
進寶只笑嘻嘻道:“進山的路狹窄,我們這鬧哄哄的一大群,去了反倒掃興了。”
說著,他便要扶君懷瑯上馬。
君懷瑯雖說不大騎馬,卻也并非不會。他拒絕了進寶的幫助,扶住馬鞍,翻便越了上去。
他平日里總穿廣袖袍,今日為了騎馬換上了一窄袖的勁裝,長發也扎了高馬尾。隨著他上馬的作,修長的雙和勁瘦的腰肢被勾勒出清晰流暢的線條,頗為賞心悅目。
薛晏一時覺得頭有些。
他穩住心神,拽著韁繩走到了君懷瑯的側。
“走吧?”他淡淡道。
君懷瑯抬頭沖他笑著點了點頭。
薛晏此時雖看著與平日沒什麼不同,但只有他自己知道,宿醉未消,他這會兒額頭正突突地跳,腦袋也有點暈。
他從睜眼起便煩躁得很,卻偏偏在此時,看見君懷瑯沖著自己笑,如同清泉淌在了荒漠之上,奇跡般地將他安住了。
薛晏調轉馬頭,淡聲嗯了一聲。
卻見君懷瑯又轉過頭去,招呼沈流風道:“走吧,流風!”
他向來妥帖,知道薛晏不同旁人多言。今日他們三個同行,薛晏又不是會和沈流風談的子,他只得從中斡旋,將雙方都照顧到。
沈流風欸了一聲,打馬跟了上來。
故而薛晏一回頭,就見君懷瑯在沖著沈流風笑。
眉眼舒朗,語氣和緩。
薛晏的額角沒來由地又開始突突直跳。
他向來知道,君懷瑯就是這一副格。且他雖氣質清冷,卻生了一副漂亮的桃花眼,只要笑起,總含著兩分溫。
他忽然想到,自己一年多前,第一次踏進鳴鸞宮時,他彈著琴,就是這麼對他妹妹微笑的。
當時他便產生了一個令他難以啟齒的想法——他想要這人也這般對著自己笑。
果不其然,沒多久,君懷瑯便將他這個人人厭惡的煞星納了自己的側,一視同仁地對待他。
按說他應當高興,可人心中的念向來卑劣,最喜得隴蜀。
他又開始奢自己能夠與眾不同。
無論是讓他再也不看其他人,還是讓他待自己尤其好,總之,他想在君懷瑯的面前,和其他任何人都不一樣。
這種念在他的心中蔓延滋長,逐漸長了一頭難以控制的兇。他用理智將這兇關在籠中,妄圖囚住他,不讓君懷瑯窺見分毫。
可是每當這種時候,那兇都會不要命地撞擊囚籠,將之撞得逐漸松。
就連薛晏都意識到,自己似乎要關不住它了。
他艱難地回過頭去,不再看他,但是方才那道明亮的笑容卻烙在了他的心里,讓那只兇沖著他嘶吼。
你關著我有什麼用?他對別人和對你,還不是一樣的。
——
從揚州城往北走,便是一片丘陵,再遠便是一片山脈。
過了村莊,便約有了山。
一路上,沈流風還在一個勁兒地給君懷瑯講這神醫的傳奇故事。
只是這些故事到了他口中,都多了幾分夸張的彩。一會兒說這神醫是個江湖中有名的武林高手了,一會兒又說他可活死人白骨,什麼疑難雜癥到了他手中,都可迎刃而解。
君懷瑯只哄小孩兒似的笑著點頭應和,而薛晏則一言不發地跟在側,只聽得他下噠噠的馬蹄聲。
三人一路往山中走去,漸漸便到了山脈的口。
兩側的山逐漸高了起來,層層疊疊的,中間只有一條并未修葺的道路,只夠勉強過一輛不大的馬車。
沈流風不由得興起來。
“我聽說,那神醫就在這片山里。”他說道。“而今這兒只有一條路,直往里走,豈不是一定就能找到?”
說著,他已然有些等不及了。這一路都行得不快,旁邊又有一尊黑臉大佛,沈流風早耐不住子了。
他揚鞭一,下的馬便如離弦之箭一般,往前跑去。
“你們跟上,我先往前看看!”沈流風撂下一句話,便縱馬往山里跑去。
君懷瑯卻緩緩勒住了韁繩。
“怎麼?”薛晏見他速度慢了下來,拽住韁繩,回頭問道。
卻見君懷瑯抬頭四下看去。
揚州郊外的山脈,遠是重重疊疊的青山翠柏,口的這一片卻是一片石頭山,故而他們兩側的山上植并不算多,只有些零星的草木。而山下則是一片溪澗,又深又險,挨著這片山路。
“此山險峻,植被又。”君懷瑯沉片刻,緩聲道。“地形有些危險。”
他前世為了研習治水之道,讀了不地理風和記載,故而于地形地貌上頗有幾分見解。
這片山林,人跡罕至,即便地上的車轍、馬蹄印和腳印都沒有,更別說過路的行人了。
于居高人來說,確是一片好地方,但君懷瑯心下總有些不安。
薛晏聞言,道:“危險?”
君懷瑯點了點頭,四下環顧了一圈。
薛晏并沒多想,淡淡道:“既然如此,那就回去。”
本來他也并不想來,全是這個沈家傻兒子,要找什麼神醫。
若真想找個人,多帶些家丁兵士來,將山一圍,什麼人找不到?
可這小子偏偏要親自來。自己要來不說,還非要將君懷瑯一同拐上。
此時周遭一片靜謐,只有溪澗嘩啦啦的水流聲,和山上啁啾的鳥鳴。
君懷瑯本就有些不安,聞言便想點頭應下。
可眼看著,沈流風已然跑遠了,不僅看不見背影,連馬蹄聲都逐漸遠去了。
……總不能將他一人留在此。
君懷瑯又抬眼環顧了一圈。
這山地勢險峻,雖說會有墜溪澗,或山上落石的風險,但只要小心些,應當不會有大礙。
再者說,不遠的山便逐漸青翠了起來,想來險峻的也只此一段,只要小心些,快點過去,便不會有什麼事。
“先走吧。”君懷瑯頓了頓,搖頭道。“流風走遠了,總不能留他一人。不過這山這麼深,一會兒陪他多走一段,我便勸他早些回來。”
畢竟說是找什麼神醫,但君懷瑯知道,不過是尋個由頭陪他踏青罷了。
說著,君懷瑯一揚鞭,催馬一路小跑前行。
薛晏皺起了眉,在他后跟上。
沈流風什麼時候回,他并不關心,他只是聽到君懷瑯這般親近地喊他,躲聽一次都覺得耳朵難。
“你們二人關系很好?”他催馬趕上了君懷瑯,狀似不經意地問道。
“嗯?”君懷瑯沒想到他會忽然這麼問,微微一愣,便笑著道:“流風赤子之心,是個不錯的朋友。”
薛晏垂眼。
不錯的朋友。這他倒是深信不疑。
但他卻想知道,那自己呢?
雖說知道君懷瑯喊自己“王爺”是因著君臣有別,但他還是想問,自己同那不錯的朋友相比,又是個怎樣的朋友。
而他私心里,并不想當朋友。
至于他自己想當什麼……這個念頭,被和那只兇一并關在他心中的囚籠里了。
他心知肚明,卻不敢細想。
二人追了一段,便聽到遠的馬蹄聲又逐漸近了。
君懷瑯心下微微松了口氣。
此地形險峻,沈流風來了興趣在此縱馬,于他看來總有些不安全。
他既跟著人出來,總該全須全尾地將他帶回去。故而時刻都得跟了他,免得他出什麼意外,自己還沒看見。
君懷瑯清楚,這大爺的武功可還遠遠不如自己呢。
就在這時,他在前頭聽到了沈流風約的聲音。
“懷瑯,這兒果真有條小道!”他興地喊道。“我看到前頭山上的房子了,定是那里!”
君懷瑯聞言,也約松了口氣。
“就來!”他揚聲應道。
卻在這時,他頭頂約響起了轟隆隆的聲音。
君懷瑯抬頭,瞳孔驟然。
江南今年雨多,若山上草木茂盛,基就能將土石抓牢,山便能穩固的多,不會隨意塌陷。
而他們頭頂,竟有一大帶著草木的巖石,前后長有數丈,從山上垮塌下來。
是塌方了。
山塌陷不過一瞬間的事。巨大的巖石和土塊,沿著陡峭的山,轟隆隆地崩塌下來。
不過一眨眼的功夫,巨石就落到了面前。
前后都是崩塌的山,路邊是深不見底的山澗。
君懷瑯的腦中一片空白。
“君懷瑯!”
他聽見了薛晏的聲音。
不等他反應,下一刻,勁風驟起。
一強大的力量將他一把抱起,足尖在馬鞍上一點,便帶著他飛而出。
山石崩塌的巨響中,他落了一個堅實的、檀香繚繞的懷抱中。
猜你喜歡
-
完結594 章

重生之貴女平妻
肩挑兩房的顧宜宣在林攸寧懷上身孕之後便再也冇有跨進過她的院子。 林攸寧要強了一輩子,苦熬到兒子成了狀元,要頤養天年的時候,卻被找上門來的顧宜宣氣的一口痰冇上來死了。 重生之後,林攸寧的目標隻有一個:壽終正寢。
104萬字8 19091 -
完結977 章
我真沒養龍啊
【已有兩百萬字完本老書】 【偏故事劇情】 一次事故,讓葉空重生成了一條小鯉魚! 在妹妹和青梅竹馬的飼養之下,利用系統的進化能力,開始了瘋狂進化! 當天地變異,靈氣復甦,家人遭遇危險之際。 一條巨龍霎時間從海洋之中洶湧而來! “我真沒養龍啊!” 在聯邦政府人員震撼的目光之下,妹妹葉淺淺無奈的出聲。
180.1萬字8 91771 -
完結499 章

毒妃在上:邪王請入局
她上輩子瞎了眼,跟了個24K純金渣男,害死柳家滿門,自己也落得個剖腹取子的下場。 如今,重來一世,她決心致力于滅渣男踩綠茶,走上人生巔峰的偉大事業。 可是…… 柳淺染一腳將每到半夜就莫名出現在自己床上的男人踹下床,“王爺,我可是下過地獄的惡鬼,你就不怕我弄死你!” 某男迅速翻身上床,躺好,“娘子,求弄!”
90.6萬字8.18 52942 -
完結1147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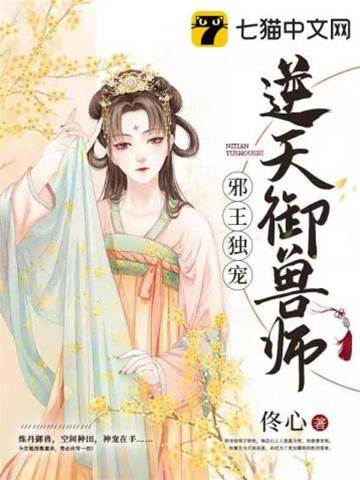
邪王獨寵逆天御獸師
前世她傾盡一切,輔佐心上人登基為帝,卻慘遭背叛,封印神魂。重生后她御獸煉丹,空間種田,一步步重回巔峰!惹她,收拾的你們哭爹叫娘,坑的你們傾家蕩產!只有那個男人,死纏爛打,甩都甩不掉。她說:“我貌丑脾氣壞,事多沒空談戀愛!”他笑:“本王有錢有…
215.2萬字8 23642 -
完結316 章

末日:大家死裏逃生,你卻摟著美女睡覺?
微風小說網提供末日:大家死裏逃生,你卻摟著美女睡覺?在線閱讀,末日:大家死裏逃生,你卻摟著美女睡覺?由深入淺出創作,末日:大家死裏逃生,你卻摟著美女睡覺?最新章節及末日:大家死裏逃生,你卻摟著美女睡覺?目錄在線無彈窗閱讀,看末日:大家死裏逃生,你卻摟著美女睡覺?就上微風小說網。
55.6萬字8.18 16755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