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狙擊蝴蝶》 第21章 第二十一次振翅
李霧雙休,時間暇余多,岑矜也跟著降低繃,熬了個大夜。
日上三竿,才從床上爬起來,沒換睡,套了件線就出來了。
次臥的門大敞著,出滿室明晃晃的亮。
轉頭折去書房找家里小孩,果不其然,他坐在里面,全神貫注地看講義。
岑矜抬手叩兩下門框,把他視線拉拽過來:“什麼時候起的?”
李霧詭異地結起來:“七、七點。”
岑矜狐疑地看他一眼,“剛考過試作業也這麼多麼。”
李霧說:“沒有也會自己找著做。”
“我要是有你一半刻苦,這會已經定居首都了,”岑矜嘆著挑高手機,下單外賣:“半個小時后出來吃飯。”
“好。”
岑矜坐回沙發,隨手繞了個揪。無所事事,打算刷會微博打發時間。
不料開屏就是“醇脆”的廣告,畫面清新,一位當紅流量小生手執酸杯,對著屏幕前所有人出了含糖量極高的笑容。
看風格都知道這張海報出自誰手,切進小組群,打字:我看到開屏了,銷量不對不起你的用心良苦。順便艾特了一個名字。
被夸的那位設計哈哈大笑,謙虛回:主要代言人好看。
岑矜笑了下,剛要再跟他胡侃幾句,突然來了電話。
岑矜瞥見名字,臉黯了幾分,摁下接聽。
吳復開門見山:“這兩天有空嗎?”
岑矜說:“有。”
“找時間面簽紙質協議吧,”吳復安排得有條不紊:“周一上午我可以請假,我們去把離婚手續辦了。”
“好啊。”岑矜輕飄飄應道。
那邊沉寂幾秒,說:“你媽給你的東西還在我這,我下午給你送過去。”
岑矜雙曲上沙發,麻木地滾出一個鼻音同意。
Advertisement
他繼續說:“下周辦完過戶,我會搬出清平路的房子。”
岑矜垂眸看自己指甲蓋:“我以為你會要房子。”
“九百多萬的房子不是誰都負擔得起的,”吳復不卑不:“當時買那邊主要還是為了讓你高興,按揭與首付的錢我只拿回了我出過的一半,你沒必要再用這些事變相攻擊我。”
岑矜無辜:“我有嗎,你太敏了。”
“我們彼此彼此。”
岑矜笑了一聲:“你是不是到現在都覺得,流產的事影響了我,讓我挫,大變,直接導致我們婚姻走到這種地步。”
吳復沒有否認:“是。”
岑矜輕輕搖了下頭,好似對面能看到一般:“不是,不關小孩的事。你還記得我坐小月子休假那會麼,有一天你回家,我坐客廳喝飲料,你很冷地說,你就造吧,還想生不出小孩麼――我只是買了杯果。我說,就算真不能生小孩又怎麼了。你回了我什麼,你說那樣婚姻還有什麼意義可言。那會我很驚訝,我以為你會擔心我,擔心我緒,但你更擔心我還有沒有繁能力。我的人份在一次流產之后對你而言變得毫無價值,你對孩子的重視遠超我們過去那些年的累積。而這些話,你恐怕都不記得了。”
“我……”吳復言又止,語氣變得虛渺,“現在再說也同樣沒意義。”
“我知道。”
可永遠都無法翻篇了。它們就像深骨髓的疤,不去還不要,但每每揭開來看,還是模糊,創巨痛深。
“所以別說了。”
“那句話對我傷害很大,我到現在都記得,我必須說,”岑矜沒有就此作罷:“可能從那天開始,我對你的里,就有了恨意。你能明白嗎,「岑矜至上主義者」。”
“要翻舊賬我也能寫下300頁PPT,”吳復不愿再為舊事糾結:“下午我再找你。”
―
書房門沒有關,人不大不小的聲音順著幽邃的走廊傳進李霧耳里,他擱下筆,用力了下眉梢。
的口氣聽起來異常平靜,但這種平靜并不像不在意,而是萬念俱灰。
他捋起袖口看了眼電子表,第一次發現學習的時間這麼難熬。
―
早餐午餐并到了一起,所以岑矜點了不家常菜,有葷有素有湯,鮮香四溢,漂漂亮亮擺了一整桌。
可興味寥寥,吃下小半碗飯就靠回椅背玩手機。
李霧著飯,多次挑眸看,也渾然不覺。
等年起去添第二碗,岑矜才分出半寸目過來:“這周重稱了嗎?”
“嗯。”
把手機擺回桌上:“重了麼。”
“重了0.35千克。”他特地確到小數點后兩位,以顯對要求的重視。
岑矜因他嚴謹的后綴單位而怔愣,在腦子里轉換為公斤才反應過來:“這算什麼,尿個尿就沒了。”
“……”
忽的前傾,細細審視起他來。
李霧瞬間如坐針氈,吞咽的作都變為0.5倍速。
人視線在他臉上轉了一圈,最后停到他面前的碗口:“我看你吃得也不算,是不是平時學習太辛苦了?”
“還好。”他永遠這個答案,以不變應萬變。
岑矜換了個問法:“飯卡用多錢了,在機子上查過嗎?”
李霧清楚記得自己每一筆賬目:“326塊九。”
“才三百?你一日三餐只吃白飯嗎,”岑矜難以置信:“還是只喝湯?”
“……”他聲音低了些:“就正常吃。”
“啊――”岑矜低嚎一聲,雙手蓋頭:“我不用你給我省這種錢,不需要,更不要你還,你可不可以對自己好點啊。”
李霧被突如其來的抓狂驚到,直接握著筷子頓在原。
岑矜垂下手,也因此把頭發兒帶得散了些,涼涼看向他:“所以你在我面前都是裝給我看的?”
李霧眉心一:“什麼?”
下挑高:“在我能看到的地方吃這麼多,吃這麼熱,轉頭回學校了又寒迫。”
“……”李霧抿了下:“我沒有。”
“那三百多是怎麼用的。”
李霧手汗都要出來了,他嗓音悶悶:“賬本在學校,沒帶回來。”岑矜完全詞窮。
李霧接著吃飯,作小心,連遠一點的菜都不太敢夾。
他能覺人的目仍在自己臉上游走,久未離去。
但他無法去直視的面龐,辨析的臉,只能猜測在以什麼樣的緒看待他。
他并未辜負的好意。他必須為自己正名。
咽下最后一口飯,李霧放下筷子,吸了吸氣,迫自己向岑矜:“憑吃飯就能判斷一個人對自己好不好麼。”
岑矜搭腮:“當然,都不好好吃飯還怎麼長,還怎麼健健康康,還怎麼有力氣面對學習和生活。”
李霧深吸一口氣:“你也吃很。”
岑矜頓了下,以為自己沒聽清,微微側耳:“什麼?”
“你也吃的很。”他幾乎一字不差的重復,面容平靜。
他是在教育?岑矜有些反應不過來,接連眨眼,“我本來胃口就這樣。”
李霧說:“我也每頓都吃飽了。”
“你意思是我自己都不吃飽?沒資格要求你是吧。”聲音趨冷,已有抬杠傾向。
“我沒這個意思。”的腦回路怎麼不跟他一致,李霧只覺困擾。
岑矜盯他兩秒,手遽得一,把自己先前沒吃完的那碗飯拉回來,還抓起筷子,對著桌面猛墩一下,而后賭氣一般開始低頭吃飯。
只一會碗底就干凈了,抬起眼來瞪他,目。
李霧第一次見到這一面,有點兒懵,又想笑。
年眼皮半垂,本不敢看。
他是不敢與對視,但可以想放進里腦子里想,反正又看不到。
所以他就肆無忌憚地想了。
怎麼這麼可啊。
這個姐姐。
“我飽得都要吐了,”岑矜還想再夾些菜,但終究是吃不下了,皮笑不笑:“現在有資格要求你了麼。”
“……”
“從三周三百變每周三百,這個能做到吧。”
“用不到這麼多。”
“那就努力用到。”
“……嗯。”
……
―
下午,岑矜化完妝換好服就出了門。
走前了個識的阿姨過來打掃,叮囑李霧多留心門響。
李霧有些坐立難安,他猜到岑矜是要去見丈夫,但最終結果如何還是未知數。
電話里的沖突并不鮮明,談攏的可能也非為零。他完全無法停止這些惡劣的祈盼與猜想。
尤其還打扮得很漂亮,這種秋風蕭蕭的天氣都穿著一字領的紅,還,鎖骨橫在皮里,好似兩支潔白的匕刃。
同的襯得盛氣凌人,不容小覷。
的樣子在他腦海里揮之不去。
李霧煩躁又懊惱地轉了會筆,仰回椅背,腔重重起伏著。
不應該這樣。
他知道。
但已經這樣了。
沒辦法。
他無法控制自己的夢境,就像無法控制自己不去想,包括想象。
他醒來后就沒能再睡著,等到東方既白,第一件事就是起床沖涼,乞求冰冷的清水能洗去他齷齪不堪的想法。
去晾服的路上,他在門前停了會,那幾秒鐘,他的心異常靜謐,靜謐得宛若立在巨大的神像之下。
但這份靜謐終止于出現在書房門前的那一刻。
他的所有神經又火燎一樣燒起來,以至于忘了要怎麼說話。
李霧闔上了眼睛,如噩魘纏那般眉心鎖。
這時,門鈴忽得響了。
他忙睜開眼,快跑到玄關,剛要去握門把,指紋鎖滴了一聲,門被人從外打開。
四目相對。
男生瞳孔驟,因跑微的氣息也漸緩,漸平,因為來人并非岑矜口中的鐘點工阿姨。
但并不陌生。他幾乎是下一秒就認出了他。
男人的驚愕不比他,他凝視他片刻,眼神轉為微妙的審視與刺探。
“你哪位。”他問。
“你不認識我了嗎,”下一刻,年以一種自己也不曾預見的無畏坦然迎上他目:“我是李霧。”
猜你喜歡
-
完結3579 章

韓先生情謀已久
“收留我,讓我做什麼都行!”前世她被繼妹和渣男陷害入獄,出獄後留給她的隻剩親生母親的墓碑。看著渣男賤女和親爹後媽一家團圓,她一把大火與渣男和繼妹同歸於盡。再醒來,重新回到被陷害的那天,她果斷跳窗爬到隔壁,抱緊隔壁男人的大長腿。卻沒想到,大長腿的主人竟是上一世那讓她遙不可及的絕色男神。這一次,她一定擦亮眼睛,讓 韓先生情謀已久,恍若晨曦,
354.7萬字8 57206 -
完結70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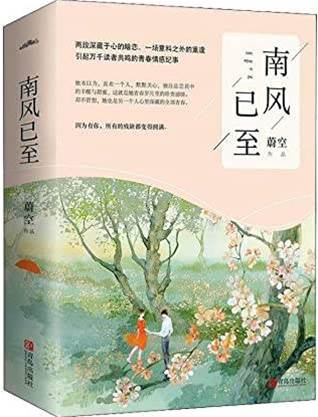
南風已至
——我終于變成了你喜歡的樣子,因為那也是我喜歡的樣子。 在暗戀多年的男神婚禮上,單身狗宋南風遇到當年計院頭牌——曾經的某學渣兼人渣,如今已成為斯坦福博士畢業的某領域專家。 宋南風私以為頭牌都能搖身一變成為青年科學家,她卻這麼多年連段暗戀都放不下,實在天理難容,遂決定放下男神,抬頭挺胸向前看。 于是,某頭牌默默站在了她前面。
22.2萬字8 6582 -
完結491 章

裴教授,你行不行啊
絕世小甜文,年齡差,先婚后愛,1v1雙潔,斯文敗類教授X古靈精怪富家女。劇情一:葉允澄可憐巴巴的看著裴修言:“老公,我作業沒寫完,你跟我們導員熟,你跟她說一聲讓她別檢查作業了好不好。”裴修言抿唇不說話。結果第二天,導員只檢查了葉允澄一個人的作業...下班回家的裴修言發現家空了一大半,葉允澄不見了...
97萬字8 44785 -
完結183 章

乖吝
【甜寵&雙暗戀&校園到婚紗&雙潔&救贖】(低調清冷富家大小姐&痞壞不羈深情男)高三那年,轉學至魔都的溫歲晚喜歡上了同桌校霸沈熾。所有人都說沈熾是個混不吝,打架斗毆混跡市井,只有溫歲晚知道,那個渾身是刺的少年骨子里有多溫柔。他們約好上同一所大學,在高考那天她卻食言了。再次相見,他是帝都美術學院的天才畫手,是接她入學的大二學長。所有人都說學生會副會長沈熾為人冷漠,高不可攀。卻在某天看到那個矜貴如神袛的天才少年將一個精致瓷娃娃抵在墻角,紅著眼眶輕哄:“晚晚乖,跟哥哥在一起,命都給你~”【你往前走,我在身后...
32.4萬字8 9635 -
完結872 章

誘捕玫瑰
五年前,溫棉被人戳着脊樑骨,背上爬養兄牀的罵名。 所有人都說她是個白眼狼,不懂得感激裴家賜她新生,反而恩將仇報。 只有她自己知道,這所謂的恩賜,只是一場深不見底的人間煉獄。 五年的磋磨,溫棉險些死在國外。 重新回來時,她煥然一新,發誓要讓裴家的所有人付出代價。 本以爲這是一場孤注一擲的死局。 卻沒想到,這個將她送到國外的養兄,卻跟個甩不掉的牛皮糖一樣跟在身後。 她殺人,他遞刀,她報仇,他滅口。 終於,溫棉忍不住了—— “你到底要幹什麼?” 而那隱忍多年的男人終於露出了尾巴:“看不出來嗎?我都是爲了你。”
84.4萬字8 2103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