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諸事皆宜百無禁忌》 第47章 宜訪舊 秋欣然每日就在這樣的動靜里醒……
安仁坊中的何記飯館卯時天未亮就已經開門做生意了。
夫妻兩個通常寅時起, 何寶進在后院的廚房里將昨晚早就備下的東西搬出來,用蒸籠蒸上包子饅頭,煮上一大鍋粥。陳氏則在廚房“叮叮當當”地準備配菜。到辰時, 飯館里頭基本上就坐滿了客人。不急著趕路的, 坐店里點上一碗白粥配上幾個爽口小菜, “呼嚕呼嚕”地就能喝掉一大碗;若是有事急著趕路的,那就揣上兩個饅頭, 路上當做干糧。
小小的飯館每天早上都著忙忙碌碌的煙火氣, 秋欣然每日就在這樣的靜里醒過來,有時睜開眼睛, 恍惚還在山里,可山里沒有這樣喧鬧的人聲。
起床洗漱時又看見掛在茶室屏風后繡工巧的袍子,站在架前出了會兒神, 過一會兒嘆了口氣, 才下樓準備用飯。
何寶進有個十七歲的閨名秀兒,是個活潑開朗的姑娘又十分能干,整日躲在后院的廚房給家里幫忙。秀兒還有個哥哥,比大上三歲, 名勇兒。勇兒長相忠厚子靦腆, 則在前面跑堂。一家人原先對住在樓上的這位房東十分客氣疏離,但隨著相的日子久了,倒也生出幾分親近來。尤其是姐弟兩個, 儼然已將當了樓上鄰居家的姐姐。
秀兒早上在大堂幫忙盛粥, 見下來高高興興地把早就準備好的早飯替端過來:“道長今天出不出攤?”
秋欣然從一旁的筷籠里取了一雙筷子出來, 同打趣:“怎麼,你要照顧我生意嗎?”
“我可付不起請您算卦的銀子。”秀兒吐吐舌頭。
秋欣然便說:“那等你什麼時候準備相看人家了,我替你合個八字。”小姑娘臉皮薄, 一說這個立即臉紅起來,道:“我哥都沒娶上媳婦,哪兒得到我,要合也是請你替我哥合。”
Advertisement
“你又在這兒胡說什麼?”何勇走過來,皺著眉頭趕,“不幫忙倒還在這兒打擾道長用飯。”
何秀兒沖他做了個鬼臉:“你自己想著懶倒還說我,別以為我不知道你晚上和隔壁王生他們約好要去芳池園!”
何勇聞言一愣,慌道:“你……你胡說什麼!”
何秀兒見他這副模樣,忍不住捂笑起來:“好好好,我胡說。不過你可別娘知道了,否則小心打斷你的!”
何勇上前一步,就要去捂的,小丫頭矮著子一溜煙跑了。等回過神便瞧見桌邊坐著的冠好奇地盯著他問:“芳池園是什麼地方?”
何勇臉皮漲紅:“你別聽那小丫頭胡說,芳池園是個樂坊。”
秋欣然還是不解:“你去聽曲兒你娘知道了就要打斷你的?”
何勇覺得臉更燙了,他左右張著結結道:“不是,我……我不準備去,秀兒胡說哪!”
便是聽個曲兒也沒什麼,秋欣然還是不大明白。不過還不等再問,店外忽然有人走進來,朝喊了一聲。秋欣然轉過頭,發現是個穿長袍,頭戴蓮花冠的青年,看清來人不由眼前一亮:“原舟?”
同七年前相比,原舟倒是沒什麼變化,不過瞧著倒比以前結實了些。秋欣然領著他去二樓轉了一圈,原舟扶著木梯往上走的時候一邊問:“你既然回來了,怎麼住在這兒?”
秋欣然反問:“住在這兒有什麼不好?這兒還是你替我挑的地段。”大約也想起舊事,原舟笑一笑:“但你自己要住,怎麼還將大半間鋪子租出去?”
“我一個人住這兒也不大安全。”秋欣然不以為意,“何況老何做飯的手藝不錯,我住這兒也方便。”
這樣說,原舟便也不再多勸。二人在茶室走了一圈,在窗邊坐下來。秋欣然替他倒了杯水,總算談起正事:“你今天是特意過來看我?”
原舟端起杯子喝了一口,回答道:“原是得了消息打算派人上山去通知你的,但沒想到你已經知道了,于是便來看看。”
“什麼消息?”
原舟一愣:“怎麼,你不是聽說那人也在長安才下山來的?”
秋欣然一頭霧水:“誰?”
二人坐在這嘈雜的小飯館里面面相覷了一會兒。異口同聲:
秋欣然:“你說的該不會是——”
原舟:“就是七年前隨余音離開長安的那位小梅姑娘。”
秋欣然一頓,恍然大悟:“是!”原舟卻是一臉狐疑地看了過來:“你方才想要說誰?”
紫冠別開臉掩飾一般地咳了聲:“沒有誰,你打聽到的下落了?”
青年瞧著的目還有些狐疑,不過到底沒有深究:“如今在芳池園。”
芳池園?
秋欣然覺得這地方聽著耳,過了片刻才想起方才剛在樓下聽何氏兄妹提起過,不由好奇道:“我聽說那是個聽曲兒的去?”
“咳——”問到這個原舟神有些尷尬,他握拳抵,仔細斟酌了一番才委婉道,“那確實是個樂坊不假,不過你知道世道艱難,里頭有些姑娘保不齊也做做別的生意。”
秋欣然一愣,顯然聽懂了他的言下之意,不由沉默下來。原舟瞥了眼的神,又說:“不過你也別瞎想。芳池園這兩年在長安名聲很大,里頭的客人下到文人雅士上到朝中大員,就是閨閣里聽曲的小姐也有請里頭的樂師到府里做客的,可見不是什麼見不得人的地方。”見臉稍緩,原舟又道,“聽說那位小梅姑娘如今也改了名字,做梅雀,正是園中極捧的樂伶。”
算算年歲,應當也有十七八了,正是如花似玉的年紀。秋欣然問:“余音哪?”
“他去年過世了,梅雀也是那時候的芳池園。”
“好端端的,怎麼就過世了?”
“大約是生了病,不過聽人說他去世前兩年境不太好,也不知發生了什麼。”原舟看一眼,“你可要去見見?”
“去吧,”秋欣然沉片刻,“心中有牽掛,見過或許便能放下了。”
二人約著黃昏后一塊去芳池園,于是太落山的時候,原舟雇了輛馬車到何記飯館外等。秋欣然特意換了男裝,上車的時候原舟看見一愣。
“怎麼了?”忍不住低頭理了理袖,檢查了一遍可有什麼不對的地方。
“倒也沒什麼……”原舟失笑,“就是不免有些蓋彌彰。”
秋欣然較一般子要高一些,按理說這量扮作男子正合適。但十四五歲時還未長開,男裝打扮還有些男未分的年。可如今二十出頭,雖能看出已裹了束,但還是難掩子形,于是不但能人一眼看穿是扮男裝,還平添了幾分說還休的意。
“總也不好穿著道袍過去。”秋欣然擺擺手,“本也是送銀子的事,大家心知肚明互不穿也就是了。”
倒是心大,原舟聞言坐正子正道:“先要說好,我這回可是陪你去的,若非如此……”
“曉得了,”秋欣然今日手上還特意拿了把折扇,拍拍對方的肩膀安道,“此事必不會老師知道,今晚的費用也都算在我的賬上。”
原舟這才放松些,又打量一眼:“你上這袍子有些眼。”
秋欣然握著扇子的手一,不自然道:“因你白天說那地方只招待貴客——”
“于是你便去借了這一行頭?”原舟循著的話猜測道,見遲疑一下未立即應聲,便自覺是猜對了,不由嘆道,“現如今外頭的鋪子竟也有這麼好的手藝了?看這紋樣不比宮里制局的師傅們手里出來的遜,確實很能唬人,想來你借這一套也要花上不銀子吧?”
“你說得不錯,”秋欣然嘆一口氣,“這服可不敢有一點閃失。”
二人坐著馬車到芳池園時,正是傍晚,天邊布滿了紫的煙霞。跳下馬車的時候,秋欣然原以為會看見一幢金碧輝煌的戲樓,卻不想眼前是座環境清幽的莊園,像是哪個大戶人家的宅院,園門大開著,上頭寫了“芳池園”三個字。外頭停滿了馬車,卻不見尋常館那些在外頭攬客的子。
秋欣然跟著原舟往里走,神間難掩新奇。倒是原舟白日同說得振振有詞,當真到了這地方,卻總覺渾不自在,神也是滿臉的不自然。
園里假山清泉遍布其間,亭臺水榭高低錯落,傳來笑語。有丫鬟上前招待,秋欣然聽見遠傳來一陣琴聲,循著聲音看過去,卻樹蔭擋住了視線:“不知梅雀姑娘在哪院?”
丫鬟名小玉,聞言了然道:“梅雀姑娘在品冬院,通常只接貴客。”
“怎麼才算貴客?”
小玉掩笑了笑:“一擲千金為貴。”
“一擲千金?”原舟皺眉道,“當真有人會出這麼多銀子聽曲嗎?”
“自然是有的。”小玉倒不嫌他大驚小怪,還是和和氣氣道,“且不哪,若是上好幾位貴客,一晚上再多銀子也不足為奇。”
原舟說不出話,他看了眼旁默不作聲的人,試探道:“怎麼說?”
“今晚可有人請梅雀姑娘作陪?”
“二位來得早,品冬院還未有貴客。”
原舟見旁的人沉默,悚然一驚:“你該不會真打算花上這許多銀子見一面吧?”秋欣然還沒說話,那丫鬟又補充道:“二位不知,這品冬院也不是靠銀子人人都能進去的,第一回 來的,還得有貴人引薦才可。”
“什麼人才算得上是貴人?”
“達顯貴為貴。”
秋欣然指著旁的青年:“我要說這位在朝中位居四品,你就讓我們進去?”
猜你喜歡
-
完結2088 章

廢柴王妃又在虐渣了
蕭涼兒,相府大小姐,命格克親,容貌被毀,從小被送到鄉下,是出了名的廢柴土包子。偏偏權傾朝野的那位夜王對她寵之入骨,愛之如命,人們都道王爺瞎了眼。直到人們發現,這位不受相府寵愛冇嫁妝的王妃富可敵國,名下商會遍天下,天天數錢數到手抽筋!這位不能修煉的廢材王妃天賦逆天,煉器煉丹秘紋馴獸樣樣精通,無數大佬哭著喊著要收她為徒!這位醜陋無鹽的王妃實際上容貌絕美,顛倒眾生!第一神醫是她,第一符師也是她,第一丹師還是她!眾人跪了:大佬你還有什麼不會的!天才們的臉都快被你打腫了!夜王嘴角噙著一抹妖孽的笑:“我家王妃肩不能挑手不能提,是個柔弱小女子,本王隻能寵著寵著再寵著!”
400.4萬字8.08 204045 -
完結1816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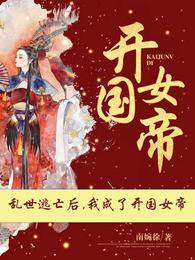
亂世逃亡后,我成了開國女帝
◣女強+權謀+亂世+爭霸◥有CP!開局即逃亡,亂世女諸侯。女主與眾梟雄們掰手腕,群雄逐鹿天下。女主不會嫁人,只會‘娶’!拒絕戀愛腦!看女主能否平定亂世,開創不世霸業!女企業家林知皇穿越大濟朝,發現此處正值亂世,禮樂崩壞,世家當道,天子政權不穩,就連文字也未統一,四處叛亂,諸王征戰,百姓民不聊生。女主剛穿越到此處,還未適應此處的落后,亂民便沖擊城池了!不想死的她被迫逃亡,開
238萬字8.18 16115 -
完結129 章

盛寵
【全文完結】又名《嫁給前童養夫的小叔叔》衛窈窈父親去世前給她買了個童養夫,童養夫宋鶴元讀書好,長得好,對衛窈窈好。衛窈窈滿心感動,送了大半個身家給他做上京趕考的盤纏,歡歡喜喜地等他金榜題名回鄉與自己成親。結果宋鶴元一去不歸,并傳來了他與貴女定親的消息,原來他是鎮國公府十六年前走丟了的小公子,他與貴女門當戶對,郎才女貌,十分相配。衛窈窈心中大恨,眼淚汪汪地收拾了包袱進京討債。誰知進京途中,落難遭災,失了憶,被人送給鎮國公世子做了外室。鎮國公世子孟紓丞十五歲中舉,十九歲狀元及第,官運亨通,政績卓然,是為本朝最年輕的閣臣。談起孟紓丞,都道他清貴自持,克己復禮,連他府上之人是如此認為。直到有人撞見,那位清正端方的孟大人散了發冠,亂了衣衫,失了儀態,抱著他那外室喊嬌嬌。后來世人只道他一生榮耀,唯一出格的事就是娶了他的外室為正妻。
31.9萬字7.92 62628 -
完結99 章

和死對頭成婚后
六公主容今瑤生得仙姿玉貌、甜美嬌憨,人人都說她性子乖順。可她卻自幼被母拋棄,亦不得父皇寵愛,甚至即將被送去和親。 得知自己成爲棄子,容今瑤不甘坐以待斃,於是把目光放在了自己的死對頭身上——少年將軍,楚懿。 他鮮衣怒馬,意氣風發,一雙深情眼俊美得不可思議,只可惜看向她時,銳利如鷹隼,恨不得將她扒乾淨纔好。 容今瑤心想,若不是父皇恰好要給楚懿賜婚,她纔不會謀劃這樁婚事! 以防楚懿退婚,容今瑤忍去他陰魂不散的試探,假裝傾慕於他,使盡渾身解數勾引。 撒嬌、親吻、摟抱……肆無忌憚地挑戰楚懿底線。 某日,在楚懿又一次試探時。容今瑤咬了咬牙,心一橫,“啵”地親上了他的脣角。 少女杏眼含春:“這回相信我對你的真心了嗎?” 楚懿一哂,將她毫不留情地推開,淡淡拋下三個字—— “很一般。” * 起初,在查到賜婚背後也有容今瑤的推波助瀾時,楚懿便想要一層一層撕開她的僞裝,深窺這隻小白兔的真面目。 只是不知爲何容今瑤對他的態度陡然逆轉,不僅主動親他,還故意喊他哥哥,婚後更是柔情軟意。 久而久之,楚懿覺得和死對頭成婚也沒有想象中差。 直到那日泛舟湖上,容今瑤醉眼朦朧地告知楚懿,這門親事實際是她躲避和親的蓄謀已久。 靜默之下,雙目相對。 一向心機腹黑、凡事穩操勝券的小將軍霎時冷了臉。 河邊的風吹皺了水面,船艙內浪暖桃香。 第二日醒來,容今瑤意外發現脖頸上……多了一道鮮紅的牙印。
25.2萬字8 140 -
完結123 章

不是聯姻嗎?裴大人怎麼這麼愛
姜時愿追逐沈律初十年,卻在十八歲生辰那日,得到四個字:‘令人作嘔’。于是,令沈律初作嘔的姜時愿轉頭答應了家里的聯姻安排,準備嫁入裴家。 …… 裴家是京中第一世家,權勢滔天,本不是姜時愿高攀得起的。 可誰叫她運氣好,裴家英才輩出,偏偏有個混不吝的孫子裴子野,天天走雞斗狗游手好閑,不管年歲,還是性格,跟她倒也相稱。 相看那日—— 姜時愿正幻想著婚后要如何與裴子野和諧相處,房門輕響,秋風瑟瑟,進來的卻是裴家那位位極人臣,矜貴冷肅的小叔——裴徹。 …… 裴太傅愛妻語錄: 【就像御花園里那枝芙蓉花,不用你踮腳,我自會下來,落在你手邊。】 【愛她,是托舉,是陪伴,是讓她做自己,發著光。】 【不像某人。】
23.8萬字8.09 92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