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奮鬥在新明朝》 四百三十三章 李太守三連擊
國朝京比地方清貴的現象確實存在,例如從二品布政使遷爲三品副都使和侍郎,往往就被視爲升,七品知縣被遷爲七品史,同樣也被看做升。
反過來,去年年初李佑以六品中書舍人的職,被外放知江都,雖品級沒變,但人人都視爲貶,是該同的。爲此李佑自己也寫詩道“天門哭罷朝南來”,十分厚的拿楊慎來比喻自己。
更別說不翰林的區別了,所以在前幾日,七品翰林編修李登高面對五品地方李佑時底氣十足,高傲的說“本清流華選,你這風塵俗吏算得了什麼”這種況。
李編修的話在場算是“話糙理不糙”,換作別的地方,也只能含忍辱,只可惜他這次用錯了對象。那功勳卓著的半勳貴半名臣李佑比李登高更加傲氣,皮子加兇狠,直接還將李登高罵到無完,辱的李大翰林要投水自盡。
話說回來,京比地方爲貴其實並沒有明確的制度去規定,更多的是一種傳統和心理。之所以出現這種現象,也有國朝初年擡高朝廷、抑制地方、加強大一統集權的政治需要因素在,好就是使得大明地方完全沒有造反能力。
隨駕大臣中,大學士袁閣老是首座,天子金口玉言不方便說話時,他必須要出面應付。
但李佑的一連串問題太尖銳,直面地方與京的利益衝突,十分不好回答。打太極拳又缺乏理論依據,四書五經裡也沒什麼話可以套用在這方面。
一般地方爲了前途命運誰敢這樣放肆?偏偏李佑是個另類,大不了抱著金書鐵券和世襲三品回家養老的另類。
袁閣老還有一點顧慮,他爲宰輔大學士,說話隨意程度可能遠不如李佑這樣的。他對政策的事務發言,很容易被天下人過度解讀,產生若干不測的後果。
Advertisement
另外,若非迫不得已,他絕對不想和李佑公開爭辯,這是幾次廷前奏對得來的教訓。
最後袁閣老謹慎的開口道:“李大人休要君前失儀!朝廷有朝廷的考量,你做好自己迎駕本分即可,不要在這裡議朝政,脅迫聖上。若有見解,可上疏言事,朝廷自有公議!”
李佑眼看第一個目的快達到,立刻拿出見好就收的勢頭。挑起這個尖銳話題,是他的第一擊,最主要就是爲了變相誇耀自己治理地方的功績而已。
他知道,天子周圍這圈隨駕大臣中很難有人爲他說好話,便製造出話題,通過辯白巧妙的將自己治理地方功績表述一番。
而且越激烈的話題,越容易流傳,順帶也就將他的功績傳出去了。至於後癥,他除了李登高,沒有針對任何個人,應該不會太嚴重…
不然即使是再無恥的人,也沒法厚著臉皮自吹自擂道,我勞苦功高,我治理地方井井有條,我這裡百姓安居樂業…
李大人隨即向景和天子請罪道:“袁閣老所言極是,確實是臣的過錯了。那日臣被李編修辱罵爲風塵俗吏,自思兢兢業業卻橫遭如此侮辱,又又慚之下恨不能投水自盡,但卻知爲臣不可荒廢王事,勉強茍延至今。不想今日又遭李編修惡言相加,實在忍不住一時憤激,險些誤了陛下南巡盛典,罪莫大焉!”
這名爲請罪實際還是訴委屈,袁閣老知道李佑難纏,只求李佑不死纏爛打即可,見李佑不再提京地方什麼的爲難天子,當即閉不言。
不過已經李佑無打擊到半晌沒有說話的李編修忽然聽到李佑冷不丁再次將自己單獨拎出來辱,登時睚眥裂,險些撲上前去拿住李佑大吼一聲,你到底想怎樣?那天最後被辱到跳水的是我而不是你,你現在裝可憐未免太假了!
見李佑舊事重提,衆人心中暗歎,李編修還是太年輕了,中探花翰林過於興得意,心浮氣躁的渾然不知場風波險惡。
風塵俗吏這種京用來取笑地方的話,已經了固定的用語。心裡想想或者私下裡說說也就罷了,非要公然當面以此去貶低別人,朝廷制上並沒有明文規定京比地方高貴,絕對是政治錯誤。
所以很容易被人抓住大題小做,如果李佑真要狠了心,發關係廣泛串聯,一起蜂擁上奏彈劾李編修,纔是大麻煩。天下有一千多個縣和數百個府州,再也可以招呼到百八十個人的。即便朝廷優容詞林之臣,面對羣洶洶,也不可能無原則的袒護。李佑剛纔大談地方與京區別,又何嘗不是造聲勢?
其實這便是李佑的第二擊了,就是將李登高貶斥不堪任用的反面典型,襯托出自己的英明神武。
無論什麼類別聲,只要有刷的機會,無功名靠聲起家的李佑從來不憚於出手的。
而那李登高年紀輕輕,才二十幾歲就中探花翰林,坐上了快速上升的直通車。不是萬衆矚目也相差不遠了,看起來確是人中龍,未來宰輔熱門人選。這麼年輕就是翰林,熬年頭也能熬大學士了。
恰恰也因爲“李探花”三個字,又與李佑同樣年輕,所以常被人一起提起。
李揚州眼中,李登高負儲相之,做技又弱得很,還敢辱自己,不刷他刷誰?
清流侮辱濁流,在崇尚清流的大環境下常常被當做場談,現實就是這麼殘酷。如果李佑不狠狠地報復回去,將李登高踩到泥裡,自己就真要李登高趣聞的背景了。
在李佑毫不留的連番打擊之下,是非先不論,但李登高這水準徹底顯示出來了。場中不但講門面功夫,也要講叢林法則。也就是說,不但要看是非,還要看水準,有時候水準太差,是也變非了。
即便是偏袒李登高的人也不得不承認,李登高與李佑相比較,大部分方面差的太遠太遠。換句話說,李佑比擁有“儲相”環之人強的太多太多…
如遇此此景,李佑的名義師長陳巡道只怕會慨,難怪當初他中了進士後被老師送到縣裡低調做。不然以他二十四年紀翰林,絕對也要面臨李登高這樣的境。
年輕儲相的環,看似芒萬丈,但也了芒萬丈的靶子,在無數明槍暗箭的夾攻下真不是那麼好混的。
從這個角度,同樣年輕的李佑沒功名反而不是壞事,大家都知道他前途有限,肯定無緣尚書或者大學士,反而減輕了很多力。
說到底,還是要怪李翰林修爲太淺,如果他能堅守本心,不心浮氣躁,李佑的魚餌又豈能勾上他來?
不過翰林院與別的衙門不同,部還算團結,而且翰林院員之間不庸俗的用品級論大小,只以科年論前後輩。在場人中,侍讀學士白翰林就是李編修的前輩,李登高被攻擊的撐不住了,白翰林總該出來打圓場。
明知李佑從頭到尾一直是故意挑逗,怎奈李登高實在不爭氣,白前輩只得出面道:“李編修無心之失,言辭不當,回京後我翰林院理當罰他。李太守大人大量,勿要耿耿介懷,且放寬心思,不必與失言之人計較。”
這話其實也暗諷李佑心狹窄,小肚腸,爲了幾個字而斤斤計較,有失風度,事實上隨駕大臣出於同仇敵愾心態都有這種覺。
李佑早有準備,又不慌不忙的放出了第三擊。拱手爲禮道:“白學士多慮了,我豈敢爲自己介懷?我爲我師不平而鳴!”
這算哪一齣?白翰林莫名其妙的問道:“你師又是何人?”
不得不說,衆人無論敵友都對李佑彷彿憑空冒出的師承很好奇。只見李佑一臉恭敬,“乃是景和五年春闈的第五名,陳東山公!”
景和天子這幾天爲了預備親政,經常翻看朝臣名錄,卻記不起有這個人。不疑道:“朝臣之中,未聞其人,莫非歸了?”
李佑答道:“東山公諱英楨,不在朝,由知縣升蘇鬆按察僉事。”
衆人除了李編修,紛紛記起來“陳東山公”是什麼人。前幾年時,陳英楨這僅次於狀元、榜眼、探花、傳臚的新科高位次進士沒有留京,卻去了地方任知縣,還是相當引人注目的。
袁閣老迅速的醒悟到,李佑此時提起陳英楨,絕非無緣無故,今天他在舟上的激辯,肯定可以完收了,爲了師長力爭在什麼時候也是場德。其他人從頭到尾全了他的圈套!
果然,李佑開始滔滔不絕的吹捧道:“東山公品行高潔,道德純粹,才幹卓越,卻不慕廟堂之紛華,甘親民之苦累…”
如果陳英楨猛然聽到這段溢,只怕也不知道說的是自己。隨即李佑話音一轉,又不知是第幾次將李登高扯了出來。
“這李翰林與我師同爲名列前茅的進士,年紀相差不多,相較之下,李翰林顯得輕浮無能!然而卻中外矚目,視爲儲相,一有過錯,上下袒護,彼此遮掩,文過飾非!簡直就是矇蔽聖君!”
“而我師東山公,難道憑藉科名進不了翰林院麼!只是他謙虛自謹,唯恐才不足而致誤國,甘願臨民地方,磨練治政之,卻至今幾爲人所忘!如此英才連聖上也不知,只留李登高之流伴駕,這般遭遇,豈能不令我心寒而憂憤!故而我爲我師不平而鳴!”
無數次被李佑拿出來當陪襯的李登高臉發白,不知所措,真正認識到了場上的殘酷無之。如果給他一個機會,打死他也不會罵李佑“風塵俗吏”了,難怪文華殿大學士袁閣老死活不出頭!
猜你喜歡
-
連載2286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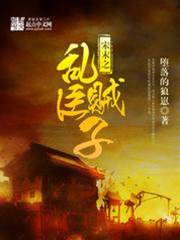
宋末之亂臣賊子
李璟穿越到北宋末年,成為梁山附近獨龍岡李家莊撲天雕的兒子。從此歷史的車輪就在這裡轉了一個彎。 他是宋徽宗的弟子,卻使趙家諸子奪嫡,自己在暗地裡挖著大宋的牆角;他是宋欽宗的股肱之臣,卻睡了龍床,奪了他的江山。 鐵蹄踐踏,盛唐雄風依舊;美人多嬌,風流千古。
439萬字8 11058 -
完結2785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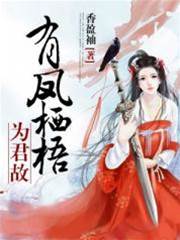
傾城毒妃:邪王寵妻無度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還他一針!人再犯我,斬草除根!!她,來自現代的首席軍醫,醫毒雙絕,一朝穿越,變成了帝都第一醜女柳若水。未婚被休,繼母暗害,妹妹狠毒。一朝風雲變,軟弱醜女驚豔歸來。一身冠絕天下的醫術,一顆雲淡風輕的心。翻手為雲,覆手為雨,棋子反為下棋人,且看她素手指點萬裡江山。“江山為聘,萬裡紅妝。你嫁我!”柳若水美眸一閃,“邪王,寵妻……要有度!”
513.1萬字8 60740 -
完結1256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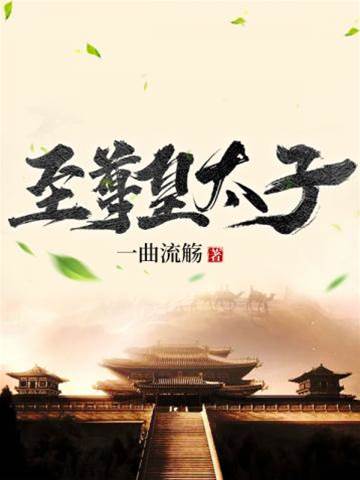
至尊皇太子
李塵穿越大唐,竟然成了東宮太子? 偏偏朝中上下,對他都是頗有微詞。 也好,既然你們不服,那本宮就讓你們服! 從此,李塵成了整個華夏歷史上,最囂張霸道的太子爺! 能經商,會種地,開疆拓土,統御三軍。 大觀音寺老方丈曾經斷言:“有此子在,這大唐,方才稱得上真正的盛世!”
237.7萬字8 40875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