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騷》 第440章 血紅雪白
在棋盤天街南端有一家陸氏飯店,距離蔚泰酒樓大約一裡路,出飯店左轉南行數百步就是巍峨的正門,在北京城,陸氏飯店是屈指可數的大客棧,單是廚房就有二十余間,酒保、夥計、妖冶、奔走服役者不下兩百人,飯店每日進出的客人也是以百人計,在這臨近年關的臘月下旬,客棧也未見冷清,住客唱曲聽戲、飲酒作樂,夜以繼日,宵只是止民眾夜晚上街外出,並不民眾待在宅中徹夜尋歡——
臘月二十日亥時初,當錦衛和南城兵馬司的軍士在大雪紛飛下列隊出正門時,陸氏客棧臨街二樓的一間客房窗前立著一個儒生打扮的男子,這男子年近三十,量頗高,形壯實,整相貌除了那張紅臉膛之外並無其他出奇之,八字眉下那雙細長眼還顯得困得睜不開似的沒什麼神——
這男子擱下手中的一卷《三國演義》,推開窗欞,任寒風灌客房,迎著徹骨的寒風還將冬氈帽摘下,又將結髻的頭髮輕輕一提,另一手探發底,輕輕挲頭皮,卻原來是個頭,不,並非全禿,頭頂心留有金錢大小的一綹頭髮,後腦杓玉枕也留了一束,各結著一細辮,為避免辮子下垂餡,這一上一下兩辮子還連接在一起,這種古怪的髮型極其醜陋——
“頭皮甚——”
這扮儒生模樣的真男子挲了一會頭,將假發髻戴好,居高臨下看著大街上匆匆跑過的錦衛和兵馬司的軍士,對後那個瘦勁拔的青年男子說道:“這些人是出正門搜索我和昂阿的嗎,這真是奇怪了!”
後那青年男子道:“翟東勝是南朝漢人,靠不住,定是他招供出旗主是住在正門外,所幸旗主早有防備,不然就危險了。”
Advertisement
這被稱為旗主的真男子道:“倒未見得是翟東勝招供的,好些個蔚泰酒樓的夥計都知道我住在正門外,只是這些南朝吏這麼快就追查到我頭上,實在大出我所料,翟東勝不是那麼愚蠢的人啊,怎麼就餡了!”
青年男子道:“旗主,明日一早我們就出城回寬甸吧,這裡境很危險,要盡快出山海關。”
那旗主皺著八字眉道:“昂阿還在正門外,可不要落在南朝人之手,此時宵,又無法通知他。”
青年男子沉默了一會,說道:“昂阿心如鐵石,對旗主無比忠誠,寧死也不會背叛旗主的。”
那旗主道:“明日我們先設法通知昂阿,若不能,那就搬到朝門外,靜觀其變,我此次來北京,離間漢、鮮是其一,更是要為我父汗找到那個人,那個人沒有死,而是早就來了南朝——”
……
臘月二十一日天亮之前,正門外的永定、左安、右安、廣渠、廣安這外城五門已經接到錦衛的命令封鎖城門,數百名錦衛力士和兵馬司軍吏逐一搜查各家客棧,同時各坊廂裡正也與坊丁盤查有外客的民戶,至午後,有幾十名沒有戶籍的紅臉人和啞被帶到南城兵馬司衙門,由蔚泰酒樓的三個酒保辨認,十幾個紅臉人很快被驗看過,三個酒保都是搖頭,待二十多名啞被帶上來,三個酒保一齊指著其中一個形壯的中年漢子道:“就是他!”
這頭顱碩大、脖頸短的漢子沒等左右軍吏上前擒拿,驀地縱起,怪吼一聲,撲向一丈外的南城兵馬司指揮使方世熊,方世熊年過五十,雖也是武舉出,但畢竟年紀大了,反應稍慢,刀不及,隻好使出劈掛拳的轆轤勁,
臂腕一合,朝兇猛撲至的啞壯漢撞去,只要緩得一緩,不讓這啞近,自有兩邊的軍吏衝上來攔截,豈料這啞力氣大得異乎尋常,一拳就將方世熊的右臂砸斷,另一手五指戟張,直接就叉在方世熊咽上,手一,方世熊頓時面皮紫脹,無法呼吸——南城兵馬司副指揮趙鎮東拔刀怒喝:“好賊,敢當堂行兇!”
啞叉著方世熊的脖頸,拖著就往堂外行去,副指揮使趙鎮東等人投鼠忌,都不敢過於迫近,眼看就要被那啞挾持著方世熊出南城兵馬司衙門,正這時,錦衛百戶甄紫丹帶著十余名校尉趕到,甄紫丹可不管方世熊死活,大喝一聲:“昂阿——”
這啞正是正白旗的牛錄額真昂阿,陡聽有人他名字,不一愣,下意識地應了聲:“喳。”此真奴才也。
“喳”音未落,甄紫丹出鞘的繡春刀如一泓春水,刀鋒映著雪朝昂阿當頭便劈,昂阿怒吼一聲,竟雙手把百余斤重的方世熊舉了起來,用方世熊的當盾牌來擋甄紫丹的刀,甄紫丹在錦衛中算得刀法好手,手腕一擰,刀鋒變向,閃電一般向下橫削,這也是劈掛拳的轆轤勁,變招迅捷,昂阿雖然力大,但畢竟不能把方世熊當作槍棒一般舞得不風,而且昂阿擅長的是馬戰,沒有了馬就顯得笨拙,隻覺右腕一涼,鋒利的刀刃削過,左手齊腕而斷——
昂阿的左手本來是扼著方世熊脖頸的,現在被一削而斷,方世熊的上凌空無支撐,就往下一栽,腦袋重重砸在青磚地上,痛得大一聲,而昂阿的那隻斷手卻依舊扼在他脖子上,只是已經沒有了力氣,方世熊呼吸一暢,大口大口地氣——
副指揮使趙鎮東從後一腳猛踹,踢中昂阿後心,昂阿只是向前一個踉蹌,並未摔倒,單手揪著方世熊的牛脂皮鞓帶,把方世熊一個大活人掄著左右砸,甄紫丹退後數步,又欺直,又是一刀劈在昂阿右臂上,右臂沒斷,但已揪不住方世熊,便將方世熊甩落在地,吼著大步奔出,兩邊灑,在積雪的道路上目驚心。
甄紫丹從一個差役手中奪過一木杖,飛步趕上,對著昂阿後膝猛掃,杖斷折,昂阿滾倒在雪地上,再也掙扎不起來,隻將下的白雪攪紅雪。
甄紫丹丟下手中斷杖,對趕上來的趙鎮東等人道:“若讓這真細挾持了人出城門,那我大明武人的面何在!”
趙鎮東等兵馬司員吏役個個覺得面無,錦衛的人又一次把他們得死死的,再看指揮使方世熊方大人,被摔得口吐白沫,昏迷不醒——
甄紫丹讓手下校尉給昂阿簡單止,綁起來押回北鎮司衙門,由千戶王名世親自審訊,把翟東勝押出來對質,又找來通真人通古斯語的通事來審問昂阿,昂阿死也不肯說出那個紅臉書生的下落,真把自己當作了啞——
這日傍晚時分,甄紫丹穿了一便服,候在翰林院大門外,見張原和幾個翰林走了出來,便恭恭敬敬叉手了一聲:“張大人。”
張原見是甄紫丹,便與文震孟等人道了別,與甄紫丹往玉河北橋行去,問:“甄百戶,蔚泰酒樓的案如何了?”
甄紫丹道:“卑職正是來向張大人稟報此事。”當即就將審問翟東勝、抓獲昂阿的事向張原一一說了。
要以殺人命案陷害朝鮮使臣者不外乎兩種人,一種人是朝鮮國中反對海君李氏王室或者與柳東溟有仇怨的朝鮮大臣,若柳東溟在大明京城犯了人命案,雖不至於要抵命,但因為柳東溟是海君的妻兄,國舅柳東溟聲譽有損對海君也是一個打擊, 更會增加大明朝廷對海君的惡;另一種人便是野心的真人,再過幾天就是萬歷四十五年了,離奴酋奴爾哈赤以“七大恨”為由反明只有一年多時間,如今的奴爾哈赤早已不是當年那個得到明朝敕封就沾沾自喜的奴爾哈赤了,這奴酋的野心越來越膨脹,已有覬覦大明江山的企圖,派出細打探大明政務軍、離間大明與朝鮮的關系,這都是極有可能的事,只是張原沒料到來大明行此離間計的會是皇太極!
——皇太極是奴爾哈赤的第八子,其母是葉赫部的孟古哲哲,奴爾哈赤完善八旗製後,四大貝勒之一的皇太極就是正白旗的固山額真即旗主,張原並不知道皇太極原名是黑還,但昂阿為正白旗牛錄額真卻甘當那書生的隨從仆役,那書生又是紅臉,不是皇太極還會是誰,皇太極通滿、蒙、漢多種語言,喜讀《三國》,在野未開化、文明程度較低的建州真中算是文化人了,奴爾哈赤對漢人是極端仇視的,殺多於納降,而皇太極知道重用漢人來收買人心,並仿照明朝的吏制度健全滿州的政治制度,皇太極對大明的威脅遠勝奴爾哈赤,因為殺戮只會激起漢人的仇恨和殊死抵抗,而皇太極的政策才是讓滿州迅速壯大的主要原因——
“張大人?”
甄紫丹見張原雙眉軒,臉上神頗為古怪,便了一聲。
張原回過神來,叮囑道:“甄百戶,一定要抓到那紅臉書生,此人極有可能是建州老奴之子,抓到他是一件大功。”
猜你喜歡
-
完結1258 章
天尊溺寵:腹黑萌妃太囂張
她是二十一世紀特工界首席特工,一朝穿越成為火鳳國蘇族嫡女……傳聞,她廢物膽小如鼠!卻將一國太子踹廢,並且耍的團團轉……傳聞,她是整個火鳳國最醜之人!當麵紗掉下來時,又醉了多少美男心?麵對追求的桃花她正沉醉其中,某天尊卻隨手掐死丟進河裡……麵對強勢的男人,她氣呼呼的罵道:“你是強盜啊!”某天尊瞇起危險的眸子,強勢地圈她入懷道:“你知道強盜最喜歡乾什麼嗎?”
226.6萬字8.18 77800 -
完結1334 章
重生九零:肥妻,要翻身
葉姚重生回到1990年,跟大院男神訂婚的時候。這個時候的她,還是人人厭惡的大胖子,受盡欺淩。所有人都在唱衰(破壞)這段戀情。葉姚笑一笑,減肥,發家,狂虐人渣,漸漸變美成了一枝花。葉姚:「他們都說我配不上你,離婚吧。」厲鋮強勢表白:「想的美。婦唱夫隨,你在哪兒,我就在哪兒!」
154.2萬字8.18 145318 -
完結3036 章
龍魔血帝
生來隱疾困前程,蓋因魔龍盤神魂。龍血澆灌神魔體,孤單逆亂破乾坤。 原本想要平凡度過一生的少年,卻不斷被捲入種種漩渦之中,從此他便改變人生的軌道。 什麼是道?吾之言行即使道。什麼是仁?順我心意即是仁。不尊道不順仁者,雖遠必誅。
831.4萬字7.58 37944 -
完結521 章

帶著物資穿到年代搞事業
出生在富裕家庭從小衣來伸手飯來張口的文舒念,從冇想過自己有天會得到傳說中的空間。 本以為是末世要來了,文舒念各種囤積物資,誰想到自己穿越了,還穿到了一個吃不飽穿不暖買啥都要票的年代當知青。 在大家都還在為每天的溫飽而努力的時候,文舒念默默地賣物資搞錢讀書參加工作,一路上也結識了許多好友,還有那個默默陪伴在自己身邊的男人。 本文冇有極品、冇有極品、冇有極品,重要的事說三遍,因為本人真的很討厭極品,所以這是一本走溫馨路線發家致富的文。 最後:本文純屬虛構。
86.7萬字8 33679 -
完結163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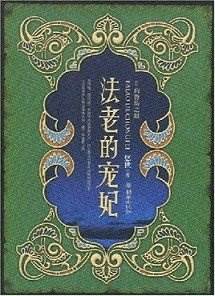
法老的寵妃
埃及的眾神啊,請保護我的靈魂,讓我能夠飛渡到遙遠的來世,再次把我帶到她的身旁。 就算到了來世,就算已經過了好幾個世紀,我和她,以生命約定,再相會亦不忘卻往生…… 艾薇原本是生活在二十一世紀英國侯爵的女兒,卻因為一只哥哥所送的黃金鐲,意外地穿越時空來到了三千年前的古埃及,而那只黃金鐲就此消失無蹤。艾薇想,既然來到了埃及就該有個埃及的名字,便調皮地借用了古埃及著名皇后的名字——「奈菲爾塔利」。 驚奇的事情一樁接著一樁,來到了古埃及的艾薇,竟還遇上了當時的攝政王子——拉美西斯……甚至他竟想要娶她當妃子……她竟然就這麼成為了真正的「奈菲爾塔利」!? 歷史似乎漸漸偏離了他原本的軌道,正往未知的方向前進……
71.2萬字8 5714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