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貼身丫鬟》 第56章 (小修)
喬三來了, 他和戴文軒一起進來,另外一個則是個生臉。
傅慎時還是親自陪他們玩兒。
殷紅豆依舊上了茶,看見喬三手上還帶著那塊白玉魚龍扳指,便提前準備好了一塊兒綢布放在炕桌上, 然后乖乖地站在傅慎時的后。
喬三坐下之后, 探究地看向傅慎時, 隨即道:“幾日不見,殷老板氣見好。”
傅慎時不言語, 淡淡一笑,道:“今兒喬公子想怎麼玩。”
喬三道:“就玩我和哥們常玩的, 一兩銀子打底, 翻番上不封頂。”
傅慎時點了點頭, 他這里的規矩基本也是這樣, 一局下來,贏家則贏取幾兩銀子,多則幾十上百兩的也有, 發財坊從大贏家手里十分之一。
殷紅豆默默腹誹, 哪里的有錢人都豪奢, 一把牌夠得上好幾個月的月例銀子。
很快就開了局, 傅慎時仔細應對,一共打了十幾圈,他贏了十圈左右。
喬三輸了也不急躁, 但是他跟戴文軒兩人喝茶喝得很快, 殷紅豆都去添了三四道茶水, 傅慎時邊的茶杯還沒過。
過了大半個時辰,殷紅豆都站酸了,喬三他們還沒有要走的意思,也只說著無關要的話,意識到不對了,喬三這樣的明家伙,吃不得虧,難道就白來給傅慎時送銀子的?
喬三喝茶喝得多了,和戴文軒二人流如廁,傅慎時穩坐不,洗牌牌,面從容。
殷紅豆抬頭一看,喬三臉上閃過一玩味兒的笑容,問傅慎時:“殷兄,陪我們說了這麼些話,也不喝口茶潤潤嗓子?”
登時明白過來,喬三今兒是來試探傅慎時份的。他還真是個有主意的人,蔫兒壞蔫兒壞的,兜著圈子說了這麼半天的話,就是想等傅慎時起如廁!
Advertisement
這就是這種人的手段,文縐縐地人出丑。
真齷齪。
傅慎時的確口干舌燥,他卻不顯毫狼狽,彎曲的手指頭過牛頭骨牌,淡聲道:“不。”
喬三挑挑眉,繼續有一搭沒一搭地跟傅慎時邊聊邊打牌。
這一打就是一個半時辰,喬三他們都出去了好幾趟,打到最后似乎沒了興致,連輸好幾把,人也煩躁了起來。
傅慎時手邊的銀票越來越厚,他也疲倦了,便稍稍放了點水,輸面比之前稍大了一些,喬三幾個漸漸回了本。
喬三臉好轉了一些,他輕哼一聲,又繼續耐著子玩了起來,他了一張牌,估著時間差不多了,便從戶部的事兒,忽然轉到了傅三采買木材的事上,他跟戴文軒說:“長興侯府的人還真是沾了傅六不的。”
他瞥了一眼傅慎時,但見對方神淡然地打出了一張牌。
這時候,汪先生敲門進來,他過來稟道:“殷爺,有兩位客人來了,說是要上二樓玩。”
二樓除了喬三他們,目前并無客人過來,指定了要來二樓,那必然是被人引薦來的。
傅慎時挑起眉,不知道在問誰:“什麼客人?”
喬三也不否認,打斷了傅慎時的問話,跟戴文軒打起眉眼司,問道:“你帶來的?”
戴文軒笑道:“我看殷兄這兒還不夠熱鬧,就跟幾個朋友打了招呼。”他又看向傅慎時道:“可能是我的朋友,不過來了就是生意,殷兄只管做你的生意便是。”
他們跟傅二并不認識,只能想法子引了傅二過來玩,暫時不好把人領到這邊來。
傅慎時饒有深意地吩咐汪先生道:“既然如此,您讓王先生和新來的人一起陪他們打牌。”他頓了頓,才道:“先生切莫輕慢了客人。”
前幾日,汪先生找了些會打牌的人過來陪打,用來控制牌桌上的輸贏,今兒正好就用上了。
汪先生會意,垂下眼皮拱手道:“是。”
屋子里放著銅腳盆,燒著碳,殷紅豆上有些燥熱,也不知道來的是什麼客人。
牌桌上,幾個人你來我往,輸輸贏贏沒個定數。
喬三正好打得累了,站起個懶腰,道:“我出去會兒。”
汪先生進來了,他瞧著傅慎時道:“殷爺,隔壁的客人輸了。”
喬三一愣,輸得這麼快?他笑道:“我去瞧瞧,要是認識的人,借幾個錢他們玩兒也無妨。”
汪先生又道:“隔壁的爺已經借過了,現在還想借,數額有些大。”
傅慎時問道:“借了多?”
“已經借五百兩了。”
喬三瞪大了眼,傅二手氣這麼差?
汪先生繼續說:“那位公子說,他是長興侯府的人二爺,不過我聽說傅二爺去保定府了。我剛說派人跟著他的小廝回侯府去取錢,他偏說只肯一塊玉佩,可那玉佩值不了五百兩。所以我才拿不定主意,過來問殷爺。”
傅慎時看向睜大眼的喬三問道:“喬公子認識?”
喬三僵住的笑容化開了,傅二這明顯是想賴賬,他訕笑道:“不認識。”
他可不想替傅二還賬。
傅慎時手里著一顆牌,輕輕地敲打在桌面上,同汪先生道:“他立字據。”他停頓了一陣,道:“若他不肯,便說明他是冒充的,就折斷他的五手指頭,打斷他的手臂。”
殷紅豆猛然想起來,傅二第一次欺負的那個夜晚,說——你再不放開我,你信不信六爺會打折你的手臂!一地掰斷你的手指頭!
的心口劇烈地跳著。
他把的話,記得那麼清楚。
喬三與戴文軒皆都睜圓了眼睛,皺眉看向傅慎時。
傅慎時沒在意,瞧著汪先生淡聲道:“先生去罷。”
汪先生點了點頭去了,傅慎時連傅二的下場都想好了,傅二便是想立,他也得想法子讓傅二立不字據。
喬三住了汪先生,他冷冷地看向傅慎時,已經確定殷櫨斗絕對不是長興侯府的人,因為沒有人會手足相殘。
但傅二這次是被他的人引來的,可不能在他手里出事。
喬三瞥了戴文軒一眼,故意了傅二的事,道:“傅二被家里人罰去保定府傅家祖祠了嗎?什麼時候的事兒?”
戴文軒默契地答道:“就前不久,不過聽說他的外室懷孩子了,誰知道是不是回來看他外室的。”
喬三深深地看了傅慎時一眼,這下子他該知道傅二的份了吧。
傅慎時面上一派鎮定。
殷紅豆卻是暗暗吃驚,實在沒想到,傅二竟然會跑回來。而且傅二那壞胚子,竟然養了外室,外室還有了孩子,這要是讓長興侯府的人知道了,那外室腹中的孩子肯定沒命,簡直是草菅人命。
殷紅豆還記得,剛來的時候還在潘氏院子里住著,也見過二太太,是個非常溫客人的人,跟丫鬟說話都輕聲細語的。
殷紅豆又想起傅二的猥瑣模樣,忍不住撇了撇角。
真是好姑娘都給賤男人糟蹋了。
喬三笑著同傅慎時出主意道:“萬一真是傅二,可要得罪了長興侯府,殷兄還是問清楚得好。”
“我不過他立個字據,他立了不就沒事兒了。”
喬三瞧著傅慎時,他這像是讓傅二立字據的樣子嗎?
傅二要真斷了一只手,長興侯府怪罪起來,不得連累喬三,他反問道:“倘或對方真是傅二公子呢?”
傅慎時回道:“喬公子剛才不是說,長興侯府的傅二公子,被家里人罰去保定府傅家祖祠了嗎?他又怎麼會在京城里?何況我讓他立字據在先,他若字據都不肯立,不是冒充的是什麼?”
喬三頭皮都在發麻,他冷眼掃過傅慎時,道:“我雖然跟他不,不過我與傅二打過照面,我去替你瞧瞧,若真是他,殷兄還是妥善理的好。”
“有勞。”
喬三跟戴文軒一道去了隔壁馬吊房,打開門裝模作樣地看了一眼,便折回來道:“是傅二,殷兄還是手下留。”
傅慎時同汪先生道:“他立字據,過幾日來還了,便了了。”
喬三松了口氣,領著戴文軒走了,下了發財坊,引傅二來的那個人也跟他們一道上了馬車。
戴文軒在馬車里拂袖道:“真是晦氣!”跟同行的人道:“以后離傅二遠點,他要再來,可跟咱們沒關系了。”
喬三也不悅地皺著眉頭,這殷櫨斗也不知道什麼來頭,連長興侯府也不怕得罪嗎?
發財坊,傅慎時等人已經回了雅間說話。
傅慎時拿著傅二立的字據,同汪先生道:“去打聽下,他的外室養在哪里,是不是真的懷孕了。”
“是。”
傅二這人心難滿,不僅好,也好賭,且容易沉迷,這次輸了,下次必然還要回來翻本。
殷紅豆有些不安,問道:“六爺,要不要跟侯府的人說,二爺回京了?”
若是跟長興侯府的人說了,傅二肯定要繼續罰,下次再回保定府,就沒那麼容易跑回來了。
殷紅豆覺得,這樣理也好,畢竟傅二和傅慎時是堂兄弟。
想起傅慎時方才說的話還有些后怕……賭坊的事萬一哪日泄出去了,傅慎時擔上手足相殘的名聲可糟了。
傅慎時閉著眼,沒有回答殷紅豆的話。
他說了要傅二的手指頭,就一定要。
猜你喜歡
-
完結3151 章

裝傻王爺俏醫妃
猝死在實驗室的柳拭眉,一朝穿越就失了身,被迫訂婚於傻二王爺。 未婚夫五歲智商,又乖又黏、又奶又兇。天天纏著她要親親、抱抱、舉高高,眼裡隻有她! 繼母繼妹暗害,他幫撕!父親不疼不愛,他幫懟!情敵上門挑釁,他幫盤! 可儘管她左手當世醫聖、右手一代毒師,唯獨,她家狗子這傻病,多少湯藥都不管用! 某日,她盯著二傻子剛剛倒進水溝裡的藥,這才醒悟:“原來你是裝的!” 靠著奧斯卡小金人的演技,這二狗子到底在她這裡占了多少便宜? 披得好好的小馬甲被撕了,他精緻絕倫的臉上笑容僵凝:“媳婦兒,你聽我解釋!”
386.5萬字7.72 1955359 -
連載1188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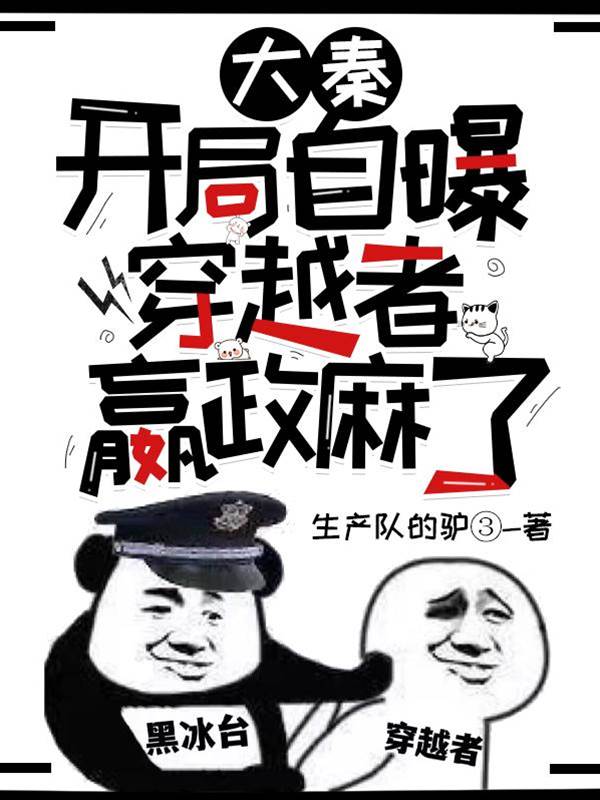
大秦:開局自曝穿越者,嬴政麻了
始皇帝三十二年。 千古一帝秦始皇第四次出巡,途经代郡左近。 闻听有豪强广聚钱粮,私铸刀兵,意图不轨,下令黑冰台派人彻查。 陈庆无奈之下,自曝穿越者身份,被刀剑架在脖子上押赴咸阳宫。 祖龙:寡人横扫六国,威加海内,尓安敢作乱犯上? 陈庆:陛下,我没想造反呀! 祖龙:那你积攒钱粮刀兵是为何? 陈庆:小民起码没想要造您的反。 祖龙:???你是说……不可能!就算没有寡人,还有扶苏! 陈庆:要是扶苏殿下没当皇帝呢? 祖龙:无论谁当这一国之君,大秦内有贤臣,外有良将,江山自然稳如泰山! 陈庆:要是您的贤臣和内侍勾结皇子造反呢? 祖龙:……谁干的?!我不管,只要是寡人的子孙在位,天下始终是大秦的! 陈庆:陛下,您的好大儿三年就把天下丢了。 祖龙:你你你……! 嬴政整个人都麻了!
247.2萬字8 9830 -
完結404 章
寒門科舉之路
簡介:獨自一人在末世里茍活三年,結果又被隊友陷害喪尸抓傷,不想變成喪尸被爆頭,楊涵自我了斷,沒想到穿越成農家小子,還是千里良田,一顆獨苗,地里拋食的工作干不了,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只能一路往科舉路上……
70.3萬字8 8104 -
完結617 章

替嫁福妃手握千億物資去逃荒
王者特戰隊教官虞棠一朝穿越,開局便淪為殘疾前戰神的世子妃,慘遭流放。夫君雙腿殘疾,身中奇毒,還是個潔癖升級版的大病嬌。婆母嬌弱貌美,卻老蚌生珠,懷揣一個四歲腹黑奶娃。戰神公公進能大殺四方,退可扛鋤種地,怎奈卻是一個妻管嚴大哭包。虞棠深吸一口氣,這個家,只有靠她來當家做主了!好在,她千億物資在手,格斗天下第一,更縱覽歷史,預知未來。世道不良,她便換個世道。等等!這個整天防著她爬墻,卻夜夜爬她床的男人,是不是也該換了?
112.6萬字8 115482 -
完結383 章

穿到荒年,我靠空間養軍隊造反啦
【種田+空間+萌寶+爽文】時魚一睜眼,成了桃花村人嫌狗憎扶弟魔。 戀愛都沒談過的她直接成了三個兒子一個女兒的媽。 哦,對了,還有個英俊無比夫君。 讓全家吃飽穿暖已經很累了,沒想到還有旱災,瘟疫,蟲災,安置無數流民…… 不過幸好,她有空間農場,能以物換物。 蘋果,西瓜,土豆,紅薯,還有西紅柿的種子通通種上,三天就能熟。 從全家吃飽到全村吃飽,再到讓流民們吃飽飯。 時魚成了大家的活菩薩。 于是當有人造反缺物資時便找到了時魚。 “夫君,你們本來就是被人冤枉造反被流放到此,何不坐實罪名?”
68萬字8 160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