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你入骨·隱婚總裁,請簽字!》 第一章:那你還勾引我?
小家伙又折了回來,背著大書包,趴在門口,對著郁紹庭用口型喊“爸爸”。睍莼璩郁紹庭雖然嫌兒子有點煩,但還是起走到門口“什麼事?”
郁景希覺得自己跟爸爸現在是統一戰線上的盟友,抓了抓書包帶,往病房里瞄了眼,笑得赧“爸爸你能先借我五十塊嗎?放學我想買束花給小白一個驚喜。”
郁紹庭蹙眉,冷的五讓他看上去極不易相。
“要是沒五十,一百塊也行。於”
郁景希看到郁紹庭抬手,以為他去套皮夾,不由笑得越加燦爛,“謝謝爸爸!”
結果房門“嘭”地在他面前甩上了。
…址…
老人家神不濟,在一番熱鬧的攀談過又沉沉地睡過去。
郁紹庭合上門回就看到靠在沙發上打瞌睡的白筱。
有過后的窗戶進來,將整個人都籠罩在金的線里。
閉著眼,眉頭鎖,睫地。
郁紹庭深沉的眼睛停在安詳的睡上,久久地,靜靜地,像是在看,卻又仿佛在過看向更遠的地方。
————————
白筱睡得昏昏沉沉,好像做了一個很長很長的夢。
夢到了一個年輕的子,秀致的五跟那張被夾在書里的黑白照中的人如出一轍,對著出溫婉的笑,媽媽……但下一瞬卻已經轉離越來越遠。
畫面忽然一轉,又看到了二十二歲的裴祁佑。
也許是因為時間隔得太久,已經看不清他的臉,唯獨不變的是掌心的溫暖。
他拉著跑過大街小巷的雪地,耳邊是自己急促的息聲,反握他的手,不問他去哪兒,只想地跟著他,希這條路永遠沒有盡頭。
Advertisement
那年裴家遭遇巨大變故,他一下子從天之驕子變落魄的乞丐王子,一夜之間從城高級別墅區搬進破舊的拆遷房,但那段日子對白筱來說卻是生命中最幸福的時。
他為了裴家四奔波,而就在家里照顧長輩,那時候裴家的積蓄已經用得差不多,為了省錢特意跑去農貿市場買棉線,又請隔壁的大嬸教怎麼打打圍巾手套。
冬天的手因為洗床單跟服生滿凍瘡,他會坐在床邊握住的手往掌心呵氣。
雪花紛飛的夜晚,他帶著翻越游樂園的鐵門,說服保安老大爺,緩緩轉的天在夜里閃爍著五六的彩,他忽然低頭親吻,能到自己紊激烈的心跳。
他說“關于天的傳說,你聽過嗎?”
一起坐天的人終究會以分手告終。但當天達到最高點時,如果與人親吻,那麼他們就會永遠一直走下去……
耳邊響起煙花升高空綻放的聲音,一簇又一簇。
白筱睜開眼,朦朧的視線里是白茫茫的墻壁,發現自己的頭正枕在一個肩膀上。
順著黑的西裝抬頭去,目的是一張棱角分明的俊臉,跟記憶里那張模糊的臉龐在的大腦里來回替,抬起的手無意識地輕輕上他的側臉。
那雙沉睡的深邃眼睛不知何時已經睜開。
在他低下頭來,白筱就像是著了魔一般,捧過他的臉主吻住了他的薄。
滾燙的溫度在齒間蔓延開來,白筱出舌尖描繪他的線,雙手十指過他的黑發間,從后把他的頭扣向自己,像是懲罰一般,用貝齒輕輕地咬著他閉的雙。
郁紹庭的黑眸幽深,深得似要擰出墨滴來,他任由親吻著自己,沒有去推開,就像在酒店的那晚,又又的氣息縈繞在他的周圍,沿著他的下顎弧線吻去。
在的上結時,他驀地攥過,頭一,低頭向嫣紅的,用力地,就像是野間的撕咬,他的虎口鉗住的下迫使仰起頭承他狂野的掠奪。
白筱的大腦一片空白,不知道自己是怎麼叉開坐在他的上,暈暈乎乎里,的羽絨服外套拉鏈被解開,寬松里的帶子松松垮垮地掛在肩上。
“唔……”一聲從微啟的間溢出。
微涼的手將他的襯衫從西里扯出來,從下擺進去,著他熾熱又結實的膛,側頭吻細地落在他微蹙的眉間,高的鼻梁上,最后嚴嚴實實地再次堵住他的。
的舌,在他的空腔肆意掃,就像一粒火種,瞬間點燃了熊熊烈火。
當寬厚的大手包裹住盈的錯時,白筱倏地揚高頭,白皙的脖頸在下閃爍著瑩白的澤,的羽絨服被褪下隨意丟棄在了旁邊。
被摘去發圈的長發凌地披在后,在半空漾出一道妖嬈的弧度。
在整個人往后傾斜下去之前,一條遒勁的手臂圈過,將往前一扣,白筱整個人都進了郁紹庭的懷里,伏在他的肩頭,呼吸急,低垂的視線黏在下那只突起的大手上,他帶著薄繭的手指劃過的峰頂,抑制不住地發出甜膩人的哦。
“啊……嗯……呼……”咬著紅腫的,的發黏在了紅遍布的臉上。
白筱的額頭抵著他的肩,手指上他線條分明的膛,長長的指甲掃過他前的茱萸,郁紹庭頭一,一雙凌厲而幽深的眼睛死死地盯著懷里胡作非為的人。
“認真的?”他按住的手,子前傾,近紅紅的耳。
白筱半閉的雙眼,又長又的睫不停地抖,的另一只手沿著他結實平坦的小腹往下,當解不開皮帶扣子時,有些惱怒地直接去扯他的西拉鏈。
郁紹庭看了眼床上的老人,驀地將整個人抱起,大步邁向洗手間。
狹隘的空間,被反鎖上的門,白筱的后背猛地抵上冰涼的瓷磚,一個哆嗦,的雙本能地夾住置其中的男人,上早已不著,的因為寒冷激起一層小顆粒。
不等回神,欺而上的是一陣邦邦的涼意。男人的襯衫著的口,兩朵艷的紅梅在空氣里慢慢立綻放,微微褪下的牛仔敞開著,出小巧的肚臍眼跟圓翹又致的,黑底蕾在牛仔邊若若現。
“啊……”白筱失聲驚呼,閉上眼,從未有過的恥從前直襲向大腦。
他修長的手重新上的渾圓,大間夾著的瘦腰讓的瘋狂地抖,原本就渙散迷離的意識仿若一葉扁舟在大海中激起伏。
翕合的雙細微地低喃著幾個字,讓前的男人驟然停頓了所有的作。
祈佑……祈佑……
繾綣在舌尖的名字讓郁紹庭的眼底瞬間仿若颶風掃境后的森冷。
白筱坐在盥洗臺邊,仰著頭,呼吸越來越重,合的眸里是迷醉的沉淪,的小手進他的西里,尋著那后開始笨拙地一下又一下地撥……
頭劇烈地上下翕,郁紹庭盯著的眼神鷙卻又熾熱,一熱流迅速地在下腹匯聚,最脆弱地方傳來的戰栗讓他的神經繃,隨時隨地都要炸一般。
忽然眼前一陣天旋地轉,白筱整個人從臺子上被扯下來,一個翻轉,的雙手撐住盥洗臺,的后背覆上男人沉重的時,飄渺的漸漸被回籠的理智沖散。
潛意識地想要推開后的男人,卻反被鉗住下頜抬起,強迫看向鏡子。
線暗的廁所,水汽朦朧的鏡子上,映照出的是兩道模糊不清的相疊影。
像是意識到了什麼,突然而來的不安讓白筱拼命地掙扎起來,腰際卻被一雙大手住,他毫不憐香惜玉地將在盥洗臺上,的肚臍被擱疼得有些不過氣來。
“……放開我……”烏黑的長發跟雪白的背形強烈的視覺沖突。
后的男人一言不發,面冷峻,就像是被激怒的雄獅,散發著冷的氣場,他一手扣著的腰,一手扯住的牛仔就大力往下。
“不要這樣……”白筱扭轉過頭,清醒后的因為恐懼而不停地栗。
像郁紹庭這種居于高位的男人,都有他人不可挑戰的底線,怎麼可能忍人在跟自己做時喊著其他男人的名字?
而白筱的一而再簡直讓他變了一只窩囊的綠,總覺得不做些什麼無法平息心頭的怒火,尤其是回過頭來哀求的眼神,非但沒讓他消氣,反而徹底被激怒了!
“不要哪樣?”郁紹庭著,眼底是深深的寒意,“剛才不是很嗎?”
看著男人那冷漠到近乎鷙的俊臉,白筱的小手著他的手,不讓他把自己的最后的遮布扯下去,這樣的郁紹庭,讓找不到早晨他把皮夾遞給自己時的那份溫和。
下一秒后傳來窸窸窣窣的聲音,白筱掉轉過頭,就看見郁紹庭解開了皮帶的金屬扣子,正在拉西的拉鏈,暗的四角短沒有掩飾里面鼓起的廓,約著巨大的發力。
白筱看得目驚心,想要掙,卻反而被制得更加厲害。
“郁……”白筱不知道該怎麼稱呼他,忽然想起那個可懂事的孩子,就像抓住了救命稻草一般“景希爸爸……”
想借孩子來喚醒他的理,卻聽到他諷刺的話“原來你還知道我是景希的爸爸。”
他的薄從后若有似無地挲的耳垂,聲音暗啞而“那還勾引我?”
“我沒有!”白筱急得解釋,耳垂卻被狠狠地一口咬住,“啊!”
發出一聲吃疼的,接著上一涼。
牛仔連著底被他蠻力拽下,白筱沒想到他居然這麼不管不顧,覺到有一碩長滾燙的抵上的,臉煞白,開始口不擇言“放開我……你放開我……禽!”
“禽?”郁紹庭的聲音冷漠得像是沒生命的機械,他一手抓住的雙手在盥洗臺上,帶著怒氣般把的雙分開“我要是禽,上回在酒店就干你了。”
他齒間咬著的魯字眼讓既覺得辱又到一陣惶恐,以致于忽略了后半句話。
牛仔被褪到大,白筱近乎全,而他卻始終穿著筆的西裝,當他上來時,的上他的西布料,而他間的火熱卻像是要燃燒芳草萋萋的幽谷。
這種未曾驗過的刺激從的表皮過直達靈魂深!
“嗯……啊……唔唔!”當他在的間來回試探時,白筱控制不住地細碎嚶嚀。
想要躲開這個晴不定的可怕男人,可是又能躲到哪里去呢?
前是冷的大理石臺板,后被他死死地著,的一個勁地哆嗦。
郁紹庭站在后,原本只是想小懲大誡一下,可是真把了在下,才發現形勢有些控制不住,三十四年來從未有過的因子在里沸騰囂。
他本就是個冷的男人,郁老太太給他算過命,算命的說他天生涼薄,命雖富貴卻太,日后難免克妻克子,落個不得好死的下場,當時老太太就把那算命的給轟了出去。
結果還真讓那個神說中了。
他結婚那天新娘子在前往婚禮現場的路上,所坐的婚車跟一輛大卡發生撞。
本來那是他坐的車子,公司臨時有事需要他去理,車子被開去了加油站,徐淑媛就把自己的車給了他,等他理完事到現場,等來的是新娘子車禍被送往醫院搶救的噩耗。
徐淑媛保住了命,痊愈后他們去登記結了婚,婚后的徐淑媛依舊會用那慕的眼神凝著他,每當夜卻變得惶恐不安,后來他才得知因為那次事故讓徐淑媛失去了子宮。
猜你喜歡
-
完結241 章
鬼王老公
迷之自信的菜鳥捉鬼師蕭安靈瞞著家族自學捉鬼,一不小心遇上一只鬼王,一不小心生死相連,為解開咒語,蕭安靈帶著鬼王踏上了捉小鬼練法術的悲催道路。 在爆笑心酸的調教史中,菜鳥捉鬼師蕭安靈漸漸成長,延續千年的孽緣也逐漸浮現水面,當真相一個個揭開,是傲嬌別扭的忠犬鬼王還是默默守護千年的暖男大鬼,菜鳥捉鬼師蕭安靈只得大呼:人鬼殊途!人鬼殊途!
44.1萬字8 16416 -
完結748 章

總裁前妻哪里逃
穆青寒,從今以后,你是你,我是我,我們橋歸橋,路歸路,再無瓜葛!兩年前,簽完離婚協議書的夏星星離開了。如今再次回來,卻被前夫窮追猛打。…
100萬字8 243658 -
連載114 章

頂級蓄謀,瘋批前任他又撩又黏人
【破鏡重圓 頂級曖昧拉扯 先婚後愛 HE】【持靚行兇大美女vs綠茶瘋批純愛惡犬】風光霽月的沈家大小姐沈清黎,隻做過一件離經叛道的事:在年少時和自家保姆的兒子談了一段持續兩年的地下情。後來沈家落魄,她淪落到去跟人相親。20歲那年被她甩了的男人卻出現在現場,西裝革履,禁欲驕矜,再也不複當年清貧少年的模樣。沈清黎想起當年甩他的場景,恨不得拔腿就跑。“不好意思,我離婚帶倆娃。”“那正好,我不孕不育。”-沈清黎的垂愛是樓璟黯淡的人生裏,唯一的一束光,被斷崖式分手,差點要了他半條命。他拚盡全力往上爬,終於夠格再出現在她麵前。按理說他該狠狠報複回來,可他卻沒有。-兩人領證那天,樓璟拿著結婚證的手顫抖不已,強裝鎮定。“樓太太,多多指教。”可某天她還是背著他,準備奔赴機場與情敵會麵,他終於破防。暴雨傾盆,他把她壓在車裏,聲音低啞透著狠勁兒。“我不是都說我原諒你了嗎?為什麼還要離開我?!”最後他又紅了眼眶,把臉埋在她頸窩,像被雨淋濕的小狗般嗚咽出聲。“姐姐,別再丟下我,求你。”
20.8萬字8 715 -
完結199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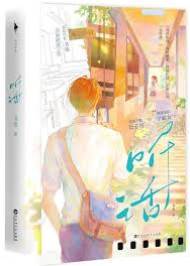
聽話
那不是程歲寧第一次見周溫宴。 她見過他意氣風發,見過他浪蕩不羈,見過他懷裏女孩換了一個又一個。 只是那次,她心動最難捱。 那天室友生日她走錯包間,偶然窺見他懶懶陷在沙發裏,百無聊賴撥弄打火機。 火苗忽明忽暗身旁女生和他說話,他勾着笑半天敷衍回個一字半句。 她回到包廂裏第一次鬼迷心竅主動給他發了信息,【今天聚會好玩嗎?】 下一秒,他回:【你不在沒意思。】 後來他們分手,多年後在風雨裏重逢,她被男友差遣輕視狼狽不堪。 他跨過一衆圍着他殷勤討好的人羣,不顧目光,拉住她的手,塞進一把傘。 冬夜昏天暗地光線裏,他垂眼看她,聲音淡淡:“撐傘,別淋雨。” 那一刻她這才知道,除了他以外都是將就。 朋友問那再後來呢?她淺笑着沒說話。 只是每年西園寺,雲蒸霞蔚煙火繚繞的銀杏樹下多了個虔誠的少女。 那天年初一,青衣僧人說有緣人贈了她一張紙條。 展開一看,字體熟悉,上面寫着‘一歲一禮,得償所願。’ 她下意識回頭,人海茫茫裏,一眼只看見他溫柔背影。
34.2萬字8.18 6027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