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慕川向晚》 第087章,逼婚
技隊就在刑偵大隊,是一個單獨的科室,獨自占了一層樓,但環境與向晚的理解還是不一樣。
不是恐怖片,沒有在顯目位置擺放的尸塊與儀,沒有存放著各種的冰柜,這里的一切人與事都顯得非常接地氣。
向晚松一口氣,“嚇死我了。我還以為這里會上演恐怖片呢。”
“差不多!”白慕川努了努,穿著白大褂的程正剛好從他的辦公室出來,“看他那張臉,你不覺得比恐怖片還恐怖?”
呃!
向晚輕咳一聲。
幸好,這個距離,程正是一定聽不到的。
瞄白慕川一眼,“你為什麼跟他這麼不對付?”
“有嗎?”白慕川瞇起眼,視線涼涼的,“也許是……天生的吧。”
天生的?不對付也有天生的?
向晚從他臉上看不出什麼涵,這時程正已經發現了他們。
他怔一下,慢慢走過來,“白隊,找我有事?”
白慕川單手在兜里,眼角噙著笑,看上去很隨意,“來看看你們的工作進展。”
程正抿,不聲地指了指,“那邊坐吧。”
順著他的手指,向晚發現那個掛著“法醫室”牌子的房間。
而程正帶著跟白慕川,正是往那里去……
門開了。
一涼氣撲面而來。
向晚往里了一眼,心臟沉了沉,突然了悟。
技科沒有電影大片那些可怕的東西,法醫室卻有。
梅心坐在冰冷的工作臺前,正對著一個顯微鏡似的東西在觀察什麼,一雪白的白大褂,蒼白得沒有的面孔,回頭瞥來時,不帶半點的目,以及背后那一人骨架,給向晚帶來一種難以言狀的驚悚。
“白隊,程隊!”
程正點點頭,面無表地說:“白隊過來視察工作,你給介紹介紹。”
Advertisement
一口大鍋就這麼迎頭砸了下來。
白慕川看他一眼,角抿了抿,沒說話。
梅心看看這個,又看看那個,慢慢站了起來。
講真,夾在兩個帶著火藥味的男人中間,向晚都替梅心覺得難做,可梅心自己卻毫無異常。
臉比程正還要平淡,拿出遙控,慢吞吞把窗簾拉上,房間頓時陷黑暗。
向晚驚一下,不知道他們要干什麼。
昏暗的線中,白慕川的一只手就了過來。
在肩膀上,輕輕攬了攬,像是緩解的張,又像帶著某種呵護的意味兒……
向晚心臟怦地一跳。
這時,房里亮起一盞微弱的燈,那是梅心控著3D顯示屏的。
“白隊請看……”
梅心用電腦演示著,指向顯示屏上的畫面。
“這是孫尚麗自殺案與帝宮碎尸案的相關證鑒定,這是孫尚麗的尸檢報告。由我、王東、劉小媛共同出的鑒定。這一張是無名尸塊做出的DNA圖譜……”
梅心緩緩道來,“這些報告,都已經給白隊過目了。”
也就是說,技隊能做的工作,他們都已經做完,進度是100%。
“目前,無名人組織的份已經確定,不知白隊接下來,還有什麼安排?”
很厲害!
向晚看著面無表地代況,順便將白慕川一軍,突然發現這個看著清冷的人不得了。
而且,發現梅心潛意識里,是向著程正的。
把技隊所有的工作責任都攬到了自己的上,順便再幫程正踹了白慕川一腳,意指他們的偵查工作跟不上,沒有更多的證出來,沒有破案完全不關技隊不關程正的事。
當然,這只是向晚自己的覺。
就像對白慕川所說,是敏銳的第六或者說第七給的覺。
這個看上去沒有什麼人味兒的冷漠法醫,或者心是為程正抱不平,或者帶了那麼幾分天長日久在一起工作產生的,釋放出了強大的氣場……
不過,向晚發現,除了自己,并沒有任何人發現這一點。
“很好。”白慕川輕拍一下手,坐到辦公椅上,對著那份完整清晰的技鑒定檔案點了點,突然轉頭看著程正,“程隊對這個案子,似乎沒有興趣?”
程正:“不明白白隊的意思。”
白慕川說:“從孫尚麗死亡開始,你除了在他們的鑒定上簽字,好像什麼也沒有做,實在有點對不起你那漂亮的履歷……”
“我相信他們。”程正不冷不熱地說:“為警隊培養更多的人才,比我一個人把所有活都干完更重要。這一點,我相信白隊懂的,難道你能把所有一線的偵查工作都做完嗎?不能吧?”
“不能。”白慕川目涼了涼,冷笑,“但我不會對涉及同事前途命運的案子視若無睹。”
“每個人不一樣。”程正沒有表,“我對與我無關的人,從來沒有多余的同心奉送。”
“呵。”白慕川慢慢站起來,“與你有關的人,你就有多余的同心了嗎?”
程正看著他略帶嘲諷的笑,抿,不說話。
法醫室,突然冷得仿若凝冰。
向晚鼻腔有點,很想打個噴嚏……
這時,梅心突然淡淡開口,“聽說向老師會側寫?我對這個也很有興趣,想請教一下,依你分析,這個碎尸案的兇手是個什麼樣的人,剩余的部分組織,又會被對方藏在哪里?”
“……”
向晚沉默一下。
“能準確回答你的人,是神仙,不是側寫。”
“不需要準確。”梅心似乎有意緩和法醫室里的怪異氣氛,接著又道:“就隨便聊聊,我想聽聽你的覺。”
冰冷的眼里,有好奇的芒。不多,很淡,但向晚覺到了,不是在有意為難。
梅心其實是一個極其簡單的人。向晚想。
簡單的工作,簡單的說話,不與太多人有復雜流,沒有復雜的社會關系……這種人,肚子里沒有什麼彎彎繞繞,也不會太在意的話會對別人造什麼困擾。
“好吧,那我就隨便說說。不用當回事,就圖一樂。”
向晚笑了笑,很快收斂表,一臉嚴肅地道:“兇手思維縝,行事果斷冷靜。他與死者應該有仇,分離了他的尸,并分別藏尸理,這麼多年沒有讓人發現破綻,可以說相當厲害了。當然,要把人組織封墻,必須有這個便利。因此,兇手與當初帝宮的承建者有關,這個毋庸置疑,只要找到當初做混凝土砌的人,肯定會有重大突破。”
淡淡地說著,不帶。
梅心聽完,看的目有的變化。
“這就是側寫?”
“不。這是推理。”向晚看了白慕川一眼,“完全是基于已知條件得來的結論,不一定正確,但八九不離十。”
說到八九不離十,那已經是相當自信了。
“其實就這個問題來說,我最覺得不可思議的是霍山居然代不出來這個人。盡管他說得好像真像那麼回事,但霍山肯定還有瞞,即便他不是兇手,也一定與兇手有某種不可說的關系。”
這句話與白慕川的分析不謀而合。
梅心回頭向白慕川,“白隊,你覺得向老師說得對嗎?”
“我只信證據。”白慕川依舊是那句不冷不熱的話,閑閑地靠在椅背上,側臉的棱角有一種堅的弧度,雙眼深邃而淡漠,帶一點若有似無的笑,態度自負而倨傲,“但側寫,可以用來參考。”
向晚瞥他一眼,噴嚏終于打出來了。
“不好意思。”抱歉地沖那二位一笑,“我想先走了,這里太冷。”
法醫室里莫名傳來的那種消毒水味道,讓總想起類似去太平間或者殯儀館那種地方,呆不下去了。
“冒了?”白慕川擔心地看一眼,“走吧!”
嗯一聲,向晚朝梅心跟程正微微一笑。
“打擾了。我先走了!”
“向老師!”不等轉,程正突然喊了一聲。
向晚回頭,看著程正清冷無的臉,莫名覺得他的面部表有一異樣,就像噙了一嘲笑,或者諷刺,但更多的,是一種不帶的冰冷。
“那天在你小姨家看到你母親了。”
“?”向晚偏頭審視他,不知道他到底想說什麼。
“似乎不太好,一直在咳。最近快換季了,流肆,你要有時間,多關心一下家人。”程正說到這里,角微微一抿,“這世界上的事太多了,我們的力卻很有限。我們能做的,就是盡可能關心好自己應該關心的人。對無關的人和事,不需要投太多的力!”
“!”
向晚沒想到程正會突然這樣說。
不是說教的說教,竟讓無法反駁。
因為他說的是的母親,不管用什麼形式反駁,都會顯得很不孝。
實際上,這些日子,沒有去過小姨家,一是為了避免那種莫名其妙的尷尬,二是自己緒太糟糕,渾都是煩躁,怕把這分沉重帶給母親。
每次電話里,母親都說很好……
還真的沒有發現,原來母親生病了。
向晚看著程正的眼睛,嚨一鯁,有一種特別難咽的酸。
“謝謝程隊。我會的。”
默默低頭,準備離開,程正卻慢慢解下手套,看著慢吞吞說:“我上次的建議,還有效。你考慮一下。”
嗯?
都這個時候了,他還記得那件事?
向晚不知該有哭,還是該笑了。
他就這麼自信地認為應該把握機會,不要錯過他這樣優秀的男人麼?
“不好意思。”向晚莞爾,“我能說的,上次就給程隊說過了。我需要的東西跟程隊你不同。你也不是那種可以讓我放棄自己的人。抱歉了!”
本來拒絕這種話,不應該當著別人的面說的。
可程正并沒有顧及被問及母親病時的尷尬,也就沒有必須顧及他會怎麼想了。
這個男人太自負!
也許他不是壞人,但向晚知道,以自己這個格,跟他是不可能有結果的。他所謂的提議,那個“不需要的”更不是能接的。所以,及時止損,一次說個明白,也免得程正惦著,彼此尷尬。
“程隊!”白慕川突然開口,角揚起,帶一點涼壞的笑,“我的建議跟你也是一樣,做好分的事。我等你更詳細的報告!相信以你的專業,會為破案提供更多的線索。”
程正站在那里,站著兩只純白的手套,目瞇起,僅僅未。
白慕川調頭,拉著向晚的手腕,大步出去。
這就很尷尬了!
向晚覺得后背上像有火在燒——那是程正的目,也是梅心的目。
他們在審視與白慕川的關系,有點囧,白慕川卻不以為意,步子邁得堅定而快速……
外面正盛。
向晚心怦怦跳著,不經意掃過他抓住的手,又不控制地抬頭看他的臉。金輝般的線從他的側臉落下,讓他五較平常更為深邃分明,漆黑的眸,冷高的鼻梁,抿住的,不羈于世的飛揚,以及一種韁野馬般恣意揮灑的……
白慕川突然低頭,“所以,你是在看什麼呢?”
他心似乎很好?向晚看著他,突然有點想笑,“所以,你是在笑什麼?”
白慕川認真凝視的臉,“你說呢?”
四目相對,視線在不可的空間里流轉,默契十足,心知肚知,那是一種并肩攜手打了個小怪的覺。
向晚噗嗤一聲,堵在心里的霾散去不,嘆息一聲,又客觀地說:“程正這個人,就是自我了一些。但工作能力很強,你還是把心放寬一些,與他合作比跟他打對臺更好。”
“哼!”白慕川不表態,“你是在為我說話,還是為他說話?”
猜你喜歡
-
連載601 章

這主播真狗,掙夠200就下播
189.5萬字8.18 8119 -
完結866 章
晝夜關系
追妻火葬場失敗+男主后來者居上+先婚后愛+隱婚+暗戀甜寵+1v1雙潔季璟淮覺得,司意眠是最適合娶回家的女人,他手機里有故事,有秘密,兩個他都不想錯過。可等司意眠真的嫁給了顧時宴,季璟淮才知道,自己到底錯過了什麼,他終究丟了他年少時最期盼的渴望。再次狹路相逢,她如遙不可及的那抹月光,滿心滿眼里都是另一個男人。他的未婚妻,最終成了別人捧在心尖上的月亮。宴會散場,季璟淮拉著她,語氣哽咽,姿態里帶著哀求,紅著眼質問道“你是真的,不要我了。”司意眠只是那樣冷冷看著他,被身邊矜貴冷傲的男人擁入懷中,男人微微抬眼,語氣淡然,“季總,我和太太還趕著回家,請自重。”她曾以為自己是全城的笑話,在最落魄時,被僅僅見過數面的男人撿回了家。后來她才知道,有人愛你如珍寶,你的每一滴淚,都是他心尖肉,掌中嬌。他不舍讓你受一絲委屈。(白日疏離,夜里偷歡,折我枝頭香,藏于心中眠。)豪門世家溫柔專一貴公子x云端跌落小公主一句話簡介京圈太子爺為愛做三
80.9萬字8 80675 -
完結199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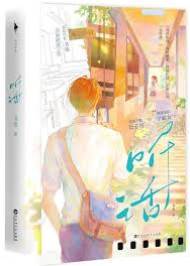
聽話
那不是程歲寧第一次見周溫宴。 她見過他意氣風發,見過他浪蕩不羈,見過他懷裏女孩換了一個又一個。 只是那次,她心動最難捱。 那天室友生日她走錯包間,偶然窺見他懶懶陷在沙發裏,百無聊賴撥弄打火機。 火苗忽明忽暗身旁女生和他說話,他勾着笑半天敷衍回個一字半句。 她回到包廂裏第一次鬼迷心竅主動給他發了信息,【今天聚會好玩嗎?】 下一秒,他回:【你不在沒意思。】 後來他們分手,多年後在風雨裏重逢,她被男友差遣輕視狼狽不堪。 他跨過一衆圍着他殷勤討好的人羣,不顧目光,拉住她的手,塞進一把傘。 冬夜昏天暗地光線裏,他垂眼看她,聲音淡淡:“撐傘,別淋雨。” 那一刻她這才知道,除了他以外都是將就。 朋友問那再後來呢?她淺笑着沒說話。 只是每年西園寺,雲蒸霞蔚煙火繚繞的銀杏樹下多了個虔誠的少女。 那天年初一,青衣僧人說有緣人贈了她一張紙條。 展開一看,字體熟悉,上面寫着‘一歲一禮,得償所願。’ 她下意識回頭,人海茫茫裏,一眼只看見他溫柔背影。
34.2萬字8.18 6032 -
完結192 章

和塑料竹馬閃婚了
樑思憫閒極無聊決定跟季暘結個婚。 儘管兩個人從小不對付,見面就掐架,但沒關係,婚姻又不一定是爲了幸福,解解悶也挺好。 果然,從新婚夜倆人就雞飛狗跳不消停。 一次宴會,兩人不期而遇,中間隔着八丈遠,互相別開臉。 周圍人小聲說:“季總跟他太太關係不好。” “樑小姐結婚後就沒給過季總好臉色。” 邊兒上一男生聽了,心思浮動,酒過三巡,挪去樑大小姐身邊,小聲安慰,低聲寒暄,委婉表達:“男人都不是好東西,但要是我,肯定比季總聽話,不惹您生氣。” 季暘被人遞煙,散漫叼進嘴裏,眼神挪到那邊,忽然起了身,踢開椅子往那邊去,往樑思憫身邊一坐,“我還沒死呢!” 樑思憫嫌棄地把他煙抽出來扔掉:“抽菸死的早,你再抽晚上別回家了,死外面吧。” 季暘回去,身邊人給他點菸的手還懸在那裏,他擺了下手:“戒了,我老婆怕我死得早沒人陪她逗悶子。” 看身邊人不解,他體貼解釋:“她愛我。” 周圍人:“……”無語。
29.4萬字8.18 3541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