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頑烈》 第26章 [VIP]
--
翌日下午, 接到傅言真的電話。
在電話里,他報了個地點,是個箭俱樂部的地址, 讓過來。
還威脅一個小時必須到。
其實離家不遠。
坐車二十多分鐘就到了。
接完電話后, 便去跟沈鄰溪說今天要去找同學。
沈鄰溪當時在花, 雖然常在曾如初房間里放一些西洋花束,但本人更偏東方花藝。
東方花藝比較喜歡留白和構型, 一般不追求那種滿滿當當的視覺效果。
也像說話,不要把話說的太滿, 要留一點余地給別人息和遐想。
不過,沈鄰溪當時說話其實是無心的。
說了句:“又出去啊。”
曾如初之前在實驗的時候, 其實沒怎麼見過周末和同學出去玩。
不是去補課就是悶在家,讓出去找同學都不去。
到了雅集好像格還變活潑了。
沈鄰溪真覺得這種變化是好事。
但做賊的人總是心虛的。
這一個“又”字讓曾如初有些惶惶。
忙解釋:“那、那我不出去了。”
聽到話,沈鄰溪放下手里的東西,抬眼看了過去。
沈鄰溪看的眼神總是很溫和。
曾如初覺得,即使媽媽還在世,對也不可能這麼溫。
但此時卻很心慌。
沈鄰溪有些奇怪, 問了句:“為什麼不去?”
曾如初:“……”
“同學愿意找你玩是好事啊, ”沈鄰溪又笑了笑,“路上注意安全。”
曾如初訥訥點頭。
但心里一時為欺騙到愧疚, 不過,很快又自欺欺人地為自己辯解。
傅言真也是同學啊。
回房,在櫥里看了許久。
最后換上一件子出門。
--
俱樂部管理嚴謹規范。
Advertisement
到了門口時,保安不讓進來。
因為沒有這里的會員卡。
直到聯系了傅言真, 他后面又打了個電話給保安。
這才被放行。
傅言真在三樓最里側的房間, 位置僻靜。
過去時, 門未合嚴, 但屋里還開著冷氣。
像是特意給留的門一樣。
煙草味從門里溢出,味道重。
曾如初對氣味敏,微蹙了下眉。
還聽到屋里有說話聲,聽著聲好像都是男的。
抿抿,手搭在門沿上,輕輕推了一下。
只見里面好幾個男生,湊在一起在說說笑笑。
看到傅言真靠墻站著。
他兩手在兜里,長疊放著,神懶漫的很。
曾如初站在門邊,有些躊躇,一時不知道要不要過去。
沒一會兒,韓紳覺察到靜,側過頭看到,角一扯,笑了聲,“呦,這是誰家小姑娘啊?”
他之前聽到傅言真打電話,當然知道這小姑娘來找誰的。
但他們這些人,不正經慣了,看到來了個文文靜靜的小姑娘,就忍不住的欠。
曾如初臉唰的一紅,不順著韓紳的話說,只小聲道了句:“來找傅言真。”
其余幾個男生都循著聲來看,還有人起哄吹了聲口哨。
傅言真視線撇過,上下打量了一眼。
今天穿了件子。
好看的。
但轉瞬之間,臉上那點異就了個干凈。
他也不做人的順著韓紳的話茬,輕描淡寫地問了句,“你誰家的,來找我?”
曾如初這回倒是抿出他話里的深意,這個“誰家的”可不是像叔叔阿姨問的“誰家孩子”這般簡單。
瞪了他一眼。
才不會說是誰家的。
傅言真看,角噙著抹淺笑,愈發顯得人蔫壞蔫壞的。
定定地站門邊,見他輕佻的沒個正經樣子,說了句狠話,“我走了。”
還不是裝裝樣子,真就抬腳往外走。
周圍幾個男的笑著起哄。
年紀大一點見過點世面的韓紳也倍意外,一般的小姑娘見到傅言真不是害的說不出話,就是想法設法的討好,頭一遭見到有人給他臉看。
他笑出聲,手肘搗了下傅言真,“欸,不給你面子啊。”
傅言真臉上沒有不被給面子的惱,他看了眼韓紳,淡淡說了句:“煙別了。”
然后就起去捉人。
他高長,沒費什麼功夫就攆上了曾如初。
在樓道口將人截下。
要走的慢了,這蘑菇怕還真就跑了。
“跑什麼?”傅言真手勾了下書包帶。
曾如初不說話。
“行了,不說了。”傅言真笑了聲,手上卻沒放松,還用了點力,將人往跟前拽了些距離。
曾如初瞪他一眼,讓他把手松開。
他挑了下眉,倒也把手松開了。
帶著人進屋。
他眼神掃了一下,讓屋里的閑人都滾到自己的地方去。
這屋子是他練習用的,平日不讓人隨便進來。
幾個人嘿嘿笑著,最后只剩下韓紳。
他早已將里的煙摘下來。
看出點門道,仗著平日里和傅言真關系好點,多問了句:“朋友?”
曾如初聽到這三個字,子猛的繃。
但沒等把“不是”說出來,傅言真先開了口。
“同學。”他聲音懶懶地解釋了句。
“普通同學。”沒多久,又說了聲。不咸不淡的語氣。
韓紳視線在他倆之間逡巡,意味不明的笑了笑。
曾如初站一邊,離他們不遠不近。
傅言真低著眸,手上在忙自己的,看上去也沒有招待的意思。
就這麼把晾在一邊,也不知道喊來到底要干什麼。
倒是那個韓紳的問要不要來試一試。
搖了搖頭。
傅言真側過眸看一眼,朝后的門抬了抬下,“東西可以放里面。”
曾如初“哦”了聲,跑過去放自己的包。
人走后,韓紳嘖了聲。
傅言真剛剛那話鬼都不信。
他這個人憎分明的很,平日本不去想掩飾什麼。
也從沒見他帶什麼人來過這里。
曾如初去了旁邊的休息室放東西,韓紳見人不在,又笑著問了聲:“普通同學啊?”
傅言真知道這人是個人,瞞不過的,只有曾如初那小傻子才以為這事能騙的了人。
他哂了聲,“不讓說。”
韓紳明顯沒想到是這麼回事,意外之余,又忍俊不。
“為什麼不讓說?”他又問。
能做傅言真這種長的帥家里又有錢的公子哥的朋友,應該恨不能在上印個LOGO才對。
就俱樂部里的幾個小姑娘,哪個看到他不是眼里冒,多說一句話回頭都要跟小姐妹叨叨半天。
沒想到還有藏著掖著的。
傅言真沒吭聲,但臉上表沒什麼不悅。
韓紳見他今天心好,又拿他打趣:“不會是嫌你帶出去丟份吧?”
傅言真不想理會他這些屁話。
看人一眼,撂下一句:“你心里知道就行了,別叨叨個沒完把人給我嚇跑了。”
韓紳笑了笑,做了個打住的作。
--
曾如初放好東西后就出來了,以為傅言真有事在忙,所以沒過去打擾。
自己又走到外面看了看。
這里不是訓練基地,屬于正常營業場所。
正逢周末,里面人還多。
傅言真那伙人里,有好幾個都帶了朋友過來玩。
聽著路上的人閑聊才知道,這俱樂部就是傅言真他們家的,幾年前被他爺爺買下,送給他孫子玩。
見太久沒回來,傅言真便出去看了眼,見呆愣愣地東張西,不知道看什麼。
他靠墻看了會。
不一會兒,跟前走過一個染著一頭熒綠的生,穿著也比較大膽,臍裝和熱。
材也確實辣。
生看到他時,眼睛忽地一亮。
在開口說話之前,他一個眼風掃了過來。
一個無聲的“滾”字。
生忙不迭的走了。
“過來。”傅言真忽地開了嗓。
那生沒走遠,聽著話跟著回頭。
傅言真加了個后綴,“蘑菇。”
曾如初:“……”
他要不喊這一聲,真以為是喊那綠頭發的姑娘。
小跑到傅言真邊,一時了最顯眼的那個。
來往的人都好奇打量。
路上幾乎每個人都認識傅言真,也都問跟在他后的人是誰。
傅言真今天出奇耐心,逢問必答,像是故意說給人聽的。
他一一回應“普通同學”。
并在“普通”二字上做重讀。
他的那些狐朋狗友,一個個又嬉皮笑臉地將這幾個字重復一遍。
“普通同學啊?”
“普通同學,普通同學。”
“普通同學哈哈哈哈……”
……
曾如初到后面才知道,他邊的人幾乎都知道是他朋友。
只有傻傻地在掩耳盜鈴。
又回到剛才的那間房。
傅言真從一旁的架子上撿了張弓給,他剛剛就是在調試這東西。
“試試。”他又拿了一筒箭過來。
然后便退到一旁。
他靠墻站著,兩手抱著胳膊,后面一句話都不說,也不指導,就這麼看著折騰。
曾如初不懂什麼技巧,手就去拉弓,作也簡單暴,就想把系著的那弦給它弄開。
試了一下。
兩下。
三下。
……
竟然就是拉不開。
傅言真在一旁看洋相,笑的都出聲。
曾如初這才知道又在捉弄,將東西往他手邊遞,一臉憤懣:“你拿個壞的給我干什麼啊?”
傅言真揚了下眉,慢慢悠悠地站直子,抬手接過弓,又了箭。
沒費什麼力的一拉,箭飛了出去。
唰的一聲。
輕輕松松了個九環。
曾如初:“……”
傅言真看一臉窘迫笑了聲,嗓音的很低,“哪里壞了?”
曾如初:“……”
傅言真才不輕易饒,抬腳去鞋,“哪里壞了?”
曾如初就不說話死命裝鴕鳥。
他屈指在頭頂一敲:“小沒用的,脾氣還大。”
曾如初忍不住駁辯:“……我又沒玩過這個……”
損完人,傅言真往門邊走,抬手拉過玻璃門,站門框跟韓紳說話。
“師兄,找個能拉的過來。”
人前,他喊韓紳一聲“師兄”。
韓紳也是有個的,并不是那種揮之即來招之即去的狗子,能跟傅言真混的這麼的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這小子平日里傲,但隔三岔五能喊他一聲“師兄”,能給他留點面子。
沒一會兒,韓紳就拿了一把28磅的過來。
他把東西給傅言真,小聲調侃了句,“讓我弟媳婦先試試,不行我再去問他們要。”
今天來了不生,這磅數低的基本都被拿去耍了。
傅言真“嗯”了聲,說了句“謝謝”。
隔著層玻璃隔斷,韓紳站外面點了煙,饒有興趣地看傅言真在里面帶小姑娘玩。
他還是第一次在他臉上看到這種神。
一個屬于他這個年紀該有的神。
平日里,這大爺神一般都冷淡,笑呢也是皮笑不笑,很展這麼鮮活的一面。
沒多久,韓紳這一畝三分地就站了好幾個人,都著脖子往里看。
眾人七八舌的議論:
“這姑娘是他朋友吧?”
“那為什麼說是同學?這哥們不會還不好意思啊?”
韓紳想到傅言真說話時那無奈的樣子,笑了聲:“是人小姑娘不好意思,你們回頭注意點,別了底,把人嚇的下回不敢來了,到時候算賬可別怪我沒提醒。”
幾人笑做一團,表示沒見過這種稀罕事。
曾如初這回倒是拉開了,但箭到旁邊的靶子上。
傅言真被逗的不行。
韓紳看出點意思。
這公子哥好像是把人當回事。
帶玩了會兒,傅言真看了下時間,問了句:“作業帶了嗎?”
電話里,他讓曾如初帶點作業過來。
曾如初嗯了聲。
“去后面寫作業。”他換了把弓給自己用,說了句。
曾如初便回里面的休息室做自己的事。
沒別的意思,他今天就是想把人喊過來陪著。
就想把困在他這眼皮底下,一眼就看到的地方。
因為有點訓練量要完,結束的時候怕又很晚,到時候再找怕不方便。
明天又是個暴雨,出來也不方便。
莫名其妙的,他現在還真是越來越會諒人。
猜你喜歡
-
完結28 章

耳朵說它想認識你
蒲桃聽見了一個讓她陷入熱戀的聲音,她夜不能寐,第二天,她偷偷私信聲音的主人:騷擾你並非我本意,是耳朵說它想認識你。-程宿遇見了一個膽大包天的姑娘,死乞白賴逼他交出微信就算了,還要他每天跟她語音說晚安。後來他想,賣聲賣了這麼久,不當她男朋友豈不是很虧。一天睡前,他說:“我不想被白嫖了。”姑娘嚇得連滾帶爬,翌日去他直播間送了大把禮物。他報出她ID:“你知道我說的不是這個。”男主業餘CV,非商配大佬,寫著玩;女追男,小甜餅,緣更,不V 各位書友要是覺得《耳朵說它想認識你》還不錯的話請不要忘記向您臉書和推特裡的朋友推薦哦!
6.6萬字8 5275 -
完結103 章

穿成大佬的聯姻對象
執歡穿書了,穿成了替逃婚女主嫁給豪門大佬的女配,文中女配一結婚,就經歷綁架、仇殺一系列的慘事,最后還被大佬的追求者殺掉了 執歡不想這麼慘,所以她先女主一步逃了,逃走后救了一個受重傷的男人,男人身高腿長、英俊又有錢,同居一段時間后,她一個沒把持住… 一夜之后,她無意發現男人的真實身份,就是自己的聯姻對象—— 男人:結婚吧 執歡:不了吧,其實我就是個不走心的渣女 男人:? 男人掉馬后,執歡苦逼的溜走,五個月后喪眉搭眼的頂著肚子回到家,結果第二天男人就上門逼婚了 父母:歡歡現在懷孕了,恐怕不適合嫁人… 男人表情陰晴不定:沒事,反正我是不走心的渣男 執歡:… 簡單來說,這是一個‘努力逃婚最后卻懷了結婚對象崽崽、兜兜轉轉還是嫁給他’的故事,沙雕小甜餅 外表清純實則沙雕女主VS非典型霸總男主
30.1萬字8 15224 -
完結147 章

鹿生
很多人說見過愛情,林鹿說她隻見過性——食色,性也。
28.9萬字8 9248 -
完結599 章

離職后我被前上司痛哭糾纏
她是他的特別助理,跟了他整整七年,他卻一把牌直接將她輸給了別人。藍星若也不是吃素的,此處不留爺自有留爺處,她一封辭呈丟下,瀟灑離開。坐擁一億粉絲的她,富二代和世界冠軍全都過來獻殷勤,全球各大品牌爭先要和她合作。可盛景屹卻發現自己整個世界都不好了。“回來吧,年薪一個億。”藍星若莞爾一笑,“盛總,您是要和我合作嗎?我的檔期已經安排在了一個月后,咱們這關系,你沒資格插隊。”某直播間里。“想要我身后這個男人?三,二,一,給我上鏈接!”
109.3萬字5 40916 -
完結199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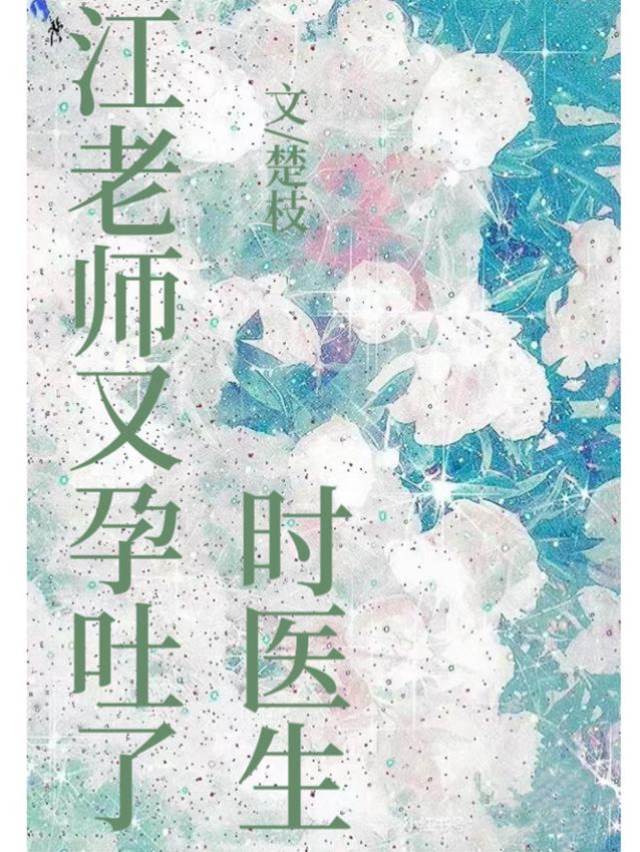
時醫生,江老師又孕吐了
【雙初戀:意外懷孕 先婚後愛 暗戀 甜寵 治愈】男主:高冷 控製欲 占有欲 禁欲撩人的醫生女主:純欲嬌軟大美人 內向善良溫暖的老師*被好友背叛設計,江知念意外懷了時曄的孩子,麵對暗戀多年的男神,她原本打算一個人默默承擔一切,結果男神竟然主動跟她求婚!*江知念原以為兩人會是貌合神離的契約夫妻,結果時曄竟然對她越來越好,害她一步一步沉淪其中。“怎麽又哭了。”他從口袋裏拿出一根棒棒糖,“吃糖嗎?”“這不是哄小孩的嗎?”“對啊,所以我拿來哄你。”*他們都不是完美的人,缺失的童年,不被接受的少數,讓兩個人彼此治愈。“我……真的能成為一個好爸爸嗎?”江知念抓著他的手,放到自己肚子上:“時曄,你摸摸,寶寶動了。”*堅定的,溫柔的。像夏日晚風,落日餘暉,所有人都見證了它的動人,可這一刻的溫柔繾綣卻隻屬於你。雖然二十歲的時曄沒有聽到,但二十五歲的時曄聽到了。他替他接受了這份遲到的心意。*因為你,從此生活隻有晴天,沒有風雨。我永遠相信你,正如我愛你。*「甜蜜懷孕日常,溫馨生活向,有一點點波動,但是兩個人都長嘴,彼此相信。」「小夫妻從陌生到熟悉,慢慢磨合,彼此相愛,相互治愈,細水長流的故事。」
35萬字8 30977 -
完結20 章

傾其所有去愛你(平裝版)
【霸道總裁+現言甜寵+破鏡重圓】落難千金自立自強,傲嬌總裁甜寵撐腰!【霸道總裁+現言甜寵+破鏡重圓】落難千金自立自強,傲嬌總裁甜寵撐腰!龜毛客人VS酒店經理,冤家互懟,情定大酒店! 酒店客房部副經理姜幾許在一次工作中遇到了傲驕龜毛的總統套房客人季東霆。姜幾許應付著季東霆的“百般刁難”,也發現了季東霆深情和孩子氣的一面。季東霆在相處中喜歡上了這個倔強獨立的“小管家”。姜幾許清醒地認識到兩人之間的差距,拒絕了季東霆的示愛,季東霆心灰意冷回到倫敦。不久后,兩人意外在倫敦重逢,這次姜幾許終于直視內心,答應了季東霆的追求。正在季東霆籌備盛大的求婚儀式時,姜幾許卻與前男友沈珩不告而別。原來沈珩與姜幾許青梅竹馬,在姜幾許家破產后兩人被迫分手。季東霆吃醋不已,生氣中錯過了姜幾許的求助……
28.4萬字8 170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