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頑烈》 第5章
曾憶昔的車停靠在校門口外兩百米的地方。
還是早上的那輛黑路虎。
造型有點招搖,但跟不遠的庫里南一比,倒遜了不。
庫里南的車牌還是一串連號。
沒多久,看到傅言真和左昕晗一前一后上了車。
傅言真走的很快,左昕晗幾乎是小跑著才趕上他。
只看了一眼,便收回視線。
因為看到曾憶昔在被人搭訕。
他這車窗是搖下來的,一條手臂還出窗外,閑閑掛著。
也是個皮相出眾的,半在外的英俊側臉引起不人看。
有個膽大的生過來問他要聯系方式,上還穿著他們雅集的校服。
曾憶昔看一眼,嗤了聲,讓回家寫作業。
生說“沒什麼作業”,還想再跟他扯扯淡。
曾憶昔懶得搭理,手臂撤回,將車窗搖起來,車門也上了鎖。
生朝他做了個鬼臉。
曾如初走過來,抬手扣了扣車窗。
曾憶昔解了車門的鎖,讓進來。
看他里叼著的半截香煙,曾如初蹙了下眉,“怎麼又上了?”
車上的氣味有些繁復。
煙草和艾草織出來的怪味。
曾如初想起來沈鄰溪今天要去醫院做理療,這幾年不太好。
本來回家還想告曾憶昔黑狀的,但這回也不想去惹沈鄰溪不開心。
皺了下鼻,重新打開車窗。
曾憶昔嗤了聲,嘲笑事多。
不不愿地摘下煙,煙圈朝窗外吐。
他另一只手搭在方向盤上,指尖輕點了兩下。
曾如初真的想跟他吵一架,憋了一天了,一肚子火呢。
但人家好歹還來接。
車子向前行駛,晚風從大開的車窗里涌進。
江城的植被覆蓋率還算不錯,風里的氣味倒是很清新。
Advertisement
曾如初現在很困。
昨晚沒睡好,中午教室也很吵。
很想瞇一會兒。
“今天老師沒拖堂麼?”但曾憶昔找說話。
“沒有。”曾如初有氣無力地應了聲。
曾憶昔看一眼,發現這臉有點臭,問了句:“你這怎麼了?”
曾如初:“累。”
“……”
十字路口,紅燈高掛,一輛輛私家車首尾相顧,連一條龍。
等待的時間有些漫長,還有人按起了按喇叭。
曾憶昔偏過臉問要不要關窗,卻看到那邊的“風景”。
他嘖了聲,嗓間溢出一聲淡嘲。
曾如初也偏過頭看了眼。
另一車道。
校門口的那輛庫里南正與他們“并駕齊驅”。
因為是紅燈,它也穩穩停著,后車窗完全搖落。
車上的人手肘支在窗沿,修長五指虛握拳,半撐在額角,擋起半張臉。
似是有所應,傅言真將手移開,眼皮不急不慢地抬起,眸準接上曾如初遞來的視線。
但人被他看了兩秒,就別過臉不讓他瞧。
甚至把那邊的車窗給升了上去。
……
傅言真勾了勾。
“怎麼了?”曾憶昔挑了下眉。
“有尾氣。”曾如初說。
曾憶昔淡嘲:“你們的事可真多。”
“不是你們男生喜歡沒事找事嗎?”曾如初這回語氣有點沖。
“……”曾憶昔嘶了聲,“你這叛逆期到了是吧?”
曾如初不說話了。
綠燈終于亮起。
后視鏡里,庫里南的前燈打著右轉信號。
他們是直行。
--
傅言真看著向前駛去的路虎,角笑意更明顯。
這蘑菇,脾氣還大。
剛剛那反應,明顯是給他臉看。
“你在看什麼啊?”左昕晗見他視線一直在外,湊過臉問。
“沒什麼。”傅言真撤回視線看著手機,并未看。
“……我昨天生日,你不來就算了,你都沒有禮嗎?”左昕晗忍不住道出心里的憋屈。
但語氣還是小心翼翼的,聽著跟撒似的。
傅言真神淡漠:“我媽沒給你買?”
“……阿姨買的,跟你送的不一樣。”左昕晗聲音有些膽怯。
傅言真笑了聲,卻沒說話。
左昕晗攥著擺,心漸漸冷了下來,卻又不想這麼跟他僵著,剛想說點什麼,手心突然一暖。
低眸一瞧,是條項鏈。
欣喜來的過于突然。
“你言阿姨買的,”傅言真卻立即掐滅了的喜悅,“讓我送的。”
東西給他的時候不是現在這樣子,裝在一個致的絨禮盒里。
他嫌麻煩,所以將盒子給扔了,現在就一條禿禿的項鏈。
在兜里揣放久了,所以沾著點溫。
“……”
左昕晗怔怔地,心一下沉江底。
前面的司機聽著有些不對勁。
夫人早上讓他去送東西時,可是囑咐了好幾遍,要傅言真千萬不要說是買的。
“不喜歡啊?”傅言真邊玩游戲邊說話,“不喜歡就扔了。”
“……你為什麼不準備?”左昕晗問。
傅言真淡笑:“我為什麼要準備?”
左昕晗:“……”
“你這生日一過,多大了?”傅言真睨著眼手腕上的疤,“能對自己行為負責了吧?”
這疤是自己割的,要死要活的要跟他一起。
左昕晗是個大小姐脾氣,也是從小被人捧著,喜歡天上的月亮家里人都要使勁兒給夠一夠。
習慣了什麼都要得到。
從本質上說,他們可能是一類人。
但同相斥。
他最厭束縛。
偏偏這一個兩個都要想來勒住他。
傅言真看的眼神像北方冬日的清晨。
眼神平靜,但是覆著一層風霜。
神更是忍耐到極限的癥候。
左昕晗:“……”
不是看不懂傅言真的臉。
傅言真從不大聲說話,語調也沒什麼抑揚頓挫。
就這麼淺淺淡淡的,卻比聲嘶力竭都讓人心冷。
“……我要下車。”左昕晗拼著最后一口氣說。
但心里是知道這里不能下車,還是在耍脾氣而已。
“可、可這里不能下車……”司機著實無奈。
“我說我要下去!”
眼淚在眶里直打轉,左昕晗又吼了一句:“你耳朵聾了嗎?”
“……”司機也快哭了。
“前面,路邊停一下。”傅言真放下手機,淡聲吩咐。
司機無可奈何,他就一幫人開車的,人微言輕能有什麼辦法。
只好照做。
沒一會兒,車便靠邊停下。
傅言真將手機揣回兜里,一條長臂抻直,五指向車門。
門鎖輕微一聲響,出一道隙。
風順勢往里鉆進,還攜著夜晚清涼的溫度。
一片月跟著,將那雙寡冷的眼映的分外深刻。
--
回到家。
沈鄰溪坐在客廳的沙發上,上披著件坎肩,面在燈下顯得有些蒼白。
屋子里還有淡淡的苦藥味。
看他們的眼神充滿期待,明顯是想聽聽曾如初在新學校的生活。
盡管今天是這麼悲催和倒霉,在面對沈鄰溪時,曾如初卻沒說一句不好的話。
路上就琢磨回來該怎麼說,東拼西湊的想了一些趣事,回來便一一說給沈鄰溪聽。
沈鄰溪被哄得很開心,以為真在雅集過上了什麼好日子。
雅集的作業并不多,在晚自習的時候就寫完了。
睡覺之前,習慣地打開書桌右側的屜,從里面出那只舊手機。
在攔截框里看到悉的號碼,并且也多了條信息。
那人又發短信來罵。
剛準備將手機放回去,一通電話打了過來。
接了接聽,證明自己還在用這個號碼,因為不想讓自己新的聯系方式被找到。
那人似乎也只是要確認是不是還在用。
通了之后,那邊惻惻笑了幾聲,又給掛了。
--
一覺醒來,時間尚早。
曾如初沒有賴床的習慣,眼睛睜開沒幾秒,就下了床。
沒開燈,赤腳走到窗邊。
將窗簾向兩邊拉開,飄窗朝外推,天是黯淡深沉的藍灰。
清涼晨風路過,送來酪的甜香。
洗漱完,準時下樓。
餐廳里,早餐已經擺好,就一個人的分量。
一份巖燒酪,一份蔬菜水果沙拉,沈鄰溪有點強迫癥,紫甘藍切的長短細都均勻一致。
咖啡香氣濃郁,黑上鋪著一層細泡。
全家就喝咖啡要加。
曾憶昔被喊起來送去學校,此時坐在客廳的沙發上,一臉困倦的發著呆,懷里還攬著個抱枕,沒個魂似的。把送到學校后,他回來必然是要補個回籠覺。
“你就像個野人。”沈鄰溪看他這窩頭,催促他趕去洗漱。
曾憶昔打了個哈欠,拖著綿無力的步子回了樓上。
餐桌上放著一只寬口花瓶,里面著一束無盡夏,一大簇一大簇的開著。
用餐時,沈鄰溪就坐在對面的椅上看吃,眼里含著笑。
曾如初每一口都咀嚼的很仔細,對食有種虔誠。
這讓做食的人很滿足。
不像曾憶昔,吃飯時不是在玩手機,就是在手機的路上,天心不在焉地,給他吃豬糠怕也就是那麼回事。
早餐吃完后,沈鄰溪送到門口。
出門前,又了的頭,溫言囑咐了句,“在學校多和同學們說說話,多認識幾個新朋友。”
曾如初點頭說“好”。
在曾憶昔的車上,從書包側袋拿出耳機盒,邊戴耳機,邊在手機里調出一個歌單。
歌單里都是英語文。
第一首是葉芝的《When You Are Old》。
“你手機不是被老師沒收了麼。”曾憶昔瞥了眼手里的東西,有些奇怪。
猜你喜歡
-
連載1504 章

夫人她A爆全世界
【甜寵,重生,虐渣,馬甲,團寵】“還逃嗎?”秦初使勁搖頭:“不逃了。”放著這麼好看的男人,她再逃可能眼睛真有病,前世,因錯信渣男賤女,身中劇毒鋃鐺入獄,自己最討厭的男人為替自己頂罪而死,秦初悔不當初,重回新婚夜,秦初緊抱前世被自己傷害的丈夫大腿,改變前世悲慘人生,成為眾人口中的滿級大佬。人前,秦初是眾人口中秦家蠢鈍如豬的丑女千金,人后,秦初是身披各種馬甲的大佬,某天,秦初馬甲被爆,全
135.4萬字8 16222 -
完結146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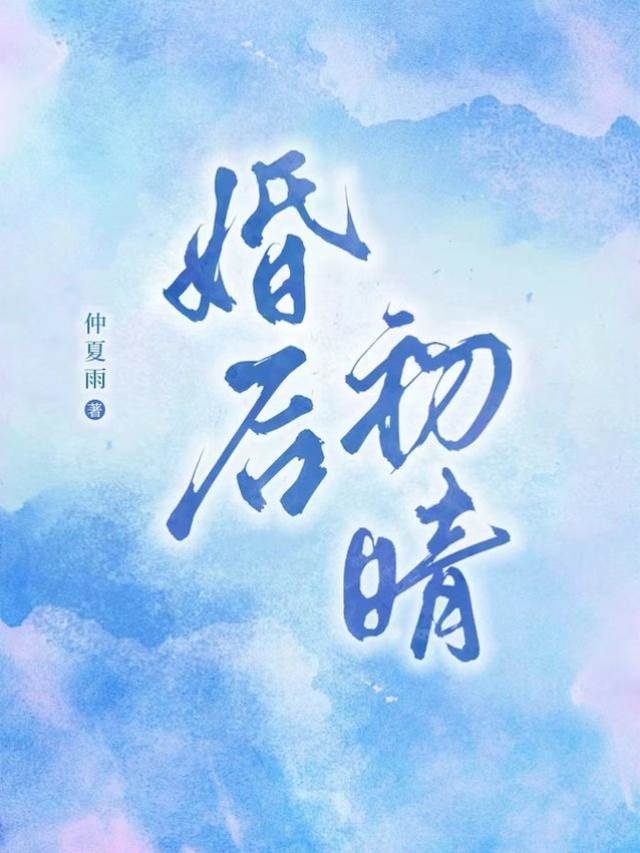
婚後初晴
沈頤喬和周沉是公認的神仙眷侶。在得知沈頤喬的白月光回國那日起,穩重自持的周沉變得坐立難安。朋友打趣,你們恩愛如此有什麽好擔心的?周沉暗自苦笑。他知道沈頤喬當初答應和他結婚,是因為他說:“不如我們試試,我不介意你心裏有他。”
27.2萬字8 4900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