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攀不起的大佬是我的[重生]》 第45章
清晨時分, 溫眠迷糊間覺得有些不對勁。
的手仿佛被束縛住了,鼻尖縈繞著不屬于的氣息,其次間能到輕的力道。溫眠睡得不深, 一下驚醒, 而后對上了鐘遠的視線。
“你在干什麼?”環繞一圈, 臥室線昏暗,四周安靜祥和。
為什麼鐘遠會出現在的臥室?
“你怎麼一親就醒。”鐘遠輕言輕語說了一句, “我早上要出去一趟, 華天找我。”
溫眠迷糊點頭, 看著他淡定松開的手, 然后下床。
突然反應過來:“這跟你親我有什麼關系啊!”
“沒關系。”他靠在門口笑, “眠眠,你好可。”
對他毫無防備, 晚上睡覺門也是開著。他在客廳能看到睡著的模樣,瘦小的個子,躺在床上仿佛整個人都要埋進去了一般,這畫面中了鐘遠的萌點, 沒忍住進去親了一口。
結果一親就醒,還茫然問他為什麼親。
可可。
鐘遠跟溫眠吃了一頓早餐后就分開了。就算華天不找他,他拋下醫院的事離開,也需要去給個說法。溫眠跟鐘遠分開后就回家了, 像平常一樣開始做題。
這學期有一個重要的會考,考試容便是九門科目,因此溫眠不得不重拾理科科文。
老師發了很多資料下來, 但是有些題目并不是看了資料就能做出來的。溫眠寫著輔導書,大部分題目是明白的,小部分題目看了答案也不太明白。
中午鐘遠并不回來,溫眠出去吃完飯回來,又繼續死磕著那些題。學習的時間總是過得特別快,溫眠約聽到門開的聲音,接著客廳響起放東西的聲音,以及走進臥室的腳步聲。
Advertisement
“好想你。”他從后面抱住,側頭親了一下。
“別鬧,我寫題呢。”
鐘遠跟著看桌上攤開的題目,“中間那題怎麼沒寫?”
“不會。”嘆了口氣,“想不出來明天就去問老師。”
“我會。”他抓住的右手,依著這樣的姿勢開始給講解題干,又用筆圈出幾個關鍵詞,在空白寫了兩個公式,溫地開始講解。從如何運用公式,到每一步的計算,溫細致,簡直就是當代好老師模范。
溫眠一點就通,哇了好幾聲:“鐘遠你好厲害呀,我覺得這方法比答案要好理解。”
鐘遠被夸得眉開眼笑:“還有哪里不會?”
溫眠當即又找出幾道題,每次鐘遠一看題目就會,帶著一步步分析。溫眠恍然大悟之余又附上一大通彩虹屁。
“鐘老師厲害嗎?”他笑著問。
“厲害厲害!”溫眠狂點頭表示贊賞。
“那什麼時候給老師結下補課費?”
“……”
鐘遠看的表,眉頭一挑:“你還想賴賬?”
“小本生意,恕不賒賬。”他慢悠悠地說道。
溫眠當即拿出自己的錢包,拍在桌上:“多錢,盡管說。”
鐘遠出食指搖了搖:“一道題一個吻,不過分吧。”
“……”溫眠嘟囔著,“你怎麼不早說?”
“早說了這麼給你反悔的機會?”
“那為了不辜負你的苦心,我決定用掉這個機會。”溫眠笑瞇瞇地看著鐘遠,他出無奈的笑,手的臉,“走了,去吃飯。”
時鐘慢慢指向六點,窗外天暗下,兩側路燈接連亮起來。
兩人牽著手慢慢走著,溫眠一時興起要走臺階上的路,但苦于平衡不好,歪歪扭扭,半晌都走不了幾米。
“鐘遠。”溫眠自然地出手,“扶一下我。”
鐘遠牽住的手,溫眠仍不滿意:“過來點,這樣我使不上勁。”
他又走過來了一點,語氣無奈:“這樣可以嗎?”
站在臺階上,輕輕踮腳,快速地在他臉上親一口,而后笑嘻嘻道:“可以呀,剛剛好。”
鐘遠愣了一下,下意識捂著被親的部位,而后他朝四周看看,手按住的肩膀:“現在沒人,再親幾下。”
“去去去……”溫眠彎腰,靈活從他手下鉆了出來。
周末很快過去,早上溫眠背著書包準備出門時,鐘遠仍抱著電腦在沙發上坐著。于是溫眠又從玄關回到了沙發:“你不打算去學校了嗎?”
“去啊,晚一點。”他湊過來親溫眠一口,聽到溫眠問:“要我等你嗎?”
“不用。”
他剛說完,溫眠一下就知道他的意圖:“你是不是怕別人知道我們住在一起,對我影響不好啊?”
“跟一個窮小子住在一起,又不是什麼值得炫耀的事。”
“我不介意這些。”溫眠腦袋抵在他肩膀上。
“總歸風評會不好的。”他親親的臉,哄道,“等我把你娶回家了,再到炫耀好不好?”
溫眠被逗笑,捶了捶他的膛,臨走前認真說:“我也不是十六七歲的高中生,很多事我已經看淡了,別人的看法對我來說沒有那麼重要。”
鐘遠嗯了一聲,溫眠覺得他聽進去了,但鑒于對鐘遠的了解,覺得兩個人理解的方面可能不太一樣。
果不其然,當晚溫眠被鐘遠拉著走到學校的小樹林時,心復雜。
“被老師抓到就完了。”道。
“不會的。而且別人的看法沒有那麼重要。”
“……”
鐘遠見沉默,問:“害了?”
“……”
“你也不是十六七歲的高中生……”
溫眠惱怒:“閉!”
鐘遠在邊低低笑了出來。
最后兩人只是在小樹林中走了一圈,連手都沒有牽。
溫眠一路都在聽鐘遠介紹:“等以后我們上了大學,北北天天在小樹林親都沒有人會舉報。”
溫眠:“……”謝謝,不是很想聽。
大概是小樹林的后癥太明顯了,溫眠竟然半夜驚醒,滿腦子都是小樹林里黃黃綠綠的事。黑暗中,心有余悸地自己的口,翻個正準備繼續睡,卻瞧見客廳里傳來微弱的。
坐起來,發現鐘遠還沒睡。
他坐在地毯上,電腦放在前的茶幾上,屏幕上幽幽的照在他的臉上,描繪出他認真專注時的廓。下一秒,他朝臥室方向看過來:“吵醒你了嗎?”
“做噩夢了。”溫眠在他邊坐下,“你怎麼還沒睡?”
“有點事沒弄好。”鐘遠說,“馬上就睡。”
溫眠嗯了一聲,卻沒走,頭一歪靠著他的肩膀:“我好像都不知道你幾點睡的。”
這幾天他睡得比晚,起得比早,簡直像是不需要睡眠一樣。
“就今天晚了點。”鐘遠平靜地說道。
溫眠沒再多說什麼,但因為心里念著這件事,第二天凌晨同樣的時間,溫眠在睡夢中醒來。坐起來,沒看見客廳的燈,但并不放棄,從臥室走了出來,看到鐘遠坐在桌前辦公。
兩人目隔著昏暗的目對視,溫眠聽到鐘遠說:“眠眠,過來。”
走過去,鐘遠拉著在他上坐下來。
“我其實已經習慣這個作息了。”他說的是上輩子,“不是故意要這樣。”
溫眠窩在他懷里,摟著他的脖子,安安靜靜的:“我希你健康。”
“我會的。”鐘遠說,“這輩子我還想和你長長久久呢。”
溫眠輕輕嗯了一聲,又道:“我覺得現在已經很幸福了,不用很大的房子,也不用很多的服,或者其他的質條件,只要有你我就很滿足了,我是不是給你太大的力了?”
黑暗中,他輕笑一聲,溫眠覺到他抓著的手,放在邊親了一口:“我家眠眠真好養。”
“不過,就算給你世界上最好的一切,對我來說也沒什麼力。”他說,“相不相信我?”
溫眠點點頭,頓了頓又道:“對不起。”
“為什麼說對不起?”他疑。
“你是不是本睡不著?”這一刻,溫眠覺得自己的猜測有幾分道理,“上輩子我離開后,你是不是就不太能睡得著了?”
說出猜測,鐘遠便沉默了,幾秒后才否認:“不是的。”
溫眠捂住他的:“別騙我,我了解你。”
五分的不確定在見到他的反應后都得到了證實。
溫眠一下就猜到了真相,的眼眶立馬紅了,鐘遠手忙腳開始哄溫眠,無奈之下說了真話:“給我點時間,眠眠。”
上輩子,深的人離世,痛苦是真的,失眠也是真的。
若是一輩子未曾擁有,大抵也不會有擁有過卻又失去來得痛苦。溫眠離開后的那一個月里,鐘遠本睡不著,無人的夜里他常常著天花板發呆,他崩潰過,痛哭過,卻始終沒放過自己。
時會慢慢消磨他臉上濃烈的緒,當無法抹去那些刻在骨子里的沉痛。他變得平靜與斂,卻未曾放棄與時間、與記憶搶奪與溫眠有關的一切。
想起會心痛,會有強烈的緒起伏,以至于難以睡。可若不想,鐘遠做不到看著溫眠在他的回憶中慢慢失。
更不要說睡夢中偶爾會夢到溫眠,他總會激烈地、瘋狂地想要拉住,而往往下一秒,他會在安靜的房間里清醒,明白那只是一個夢。
有些,熬過了時間與回憶,并在那漫長的等待中燃熊熊大火。
這輩子鐘遠總告訴自己,不要太急切,怕嚇走,也怕難過。他知道自己已經抓住了溫眠,可是在每個安靜的夜里,他無數次抬頭看著天花板,不知道這是否又是一個夢。
猜你喜歡
-
完結574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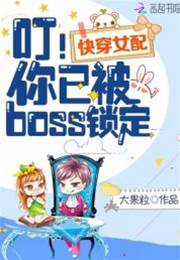
快穿女配之你已被boss鎖定
阮綿綿隻想安安分分地做個女配。 她不想逆襲,也不想搶戲,她甘願做一片綠葉,襯托男女主之間的純純愛情! 可是為什麼,總有個男人來攪局?! 阮綿綿瑟瑟發抖:求求你,彆再纏著我了,我隻想做個普通的女配。 男人步步逼近:你在彆人的世界裡是女配,可在我的世界裡,卻是唯一的女主角。 …… (輕鬆可愛的小甜文,1v1,男主都是同一個人)
103萬字7.83 14294 -
完結231 章

離婚夜,植物人老公扒光我馬甲
成為植物人之前,陸時韞覺得桑眠不僅一無是處,還是個逼走他白月光的惡女人。 成為植物人之後,他發現桑眠不僅樣樣全能,桃花更是一朵更比一朵紅。 替嫁兩年,桑眠好不容易拿到離婚協議,老公卻在這個時候出事變成植物人,坐實她掃把星傳言。 卻不知,從此之後,她的身後多了一隻植物人的靈魂,走哪跟哪。 對此她頗為無奈,丟下一句話: “我幫你甦醒,你醒後立馬和我離婚。” 陸時韞二話不說答應。 誰知,當他甦醒之後,他卻揪著她的衣角,委屈巴巴道: “老婆,我們不離婚好不好?”
56.4萬字8 19064 -
完結81 章

仲夏呢喃
霖城一中的年級第一兼校草,裴忱,膚白眸冷,內斂寡言,家境貧困,除了學習再無事物能入他的眼。和他家世天差地別的梁梔意,是來自名門望族的天之驕女,烏發紅唇,明豔嬌縱,剛到學校就對他展開熱烈追求。然而男生不為所動,冷淡如冰,大家私底下都說裴忱有骨氣,任憑她如何倒追都沒轍。梁梔意聞言,手掌托著下巴,眉眼彎彎:“他隻會喜歡我。”-梁梔意身邊突然出現一個富家男生,學校裏有許多傳聞,說他倆是天作之合。某晚,梁梔意和裴忱走在無人的巷,少女勾住男生衣角,笑意狡黠:“今天賀鳴和我告白了,你要是不喜歡我,我就和他在一起咯。” 男生下顎緊繃,眉眼低垂,不發一言。女孩以為他如往常般沒反應,剛要轉身,手腕就被握住,唇角落下極輕一吻。裴忱看著她,黑眸熾烈,聲音隱忍而克製:“你能不能別答應他?”-後來,裴忱成為身價過億的金融新貴,他給了梁梔意一場極其浪漫隆重的婚禮。婚後她偶然翻到他高中時寫的日記,上麵字跡模糊:“如果我家境優渥,吻她的時候一定會肆無忌憚,撬開齒關,深陷其中。”·曾經表現的冷漠不是因為不心動,而是因為你高高在上,我卑劣低微。 【恃美而驕的千金大小姐】×【清冷寡言的內斂窮學生】
40.2萬字8.18 4839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