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明今夜想你》 第62章 羈絆
馳厭就著這個姿勢抱住, 懷里的姑娘小聲抱怨:“外面可真是冷啊馳厭,我手都快凍僵了。”
馳厭把放下, 無聲握住的一雙手。在他掌心,一雙小手涼得像冰一樣。
卻笑盈盈的, 長睫上雪花融化,變晶瑩的水珠, 簡單又好懂, 馳厭幾乎一下子看懂了的緒——還說不心疼我。
馳厭低眸笑了笑:“在你大伯家不好玩嗎, 他們對你不好?為什麼會回來?”
姜穗搖搖頭:“大伯很好的, 只是我一想到你一個人, 就特別想回來。”
走出門后, 冬夜的風雪似乎也不冷, 心里燃燒著一個念頭, 想要陪在他邊。
馳厭什麼也說不出來。
姜穗夜里匆忙趕過來, 早就困倦了,眼睛:“馳厭,有什麼我們明天再說啊, 我好困。”
馳厭注視著, 低聲說:“穗穗,新年快樂。”
笑了:“明天才過年呀,現在都還沒過十二點, 你怎麼也像我一樣口不擇言?”
馳厭便也笑了:“嗯。”
姜穗回房間之前, 馳厭住:“穗穗!”
回眸。
馳厭道:“還有什麼愿沒有實現嗎?”
姜穗愣了愣, 隨即認真搖搖頭:“沒有了, 我心很小的,爸爸能健康起來,就是我唯一的愿。”
他眸像夜,倒映出的模樣,姜穗見他只是注視著自己,于是又往房間走。
馳厭突然幾步追上來,他息著,捧住臉頰。
姜穗困道:“馳厭,你怎麼啦?”
男人一言不發,卻驟然抬手關了燈。
冬夜沒有月,花園小洋房外漆黑一片,這樣的夜里,誰也看不見誰。
他聲音喑啞:“我只想看看你。”
Advertisement
姜穗糯聲道:“可是關了燈就看不見了。”
“那就給我抱一抱,我有些想你了。”
男人嗓音又低又沉,姜穗疑極了,抬手想開在邊的燈。
馳厭握住的手,驟然附抱住。
這個懷抱極其漫長,像是要就這麼過一輩子。
他下擱在肩窩,姜穗看不見他早已經紅的眼眶,只能聽見他紊的呼吸。
還有這個冬夜里,肩膀上突如其來淺淺的潤。
是還有雪才化嗎?
黎明以前,馳厭走出了房子。
雪已經停了,鋪天蓋地滿世界都是白,這個冬天可真是冷。他失控也只有那麼一瞬間,隨即把哄睡著了。
一墻之隔,溫暖的房子里面,睡著他最喜歡的人。而一墻之外的風雪中,他選擇一步步離開。
他的神重新變得冷漠起來,顯得尖銳又輕慢。
一行車停在一里之外,安靜地等著他。
他走過去了,眾人沖他微微鞠躬。
馳厭坐上車,水的神也變得凝重而嚴肅。馳厭說:“開車。”
回橫霞島嶼,先要坐飛機,然后轉水路。
水一直沒說,馳厭晚來了好幾個小時。
好在現在馳厭看上去冷沉毫無緒,似乎并沒有任何懦弱的緒可以影響他。
然而車子啟前,所有人都愣住了。
花園那邊,走過來一個穿著冬天睡和棉拖鞋的姑娘。
水不自咽了咽口水:“boss。”
馳厭轉頭,就看見了車窗的。
冬夜里,只有路燈有昏黃的,眸中漸漸蔓延上水汽。看著他們的方向——
一行整整齊齊的車,還有為首坐得端端正正的男人,他瞳孔里盛滿煙灰,里面淡得像沒有任何東西。
姜穗想,踏過冬天厚厚的積雪,來到他邊,那時候多希他這輩子能夠不再孤獨,開心一些。
可他卻不要了。
甚至沒有解釋,也沒有離別。
第一次,首先想到的不是馳厭離開以后到底要怎麼逃開馳一銘,而是馳厭的心是石頭做的嗎?
石頭也該捂化了啊。
馳厭轉過頭,冷靜地命令道:“開車。”
司機得了令,踩下離合。
車子開始慢慢啟了。
跑向他:“馳厭!”
聲音并不夠大,甚至因為礙事的棉拖鞋,跑得并不快,小小一個人影,渺小地像一只飛蛾。
看著他走遠,到底還是哭了。
水用盡意志力,沒敢看姜穗一眼。
馳厭坐得端端正正,像是沒有到這一切,他神冷靜得要命。仿佛這不是別離,也不是不辭而別的拋棄,而是一場路過的風,一滴冰冷的雨,不能阻擋他腳步的塵埃。
車里很安靜,安靜得聽不到車窗外的風聲。
他們漸漸看不到那個又可的了。
水才聽見他boss淡聲問:“雪是不是快化了?新年到了吧。”
一個無關要的問題,在這樣的夜里,讓人不著頭腦。
水側頭看馳厭,正在小心翼翼斟酌用詞。卻一時驚駭,一個字也說不出來。
馳厭怔愣著,拇指了角滲出來的。
或許連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說什麼。
姜穗站了許久,大風把眼淚吹干,眼里干又難。
知道他不會回頭。
馳厭這輩子,從來沒有回過頭。他苦過累過,被人折辱恥笑,可他沒有哭過,也從未回過頭。
這場奇怪的羈絆,伴隨著新年的離別結束了。
的人生還得繼續,姜穗蹲在路燈旁哭完了,站起來回到房子里。
蜷著躺回床上,用被子裹自己。
姜穗想,明天就離開!
然后明天就把馳厭忘掉。才不是姜雪,被高均放棄一萬次,像不知道傷痛一樣,還要往上湊。
而且明白,找不到馳厭了。
渾渾噩噩睡了一夜,醒來眼睛腫了,姜穗的枕頭,才知道夢里原來也哭了。
這世上沒人了,除了爸爸。
堅強地穿好服,收拾好自己的東西,馳厭給的卡、給買的服飾品,一樣沒拿。
等關好了門,姜穗把鑰匙從窗戶里扔了進去。
他不要了,也不要這個房子。所以這里也不是的家了。
姜穗知道自己狀態不太好,深吸一口氣,決定先回大院兒。不管是姜水生還是姜雪,看見紅通通的眼睛一定會擔心。
今天就會好起來了。
然后有更重要的事,爸爸還得治病呢。
今天是除夕,大院里卻安安靜靜。幾顆榆樹堆滿了積雪,看不出原本的模樣。
才恍然記起,這里也不是小時候熱鬧的模樣了,它已經被馳厭收購,住的人寥寥無幾。
姜穗為自己下了一碗面,暖了暖手,又輕輕挨了挨臉頰,到了暖和舒服。
姜穗笑了。
誰都會長大,是不是?好像這些事,一個沒多的人,也沒那麼大不了。
窗外攝像頭一閃,在雪地中微不可察。
馳厭看著手機里發過來的電子照片,他手指挨著,克制著沒過多的表。
再過不久,他們就抵達橫霞島嶼了。
發電子郵件的人說:沒有冷著,也沒有著,回家了。
那就好,這就很好了。他慶幸沒有自己這樣極端的,馳厭平靜地關了手機,將號碼永久清除。
穗穗,回家就好。
春節時,姜穗狀態已經好起來了。
打算去醫院陪著姜水生。
這次姜水生高興地沖揮揮手:“穗穗來了。”
姜穗點點頭,見爸爸吃力要下床的模樣,趕過去扶住他。
見他這樣虛弱,眸中出一驚怕。
姜水生卻笑得開懷:“我的病好了,只是手以后還不太能走,但是我覺自己好多了。穗穗,等恢復了,爸爸覺得還能再養你幾年。”
姜穗怔住:“爸爸病好了?”
姜水生樂呵呵說:“對,前段時間復查沒有問題,手很功。嚇壞了你嗎?我怕你擔心,馳先生也建議完全確認好起來再告訴你。”
“什麼時候做的手。”
“十二月的時候。”
姜穗輕輕抿了抿,心里到底還是喜悅居多,眼里也帶上了笑意。
姜水生拍拍肩膀:“我知道你把房子什麼的都賣了,拜托馳先生幫忙,他也確實盡心盡力,可惜了你媽媽留下的房子。但是沒關系,我們都努力一點,以后也能住上新房子。”
姜穗心中震驚,家房子,戶主依舊沒有變更。
然而姜水生卻以為是賣掉了房子,給了馳厭所有積蓄,馳厭才愿意幫這個忙。
看著父親欣又嘆的臉,突然明白,馳厭抹掉了一切與在一起過的痕跡。
他還給了一個純白的世界,將推回到原本的生活中。
依舊可以過簡單無憂的生活。
初二的時候,收到了學校的一個電話。
姜穗那時候在給姜水生洗蘋果,姜水生說:“穗穗!電話。”
姜穗干凈手,點開接聽鍵。
電話那頭溫雅的生說:“姜穗同學,你的留學申請已經過了,可以去往國的大學進行學習,留學期間一切公費,每月還有兩千元補助,介于你的家庭況,我們在那邊為你申請了免費住宿,你可以帶著父親一同過去。”
姜水生震驚了一瞬,等掛了電話,他驚喜而不確定地問:“穗穗,這是真的嗎?”
姜穗眼眶熱熱的。
不是真的。
從來沒有申請過留學,r大這樣的二流大學,也鮮有留學名額,還有每個月一萬多的人民幣補,不會有哪所學校這樣慷慨這樣笨。
唯一能想到的理由,是曾經握住他的手,聲請求道。
“未來無論發生什麼事,也不要把我丟給馳一銘好不好?”
那晚月人,男人注視著的眼睛,沉默片刻道:“我盡力。”
那時候失落極了,可2006年開春,第一次明白,原來他早就什麼都給了。
猜你喜歡
-
完結271 章

且以深情共余生
相似的聲音,相似的容貌,遇見了同一個他。兜兜轉轉,走走停停,時光不改蹉跎。如果上天再給她一次重新選擇的機會,她一定奮不顧身愛的更加用力!
50萬字8 9205 -
完結378 章

玄門回來的假千金又在擺攤算卦了
肖梨在玄門待了一百年,同期進來的那條看門狗小黑,都已經飛升上界,她還只能守著觀門曬太陽。老祖宗顯靈告訴她,“肖梨,你本來自異界,塵緣未了,若想飛升,还得回去原来的地方,了却凡尘杂事,方可勘破天道!” 回到现代,肖梨成了鸠占鹊巢的假千金,这一世,没有留念,两手空空跟着亲生父母离开肖家。 圈内人都在等着,肖梨在外面扛不住,回来跟肖家跪求收留。 却不想…… 肖梨被真正的豪门认回,成为白家千金,改名白梨。
64.4萬字8 60458 -
完結189 章

荒腔
沈弗崢第一次見鍾彌,在州市粵劇館,戲未開唱,臺下忙成一團,攝影師調角度,叫鍾彌往這邊看。 綠袖粉衫的背景裏,花影重重。 她就那麼眺來一眼。 旁邊有人說:“這是我們老闆的女兒,今兒拍雜誌。” 沈弗崢離開那天,州市下雨。 因爲不想被他輕易忘了,她便胡謅:“你這車牌,是我生日。” 隔茫茫雨霧,他應道:“是嗎,那鍾小姐同我有緣。” 京市再遇,她那天在門店試鞋,見他身邊有人,便放下了貴且不合腳的鞋子。 幾天後,那雙鞋被送到宿舍。 鍾彌帶着鞋去找他。 他問她那天怎麼招呼都不打。 “沈先生有佳人相伴,我怎麼好打擾。” 沈弗崢點一支菸,目光盯她,脣邊染上一點笑:“沒,佳人生氣呢。” 後來他開的車,車牌真是她生日。
28.8萬字8 1773 -
完結196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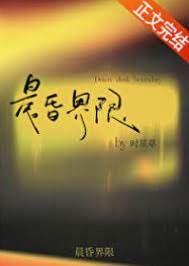
晨昏界限
林霧有些記不太清自己和陳琢是怎麼開始的,等她後知後覺意識到事情變得不對勁時,他們已經維持“週五晚上見”這種關係大半年了。 兩人從約定之日起,就劃分了一條明顯的,白天是互不相識的路人,晚間是“親密戀人”的晨昏界限。 而這條界限,在一週年紀念日時被打破。 - 人前不熟,人後很熟的故事TvT
27萬字8 5640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