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緋聞戀人》 第052章
其實簽下合約的那天, 不是兩人久別之后第一次見面。
第一次重逢, 是在十八歲那年的夏天。
那時秦郁絕雖然轉學,但學籍仍然在原來的學校。所以高考的時候, 得回到柳川市的考場進行考試。
那是一年之中最熱的時候。
大批的學生涌考場學校,站在教學樓下面等待著考場的開放。度極高的人群, 讓空氣仿佛都變得稀薄。
頭頂上是烈日, 曬得人腦袋發暈。
多數人都和邊識的同學聊著天, 三個兩個聚一塊。
同學給謝厭遲占了一涼地, 扯著他邊說著有一搭沒一搭地聊著天,邊用手在額頭上搭起個小帳篷, 四張:“讓我看看別的學校有沒有什麼好看的漂亮妹妹。”
謝厭遲后背抵著墻,懶洋洋地打著哈欠,也懶得搭話。
直到旁邊的人激地扯了下他的袖子:“看左邊!告示牌下面, 雖然只有個側臉, 但看材和氣質就看得出,絕對條兒順!”
謝厭遲敷衍地抬了下眼。
然而在捕捉到那個影時, 卻突地頓住。
不管隔著多遠的距離,也不管兩個人分開了多久,他還是能一眼認出那個人是誰。
秦郁絕站在完全暴在的地方, 低垂著眼翻看著進校門時志愿者發的考場結構圖。
扎了個高馬尾,有幾縷碎發順地垂在臉側, 后背得筆直。
即使沒什麼刻意的打扮,卻也格外吸引人注意。
興許是太過炎熱,抬起手, 用手腕輕拭了下脖頸的汗。
謝厭遲安靜地看了一會兒,然后突地直起了。
旁邊的同學一愣,下意識地喊了一句。而他卻置若罔聞似的,徑直朝著秦郁絕的方向走去。
Advertisement
然后,在后停下。
謝厭遲個子很高,漆黑的影子瞬間籠罩了下來,將秦郁絕遮了個嚴嚴實實。
灼目的線被擋去,留下一塊地,讓人被太燒得生疼的眼眶頓時放松了下來。
秦郁絕覺察到影的變化,不由一頓,微微偏了下頭。
后的男生姿態慵懶地靠著告示牌,正皺著眉低頭看著準考證上的字符,似乎沒把注意放在自己上。
沒什麼奇怪的事。
秦郁絕收回視線,轉過頭。
兩人一前一后,就這麼安靜地站著。
沒有任何流。
宛若是一對從未有過集的陌生人。
鈴聲響了,考場開放。
秦郁絕將準考證夾著考場示意圖收好,轉朝著教學樓的方向走去。
半點停留都沒有。
只是在轉的時候,高馬尾被風帶起,發尾輕輕打過謝厭遲的胳膊。宛若羽拂過一般,稍縱即逝。
他沒有,只是抬起抬眼,目送著的背影逐漸吞沒在人海里。
將近上千人在涌上前。
但唯獨只有的影格外的清晰。
有什麼東西靠近了,又離開了。
就像一粒紅塵滾洶涌的波濤之中,洗刷,沖撞,然后再也尋找不到。
第二次重逢,是在大一。
謝厭遲作為代表,來到秦郁絕的學校來參加聯辯論賽。
中午午休的時候路過報告廳。
話劇社正在排練著不久之后給學長學姐們的畢業儀式表演的節目。
秦郁絕是主角。
謝厭遲靠著后門,朝著舞臺的方向去。
站在舞臺上的,即使沒有任何華麗的裝扮,卻也能將上的芒展得淋漓盡致。
報告廳只是借用,所以并沒有開空調。在最炎熱的季節,就連地板和座椅都悶得發熱。
結束演練后,秦郁絕因為下午有課,并沒有回宿舍,而是挑了個座椅,側趴在扶手上小憩。
謝厭遲靜靜地看了一會兒,等人全都走了,才走到旁的位置坐下。
秦郁絕的碎發著脖頸,被汗水浸,呼吸輕輕的,眉頭皺,看上去睡得很淺,而且并不安穩。
然后,突然來了陣風。
裹挾著清涼,溫和地拂過。
謝厭遲靠著椅子,將辯論賽的稿件折四分之一,胳膊架在扶手上,有味甜一搭沒一搭地替扇著風。
從頭到尾,一言不發。
這場覺睡得是意外之中的舒適。
秦郁絕醒來的時候,手了自己的后背。
意料之外的,沒有被汗,反而脖頸還有些涼意。
起,拿起自己的課本,看了眼時間,然后抱著書匆匆地趕往教室。
這不知道是多次,謝厭遲目送著秦郁絕的背影離開。
屈指可數的重逢里,兩人從沒有說過一句話。
哪怕是一句問好。
但有些事從來沒有什麼公平與不公平的。
世界上大多都是這樣。
所隔山海,山海不可平。
喜歡一個人是藏不住的。
哪怕是賀懷早就告訴過自己,像謝厭遲這種滿跑火車,看上去花言巧語一大堆的人,在上是最靠不住的。
但秦郁絕卻還是會相信他的話。
只要他說,就愿意相信。
現在他說了。
那麼就愿意去賭。
秦郁絕無比認真地看著他的眼睛,眸沒有半點閃爍:“你還有什麼其它的相對我說嗎?”
“有。”謝厭遲回著,然后一字一句地說出那三個字,“我你。”
“好。”秦郁絕垂眼,似乎是笑了,但又似乎是沒有,只是輕聲說,“那我相信了。”
接著,出手搭上他的側頸,拉近兩人的距離,閉上眼睛抬頭吻上他的。
腦海中的那栓著理智的弦徹底被剪斷。
謝厭遲抬手扣住秦郁絕的后腦,加深了這個吻。
帶著侵略的氣息闖,仿佛就連空氣都變得稀薄。
這是一個漫長而又短暫的過程。
從玄關一路到客廳,最后在陷進沙發之中,將衫出一條又一條的折痕。
呼吸在這一刻徹底癡纏在一起。
與深一同宣泄,天花仿佛都在墜落,連帶著兩人的軀,一起陷。
許久后終于分開。
“這麼容易相信我。”
謝厭遲啞著嗓音,抵住的額頭,扣住的后頸,輕聲問:“就不怕我利用你?”
“謝厭遲,我不在乎有沒有被利用。”秦郁絕的語調平靜,沒帶一點抖。
看向他眼底時,眸中干凈地讓人不忍將拉進任何泥潭。
說:“我在乎的事,已經知道答案了。”
謝厭遲沒立刻接話,只是這麼安靜地看著面前的人。
在自己面前。
就這麼毫無保留的,毫無抵的躺在自己面前。
不是一個背影,也不是一個肩而過。
沒有任何盔甲,就這麼無比信賴地看著自己的眼眸。
明明這一切都是謝厭遲的東西,但在這一刻,卻不知道從何而來的一緒涌上心頭,撞得五臟六腑仿佛都在撕裂般的疼痛。
那雙眼眸越干凈,越是毫無保留地去托付真心,就越像千斤重的力附著在自己的心臟上。
他從來沒有這麼憎惡過自己。
自己到底做了什麼。
親手將秦郁絕推到了他無法承擔后果的位置,讓與自己共同面對一個并不確定的未來。
僅僅是為了那一點私心。
謝厭遲閉上眼,眉頭皺。
即使是這樣,秦郁絕卻也能從他的神中讀出痛苦。
不知道那痛苦的來源,但確信與自己有關。
秦郁絕沒有說話,也沒有任何作,只是就這麼安靜地看著他的臉。
下一秒,謝厭遲傾而下,扣住的后背,將擁懷中,然后低下頭靠進的肩窩。
“我不知道你在顧慮些什麼,謝厭遲。”秦郁絕抬手,搭上他的后背,聲音溫而又堅定,“但是我還年輕。”
“我不計較后果。”
從十年前,二十年前,或者很久很久以前開始。
秦郁絕就是這樣一個人。
無論擁有什麼樣的家世,無論是天之驕,還是從高落下,始終都是這樣一個人。
不計較后果。
不怕面對后果。
夜。
凌晨四點的時候,謝厭遲睜開眼。
他起靠在床頭,將胳膊搭在膝蓋上,轉頭看著旁睡的秦郁絕。然后出手,替撥去臉頰的碎發,傾而下,輕輕吻在的額頭上。
接著,下床來到臺。
謝厭遲關上臺的門,出手機點開微信。
第一條消息,就是陳助理發來的。
陳助理:【謝何臣先生的機票是明天,大概后天就會回國。】
謝厭遲垂眸,轉靠著欄桿,從兜里出一煙,夾在指間點燃。
這是一個信號。
從謝何臣回國開始,謝氏就要徹底變天了。
他側,指間那點腥紅忽明忽暗。
許久后,似乎又想起什麼,給一個號碼撥去電話。
電話很快被接通。
“凌晨四點給我打電話,也只有謝二有這個面子讓我不當場罵人了。”那頭的男聲語調謙和,摻雜著幾句調侃。
謝厭遲沒同他調侃,只是淡淡道:“我答應你了。”
電話那頭突地沉默了下來。
許久后,才傳來幾聲爽朗的笑:“這可是個大工程,投資風險也很大,謝先生不多做考慮?”
“有條件的。”謝厭遲抬了下眼。
男聲稍有停頓:“您說。”
“照顧好,萬一我不在了。”謝厭遲說,“畢竟是你的妹妹,秦先生。”
“我猜到了。”那頭的人低聲一笑,“謝先生不必多慮,我和郁郁遲早會站在一條線上的,自然會照顧好。”
說到這,他一頓,畫風一轉:“反倒是您,真的決定這麼做了?”
謝厭遲笑了聲:“我沒得選。”
“那希您能順利回來。”電話那頭的人朗聲開口,“期待和您的下一次合作。”
掛斷電話后,謝厭遲將手機拋了拋,收了起來,然后轉——
秦郁絕披著件外套,站在一門之隔的地方,看著他。
見謝厭遲打完電話,才拉開推拉門走到臺,站在了他的邊。
“你們男人都有半夜不睡覺的習慣嗎?”秦郁絕看他一眼,“放心,我沒有聽人電話的習慣。但還不至于遲鈍到,覺察不到你的不安穩。”
謝厭遲掐滅指尖的煙:“這里風大。”
秦郁絕深吸一口氣,抬眼看著天上的漆黑的夜空,聲音帶著些輕:“謝厭遲,如果有一天你要離開,不要編造任何理由騙我。”
謝厭遲沉默一下,然后閉眼:“嗯,我不騙你。”
作者有話要說: 過渡章無敵卡文……
第三更可能得咕咕咕了抱歉!
猜你喜歡
-
完結106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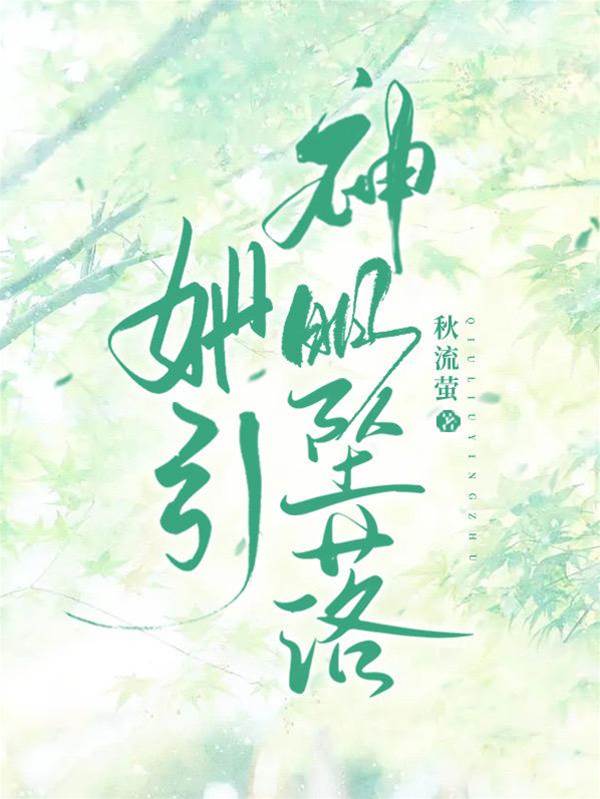
她引神明墜落
沈黛怡出身京北醫學世家,這年,低調的母親生日突然舉辦宴席,各大名門紛紛前來祝福,她喜提相親。相親那天,下著紛飛小雪。年少時曾喜歡過的人就坐在她相親對象隔壁宛若高山白雪,天上神子的男人,一如當年,矜貴脫俗,高不可攀,叫人不敢染指。沈黛怡想起當年纏著他的英勇事蹟,恨不得扭頭就走。“你這些年性情變化挺大的。”“有沒有可能是我們現在不熟。”宋清衍想起沈黛怡當年追在自己身邊,聲音嬌嗲慣會撒嬌,宛若妖女,勾他纏他。小妖女不告而別,時隔多年再相遇,對他疏離避而不及。不管如何,神子要收妖,豈是她能跑得掉。某天,宋清衍手上多出一枚婚戒,他結婚了。眾人驚呼,詫異不已。他們都以為,宋清衍結婚,不過只是為了家族傳宗接代,那位宋太太,名副其實工具人。直到有人看見,高貴在上的男人摟著一個女人親的難以自控。視頻一發出去,薄情寡欲的神子人設崩了!眾人皆說宋清衍高不可攀,無人能染指,可沈黛怡一笑,便潦倒萬物眾生,引他墜落。誰說神明不入凡塵,在沈黛怡面前,他不過一介凡夫俗 子。
20.2萬字8 45509 -
完結169 章

溫先生的心尖月
(蓄謀已久 細水流長 甜寵 雙潔 無虐 年齡差五歲左右)(女主醫生,非女強)*【溫婉清麗江南風美人 & 內斂沉著商圈大佬】容煙出身書香門第,自小跟隨外公生活。聽聞外公給她尋了門親事,她原以為聯姻對象是同為醫生的溫二公子,殊不知卻是接管溫家的溫景初。煙雨灰蒙,寺廟裏,容煙瞥見與她擦身而過的男人。上一次見他還是四年前,可他從不信神佛,為何會出現在這裏?朋友生日聚會結束,溫景初送她歸家。車內,容煙壓住心中疑惑,終究沒問出口。*容煙本是溫吞的性子,喜靜,信佛。她自認為婚後的兩人是相敬如賓,搭夥過日子。而他卻步步誘她淪陷。某日,容煙在收拾書房時看到了寺廟的祈福袋,裏麵白色宣紙上寫著她的名字,似乎珍藏了許久。而此時溫景初正接受電視臺采訪,清肅矜貴,沉穩自持,淡定從容與人交談。主持人問,“溫先生,聽聞您並不信神佛,但為何每年都到靈山寺祈願?”容煙手中拿著祈福袋,略帶緊張的等待著他的回答。男人黑眸如墨,思忖片刻,緩緩啟唇,“因為溫太太信佛。”簡單一句話卻擾亂她的心。
33.1萬字8.09 26548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