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迫營業的算命先生日常》 279
南時聽了這句話,反應尤為的大,他猛地抬頭看向了池幽,驟然與池幽四目相對,又連忙的垂下頭,只聽他說:“……不了,師兄要不我站著?”
池幽緩緩地說:“南時,你聽話些,不要讓我人來請你去書案。”
南時呼吸一滯,咬了咬牙認命地站了起來,書案本就在他的側,他旋就伏了上去。他悶悶的說:“好了,師兄。”
話音未落,他就覺得他的背脊被一件冰涼的東西抵住了,他敏得抖了一抖,他心知池幽就站在他的背后,最好什麼作都不要有,便解釋說:“……有點涼。”
很快抵著他的戒尺就不那麼涼了,本就是手生溫的東西,他的溫染了上去,稍稍好了些,但存在實在是太強烈了,說一句如芒在背也不過分。
南時神有些張,全副心力都關注著那柄戒尺。
突然之間,他的手腕被人了一,他側臉看去,就見池幽一手落于他的手腕上,松松地罩在上方,池幽慢慢的說:“會疼,但不許掙,也不許用力握拳。”
師兄你怕我把傷口掙得崩開就不能不打我嗎?!
南時心下這麼想著,口中卻溫和的應了一聲:“好,師兄,我知道了。”
戒尺離開了南時的背脊,南時深吸了一口氣,咬住了牙關,卻久久沒有等到背上的痛楚,他還是不自覺地有些張——廢話,誰知道接下來要挨打能不張?他只求池幽可別猶豫了,趕打完了事也比現在懸而不落來得好。
正在他想開口之際,戒尺落了下來,卻不是帶著力道的,而是輕輕地抵在了他的背脊上。
而池幽卻著南時的背脊沉著,不知該如何手。
Advertisement
南時伏在案上,肩胛骨向兩側飛起,出了一個玲瓏的弧度,脊柱所在微微向下凹去……這里,是不能打的。
脊柱是人致命之一,稍有不慎,打死打殘都是正常的,其下又有五臟六腑,他往日從不打南時背脊就是因為這個原因。
他自然不愿意南時傷筋骨,還是那句話,打他是為了訓誡他,教育他,而非傷害他。
正思索著應該如何理才好,突然戒尺上卻傳來了一陣震,池幽抬眼去,就見南時回頭再看他,苦著臉說道:“師兄,您就趕下手吧,我知道錯了。”
池幽那柄戒尺居然沿著他的脊椎劃了一下,南時差點沒控制住本能反應直接從桌子上跳起來。
……有點,還有點麻。
南時此刻并不是很愿意用親昵得近乎于猥的想法求想池幽,但也架不住池幽這麼整他啊!
池幽嗤笑了一聲,居然就此放手,仍由戒尺落在了南時的背上,轉而手了他的腰帶,綢衫本就堆積在腰間,全靠腰帶撐著,失去了腰帶,就全順著落到了地上。
有什麼好猶豫的,還有一適合手不是嗎?
南時只覺得下一涼,接著破風聲響起,戒尺與皮接的響聲幾乎和火辣辣的痛覺同時傳來,南時倒了一口氣,下意識想要抓住什麼,卻只能抓住池幽的一手指。
淡淡的荒謬傳上了南時的心頭,還未來得及出聲就聽池幽道:“不許掙。”
手上傳來作,池幽將他的手翻了過來,以五指將他的手指扣住,南時張了張口,破風聲又響了起來,他想出口的話又變了悶哼聲。
池幽每打一下就問一句:“知錯了嗎?”
“知錯了。”南時回答道。
“錯在哪里?”
“不該以犯險,仗著自己有幾分本事就胡鬧。”
“還有?”
“我能選擇更好的方式……嘶——疼……我大可以等家里來人,再將水潭給干凈了,什麼不能找?我偏生慣著它自己往下跳……”
“以后還敢嗎?”池幽收了手,戒尺自然垂下,不再他。
本來的皮上已經腫了一片,戒尺兩側的棱柱在南時上留下了明顯的腫脹的痕跡,池幽輕輕地松開了自己的手,卻發現南時的手指正用力的扣著他的手掌:“松開。”
南時伏在案上不敢,疼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不太方便說,還是再趴一會兒比較好,他也發現了自己不聽話的手,默默地松了開來,仍由池幽的手離去:“師兄,我不敢了……我疼得厲害。”
“起來。”池幽吩咐道:“難道你希就這樣人來看傷?”
“別別別……”南時一迭聲的說:“太丟人了,我自己涂點藥就行了。”
“嗯,知道丟人倒還好。”池幽沒有理會堆積在南時腳跟上的綢衫,轉去一旁的架子上了一件干凈的長衫過來披在了南時上,也不管他如何,攔腰就將他提溜到了床上去,他似乎到了什麼,卻又一個字都沒有提,轉而道:“趴著。”
南時已經沒臉見人了,恨不得一把掐死自己,他聞言立刻翻了過去,也顧不得疼不疼的事了,廢了了事,免得以后還這麼丟人。
池幽轉出了屏風,南時聽見腳步聲遠了,這才小心翼翼的探頭打量了一圈周圍,見池幽不在了才松了一口氣。
床是標準的拔步床,一側旁邊放著一個長木幾,上面擺著一壺水,南時半撐了起來也不講究什麼,給自己灌了小半壺水,轉而手朝尷尬的地方了一把,倒了一口氣將它了回去。
真是要命。
沒想到過了好一會兒外面才聽見響聲,南時很清楚的知道只有池幽進來了,而沒有帶別人——早知道池幽隔了這麼久才回來,他廢那個功夫做什麼?疼得要命!還不如等它自然消退下去。
池幽緩步進了里間,手中還帶著一罐藥膏,南時出手要接過,就看見池幽避了開來:“老實躺著。”
南時一瞬間就領悟到了池幽的意思,尷尬的說:“不用,師兄我自己來就好了。”
“或者我晴嵐來替你上藥。”池幽說是一個選擇題,實際上沒有給南時選擇的機會,一手按住了南時的背脊,將他生生按趴了下去。
被一揭開,便出了滿是傷痕的,已經腫了一片,倒是沒破皮。
池幽顰眉,暗忖是不是下手太重了些,轉而一想,重什麼重?
他服是為了不讓的碎片嵌進皮里,難以清理,如今連皮都沒破,算什麼下重手?
碧綠如同一塊水晶一般的膏糊在了南時的上,南時不自覺地抖了抖,火辣辣的痛覺瞬間轉化為了清涼冰爽的覺,他舒服得低嘆了一聲,轉而將自己埋了枕頭中。
縱然知道池幽沒有別的想法,南時還是有些臉上發燙。
“我希這是我最后一次訓誡你。”池幽突然說。
“嗯。”南時低低的回答道:“我知道的,師兄,我以后不會了。”
“以后出門要帶人。”池幽慢慢地說:“我給過你自由了,南時,你沒有把握住。”
南時:“……也還好?其實習慣了邊沒人我還覺得有些不習慣。”
池幽一哂,上完藥后也不替南時蓋上被子,就任由他這麼躺著:“不許蓋被子,等到藥干了就好了。”
“是,師兄。”南時應了一聲,聽見了幾步腳步聲,接下來卻沒有靜了。他悄悄抬頭一看,卻見池幽就坐在不遠的書房里,過屏風還能瞧見他的一二分角。
南時又趴了回去。
池幽是真的不拿他當外人,他著躺在床上,池幽就是有那個耐心擱那兒一坐。
天道爸爸給了他象暗示他會和池幽結發,瞧這德,得了,七分天定三分人定,結個鬼的發。
***
翌日,南時睡得迷迷糊糊的只覺得自己上粘了什麼東西,手往后一,就到了一張乎乎的膠狀玩意兒,直接住了邊緣用力一撕:“嗷——!”
南時睜開眼睛,看了看手上著一張半明的膠狀,也不明白自己怎麼就把藥膏扯下來了,這算是干了吧?——剛剛那聲是他的吧?
猜你喜歡
-
完結191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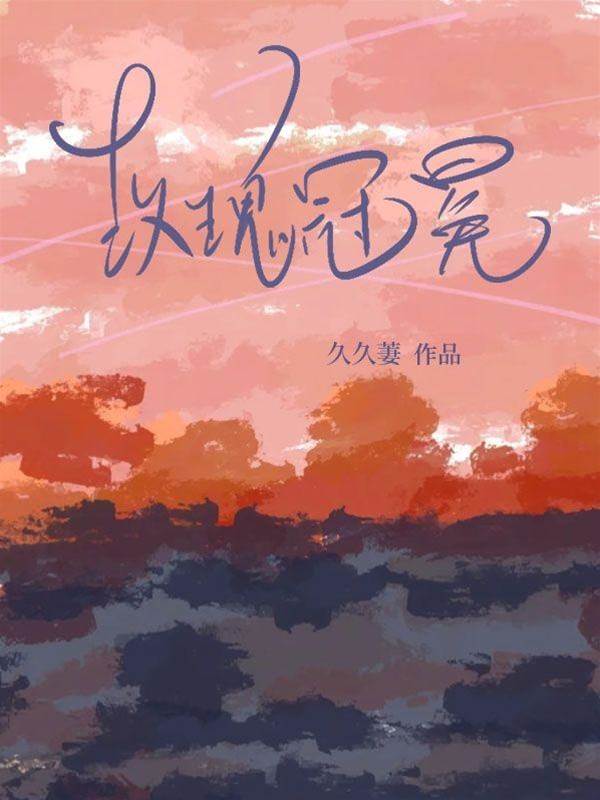
玫瑰冠冕
【先婚後愛?暗戀?追妻火葬場女主不回頭?雙潔】她是徐家的養女,是周越添的小尾巴,她從小到大都跟著他,直到二十四歲這年,她聽到他說——“徐家的養女而已,我怎麼會真的把她放在心上,咱們這種人家,還是要門當戶對。”-樓阮徹底消失後,周越添到處找她,可卻再也找不到她了。-再次相見,他看到她拉著一身黑的少年走進徐家家門,臉上帶著明亮的笑。周越添一把拉住她,紅著眼眶問道,“軟軟,你還要不要我……”白軟乖巧的小姑娘還沒說話,她身旁的人便斜睨過來,雪白的喉結輕滾,笑得懶散,“這位先生,如果你不想今天在警局過夜,就先鬆開我太太的手腕。”*女主視角先婚後愛/男主視角多年暗戀成真【偏愛你的人可能會晚,但一定會來。】*缺愛的女孩終於等到了獨一無二的偏愛。
33.4萬字8 61089 -
連載199 章

她一哭,他發瘋,京圈誰都惹不起
傅梟寒是A市權勢滔天的商業大佬,他手段狠辣,冷血陰鷙,禁欲高冷,不近女色,是無數名門世家女擠破頭,也觸碰不到的高嶺之花。唐星覓從小日子過的清苦,寄人籬下,舅媽為了16萬把她送給一個大腹便便的油膩男。她不想斷送自己的一生,拚命反抗,逃出狼窩,卻意外闖入他的房間,一夜旖旎,誰知,一個月後檢查出她肚子裏懷了寶寶。自從那夜嚐過她的“甜美”後,男人食髓知味,一發不可收拾,找到她,臉皮厚的纏著她非得要一個名分
27.6萬字8 5806 -
完結113 章

多雨之地
青春治愈 校園 情有獨鐘 HE 如果淋雨無法避免,那就一起變潮濕。陳準知道凌羽是誰。是開學遞給他一把傘的陌生人,是朋友口中有名的“怪咖”, 是舍友昔日的追求者,更是往他心口上插一把刀的騙子。
16.6萬字8 409 -
完結574 章

她發瘋,他兜底,團寵誰都惹不起
雙潔+馬甲+醋王暗戀+強寵酥爽+互撩拉扯+先婚后愛+虐渣打臉和渣男分手后,徐方梨準備回家繼承家業,結果家里的總裁哥哥可憐巴巴跪求:“家里要破產了,你去聯姻吧!” 聯姻就聯姻,可誰能告訴她不是破產了嗎?那個民政局門口開著跑車,載著美女,呲著大牙的狗頭怎麼那麼像她哥! 為兄弟兩肋插刀,為了妹夫徐方野直接插自己兩刀! - 韓二爺心底有一個埋藏近二十年的秘密。 他連跳數級出國深造,不擇手段掌控權勢,都是為了早一天站到那個女孩面前。 他最潦倒的那一年,她談了戀愛,他往返數次沒敢露面。 六年后,她分手,他果斷出現聯合大舅哥將人叼回家。 - 小糊咖搖身一變成了豪門團寵,隱婚闊太! 娛樂圈三料視后:從今天開始,這就是我親妹子! 國際頂流音樂天才:小梨子,再給我寫首歌怎麼樣? 買下一座山隱居的老爺子:小祖宗,趕快回家繼承家業! 人傻情多狗頭哥:老妹!給你買了個小島,你看起個什麼名比較好? 韓二爺將人按進懷里,低聲誘哄:果寶,還想往哪跑?
101萬字8 1946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
